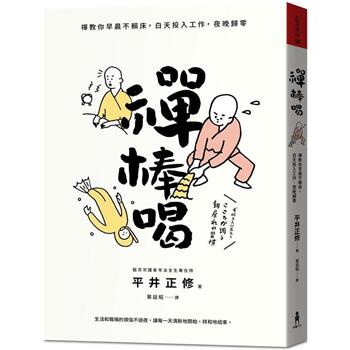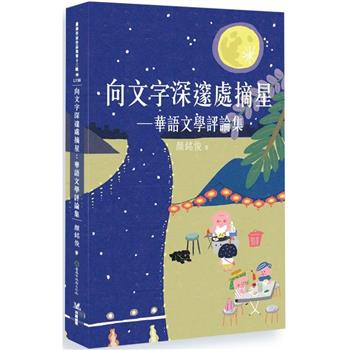2如果這都不算憂鬱症
冷小星宣布我得了憂鬱症的現場遠比想像中的平淡無奇。沒有太多的歇斯底里。因為最大的歇斯底里已經過去,而小的歇斯底里已經成為常態。
那是一個同樣非常冷的早上,我醒得很早,雖然睡了覺卻渾身疲倦,頭腦昏昏沉沉。肚子無止盡的隱隱難受仍未消失,不停地消耗著我的耐心。我叫醒昨晚剛剛和我吵過架還沒跟我和好的男友,沒好氣地說了一聲「我不舒服」。
冷小星閉著眼睛沒有出聲。
我知道他在裝睡,不想理我,於是狠狠地扭動了幾下自己的身軀。在扭動的過程中,我突然感覺到自己的身上好像布滿了滑溜溜又甩不掉的肉。我從床上跳起來,跑到浴室裡,從鏡子中觀察自己。雖然我早就知道自己已經胖得不成樣子,不過鏡子中的形象仍然震顫了我的心靈:胖大的臉龐,胖大的後背,外加原來自己最痛恨的胖大的大象腿!我走回房間,再次搖動冷小星並問他:「喂,你知道『虎背熊腰』是什麼意思嗎?」
他這次睜開了眼,但仍然沒有回答。
不得已,我只好提示他:「就是說我這樣的。」
我等待著冷小星的反應,希望他能安慰我兩句,他卻像想起來什麼似的問我:「現在幾點了?」
我失望地倒在他身旁,翻了個身,沒有理他。過了一會兒,他自己坐起來,伸了一個懶腰,拿起桌子上的手機看了一眼時間,然後說:「我得走了。」
我知道他這句話是說給我聽的。
每一個清晨,都好像是同一個清晨;每一場戰爭,都好像是同一場戰爭。我和冷小星日復一日地為他上班的事爭吵。我不喜歡他在我還沒起床的時候就走了,我不喜歡他在還沒有跟我說完話的時候就走了,我不喜歡他在我難受不舒服的時候就走了,我不喜歡他在我還沒有吃完早餐的時候就走了。我沒有說出口的是:無論是什麼藉口,其實我就是不喜歡他去上班。因為他走了之後,滿屋子空蕩蕩的,我一個人承受不了。有時我問自己:妳承受不了的是什麼?是寂寞嗎?
是孤獨嗎?是身上的難受嗎?是心裡的煩惱嗎?我面對自己的質問,卻不知該如何回答:答案太過複雜,我欲言又止。
都不是,又都是。
一個人在家的時候,我常常會覺得心裡有解不開的結。為碰到的每一件事、每一個人擔憂,想了各式各樣的辦法,卻又覺得這些辦法都是死路,總有這樣那樣的原因讓這些辦法成為不可能。我也常常站在陽台上朝著對面的大樓大聲呼喊:「喂,有人嗎?」結果當然是無人應答。
想到這些我就覺得忍受不了。等我回過神來的時候,冷小星已經穿好衣服、穿好鞋走到門口了。
我幾乎是下意識地跳下床,衝到門口。我沒有看清他是什麼表情,只是抱著他的胳膊不肯放手,一邊抱著一邊哭,眼淚不受控制地紛紛落下。
「妳是不是又不想讓我走了?」
我愣了一下,然後又繼續哭。我不敢回答他的問話,我怕回答了之後,又是爭吵,而爭吵到最後,還不是魚死網破,他還是要走,我還是要繼續承受這一切。
冷小星默默地站了一會兒,就讓我這麼哭著。我聽到他的嘆息聲。
這次他沒有發火。他說:「妳別哭了,我今天不去上班了。」我擦擦眼淚,揚起臉,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我看見冷小星十分平靜,一臉溫柔,不像是騙人,於是漸漸止住了哭聲。
我其實一直不知道那天早上是什麼使冷小星一改平日作風,毫無怨言地陪我待在家裡。那天我們一起做了早餐,又去樓下的院子裡散步,像美好得不能再美好的正常情侶一樣。回到家後,他打開連接著電腦的電視機,陪我看起了《龍貓》。
動畫片中漫長得似乎沒有盡頭的日本鄉村夏日午後的氣息,藉著電視機的螢幕,慢慢滲透過來,我感覺心裡暖洋洋的,也沒有什麼擔憂。好想時間靜止,將生活定格在這幅畫面裡。
「妳為什麼不願意讓我去上班?妳怕什麼嗎?」
看來他和我有同樣的疑問。我搖搖頭,表示不知怎麼回答。
「為什麼不找點自己喜歡的事做呢?」
「我……沒有喜歡做的事……」
冷小星一臉懷疑地看著我:「不會吧,一件喜歡做的事都沒有嗎?」
「嗯。」
「妳不是很喜歡看書嗎?」
「現在看不進去了。」
「那動畫片呢?」
「不想看,覺得很無聊。」
「妳現在不就在看動畫片嗎?」
「那是因為有你陪我,要是我一個人就堅持不下去。」
冷小星對我的回答無可奈何,不過還是進一步問我:「為什麼以前喜歡做的事,現在都沒興趣了?」
「因為我覺得很虛無,什麼都沒有意義。」
「是虛無嗎?」他半是問我,半是問自己。
我點點頭。
冷小星沉默良久,我也沉默良久。「虛無」這個詞,讓我們都說不出話來。
冷小星不甘心,又問我:「那妳為什麼一直哭?」
這次輪到我用懷疑的眼光看他:「哭也不行?」
「不是說不能哭,但總有理由吧。」
對,我為什麼總是哭哭啼啼呢?
「妳是委屈嗎?」
嗯,我是有點委屈,因為覺得自己已經很努力在生活,但別人不理解。
「妳是害怕嗎?」
可能我也有些害怕。我總覺得身體隨時有可能越出可控的範圍,各種疑難雜
症的名字充斥在我的腦海裡,不停地飛速旋轉。
「妳是擔心嗎?」
這簡直是廢話……肯定有各式各樣的擔心。光是越來越胖的身材和越來越近的學位論文寫作就夠我糾結一萬次了。更別提還有男友、家人,五花八門的關係纏繞著我,對哪個都得負責,但我現在又沒有能力負責。
浮想聯翩之際,冷小星大喝一聲:「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妳這樣啊?」他大概是問得不耐煩了。他的大吼驚醒了我,但這也讓我大哭起來。
「嗚嗚嗚。」
我一哭,冷小星著急了,趕忙哄我,「妳別哭呀,別哭、別哭呀!」但我一時卻停不下來。
「妳幹嘛哭啊?我……我也沒對妳怎麼樣呀。」
「你是沒對我怎麼樣,但我就是想哭……你老是問我為什麼,但我說不出來,我……我不會表達了。」
「怎麼會不會表達呢?」
「我……我有話說不出。」
「所以妳就哭?」
「嗯。我控制不了,就是想哭。雖然知道哭也沒什麼意義,但除了哭也沒有別的辦法……」
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沒有邏輯的話。
冷小星不再說話。我拿起桌子上的面紙,一邊擦眼淚,一邊繼續哭。我抬頭看著他,他的睫毛翻飛,眉頭有點皺,想事情的時候他總是這副表情。
「我想,妳是不是—我覺得妳得了憂鬱症……」
冷小星宣布我得憂鬱症的瞬間,我的腦子「轟」地響了一下。這響聲不是那種因為受刺激產生的反應,而是突然被點醒了什麼事的時候腦中發出的聲音。說是一下子豁然開朗了也不算太誇張。我並沒有心情沉重,也沒有悲傷,反而置身在一種幸福的幻想中,覺得一下子釋放了什麼。那種感覺就好像坐在一個花園裡,滿眼綠色,各式各樣的花開著,四周馨香,微風吹來又吹去,什麼聲音都沒有,好安靜。
我晃了晃腦袋,試圖把這些奇怪的感覺趕跑,看著冷小星睜得大大的眼睛,重新思考他剛才提出的話題。雖然我內心覺得有這個可能性,但還是不想就這麼承認:「不會吧,我怎麼會得了憂鬱症呢?」
「妳睡不好吧?」
「嗯……有時候不太好,有時候還行,只是每天都做好多夢。」
「無節制地哭?」
「……有點。」
「心裡的想法不能表達?」
「因為表達了也沒有任何人能懂啊……不過我有時會自己對自己說……」
「想去戶外參加活動嗎?」
「有時候想,不過出發前又會突然覺得沒意思,然後可能就不去了。」
「妳對自己還有希望嗎?」
我搖搖頭。
「妳覺得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懂妳,是嗎?」
「除了迴力球。」
「迴力球?迴力球是誰?」
「是我自己想像的能懂我的小伙伴,他就住在對面的大樓裡,我有時朝著對面的大樓跟他喊話,然後在想像裡回答自己。這樣,才覺得還有人陪著我,懂我。」
我的話把冷小星噎得半天都沒喘過氣來,之後他板著一副嚴肅的面孔,一字一頓地說出這樣一句話:
「如—果—這—都—不—算—憂—鬱—症,那—妳—可—能—是—腦—子—進—水—了。」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男友說我得了憂鬱症的圖書 |
 |
男友說我得了憂鬱症 作者:學中文的許小姐 出版社: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出版日期:2023-10-13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85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34 |
精神疾病 |
$ 300 |
中文書 |
$ 300 |
心靈勵志故事 |
$ 34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男友說我得了憂鬱症
正視成長傷痛,走出內心孤島,來自憂鬱星人的內心告白。
百萬讀者邊哭邊笑共感大推,改編影視劇製作中!
獻給微笑但不快樂的你──
別怕,這個世界上有許多和你一樣,需要被溫柔以待的人。
你終將獲得直視生活的勇氣,與世界和解,與自己相愛。
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感到不快樂,無法擺脫不安,想被愛又怕受傷害,委屈自己滿足他人期待,請翻開鍾西西的故事。
你會看見,面對個人成長、原生家庭、親密關係的不知所措、不被理解、不被認可,究竟能夠做些什麼。
鍾西西,二十五歲,某知名大學中文系研究生。
學業和愛情看起來都順利的她,卻從某一刻開始感到身體不舒服,對任何事都提不起勁,無法獨處,動不動想哭,還經常對喜歡的人發脾氣。
她不知道自己怎麼了,直到有一天,男友宣布她得了憂鬱症。
「不會吧,我怎麼會得憂鬱症?」雖然不想承認,但她終究得面對。西醫檢查、中醫調理、接觸信仰、閱讀、跑步……
此時的她還不知道,最激烈的衝突才要展開……
但當一切歇斯底里都塵埃落定後,鍾西西發現,這個世界上重要的是──愛與和解。
每個人都可能遇到絕望、孤獨、低潮,如果你憂鬱了,這個故事會陪著你,把不知如何表達的都展現出來;
若你是陪伴者,除了幫助你更理解憂鬱星人,也希望你記得好好照顧自己。
【讀者誠摯推薦】
「越溫柔的人越是容易痛苦。但我更願意相信,憂鬱症是心軟的神給人類的假期,讓疲憊的心靈得到撫慰和休息。」──蘇更生
「讀到一直哭。我非常非常喜歡這個故事。就好像骨頭模到骨頭一樣的相處和愛,還有長大。」──SCALLET
「總能被裡面的一些字句觸動內心,會在生活中突然想到,並讓我重新打開這個故事去閱讀。」──再見天南星
「其實我也和主人公一樣,在生活中總是為自己畫上條條框框,這個事實讓我一直處在傷心和恐懼裡。謝謝這本書讓我有勇氣丟掉那些框架,慢慢變成更好的自己。」──AMBER_YT
「用兩天時間一口氣讀完,好幾次崩潰大哭。很療癒,謝謝。」──袁小安
作者簡介:
學中文的許小姐
學中文的許小姐,本名許莎莎,一九八七年出生於北京,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
作品散見於《芙蓉》、《詩林》等。
章節試閱
2如果這都不算憂鬱症
冷小星宣布我得了憂鬱症的現場遠比想像中的平淡無奇。沒有太多的歇斯底里。因為最大的歇斯底里已經過去,而小的歇斯底里已經成為常態。
那是一個同樣非常冷的早上,我醒得很早,雖然睡了覺卻渾身疲倦,頭腦昏昏沉沉。肚子無止盡的隱隱難受仍未消失,不停地消耗著我的耐心。我叫醒昨晚剛剛和我吵過架還沒跟我和好的男友,沒好氣地說了一聲「我不舒服」。
冷小星閉著眼睛沒有出聲。
我知道他在裝睡,不想理我,於是狠狠地扭動了幾下自己的身軀。在扭動的過程中,我突然感覺到自己的身上好像布滿了滑溜溜又甩不掉的肉...
冷小星宣布我得了憂鬱症的現場遠比想像中的平淡無奇。沒有太多的歇斯底里。因為最大的歇斯底里已經過去,而小的歇斯底里已經成為常態。
那是一個同樣非常冷的早上,我醒得很早,雖然睡了覺卻渾身疲倦,頭腦昏昏沉沉。肚子無止盡的隱隱難受仍未消失,不停地消耗著我的耐心。我叫醒昨晚剛剛和我吵過架還沒跟我和好的男友,沒好氣地說了一聲「我不舒服」。
冷小星閉著眼睛沒有出聲。
我知道他在裝睡,不想理我,於是狠狠地扭動了幾下自己的身軀。在扭動的過程中,我突然感覺到自己的身上好像布滿了滑溜溜又甩不掉的肉...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自序過去種種拼湊出未來
轉眼間,距離這本書開始在豆瓣網站上連載已經過去八年了。編輯說讓我在這次出版前寫一篇序言,腦海裡盤旋的便都是一路走來所經歷的各種細節。八年來,就像每個人一樣,生活帶給了我諸多的驚喜與驚嚇。但整體來說,我深深感恩所遇到的一切。
寫這本書的日子在記憶中已經變得有些恍惚。那時候我應該非常年輕,是一個痛苦而困惑的年輕人,苦大仇深地想著:為什麼別人的生活充滿鮮花與朝陽,而我卻生活在一片絕望的沼澤之中。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我是那麼可愛,真切地思考著人生中最根本而艱深的問題,並毫不畏...
轉眼間,距離這本書開始在豆瓣網站上連載已經過去八年了。編輯說讓我在這次出版前寫一篇序言,腦海裡盤旋的便都是一路走來所經歷的各種細節。八年來,就像每個人一樣,生活帶給了我諸多的驚喜與驚嚇。但整體來說,我深深感恩所遇到的一切。
寫這本書的日子在記憶中已經變得有些恍惚。那時候我應該非常年輕,是一個痛苦而困惑的年輕人,苦大仇深地想著:為什麼別人的生活充滿鮮花與朝陽,而我卻生活在一片絕望的沼澤之中。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我是那麼可愛,真切地思考著人生中最根本而艱深的問題,並毫不畏...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自 序 過去種種拼湊出未來
第一章 為什麼是憂鬱症
1我
2如果這都不算憂鬱症
3憂鬱症是什麼?
4藍色的催狂魔
第二章 心疾與身疾
1打著遊戲跑醫院
2天地陰陽之氣
3生與死
第三章 亞當和夏娃
1我的朋友周輕雲
2隱形的生活
3溫柔對待自己愛的人
第四章 跑步與幸福
1邂逅村上春樹
2大森林
3愛情心理學
4心理諮商和關於「放棄」
第五章 最終回的說走就走
1青色的島嶼
2我和爸爸
3大結局
附錄:減壓的十個方法
後記
第一章 為什麼是憂鬱症
1我
2如果這都不算憂鬱症
3憂鬱症是什麼?
4藍色的催狂魔
第二章 心疾與身疾
1打著遊戲跑醫院
2天地陰陽之氣
3生與死
第三章 亞當和夏娃
1我的朋友周輕雲
2隱形的生活
3溫柔對待自己愛的人
第四章 跑步與幸福
1邂逅村上春樹
2大森林
3愛情心理學
4心理諮商和關於「放棄」
第五章 最終回的說走就走
1青色的島嶼
2我和爸爸
3大結局
附錄:減壓的十個方法
後記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