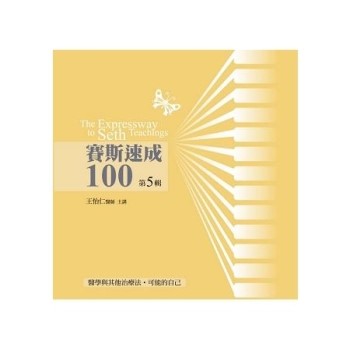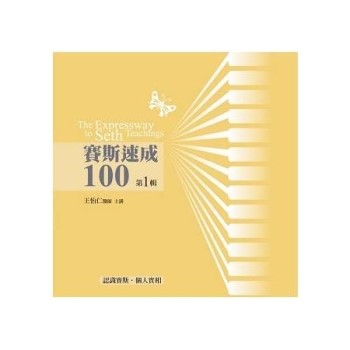第一章 劫法場
太平三年,秋。
汴都西市口處,法場周圍擠滿了看熱鬧的老百姓。
「這般模樣的女子竟要被砍頭,真是作孽啊!話說,她到底犯了什麼罪?」祁宋律法雖嚴,但對女子而言,若非十惡不赦之大罪,一般不會問斬。
「你竟不知?她乃汴都富商秦家才貌雙全的三房嫡女,秦無雙。唉,她哪是犯了什麼罪,不過是被家族連累的。」
那人恍然大悟。「我想起來了,富商秦家!說的可就是他們家的藥行……上貢的保胎藥出了問題,導致皇后娘娘一屍兩命?」提及皇室,那人刻意壓低了聲音。
另一人也低聲道:「正是他們家。」
「不過我聽說,秦家的滿門男丁早在三個月前就被斬首示眾了,女眷也全數充做官妓,為何三房嫡女又被判了斬刑?」
「哪是被官府判的,聽說是她自個兒求的,說什麼『寧做斷頭鬼,不做風塵女,自請與秦家兒郎同生死』。皇上得知後,就隨了她的意,定了秋後問斬。」
「倒是個貞潔烈女,可惜了……」二人唏噓搖頭。
秦無雙穿著囚服,跪在法場中,弱不禁風的背脊上插著一根亡命牌。兩彎似霧非霧遠山眉,一雙似笑非笑清冷目,雖蓬頭垢面,卻風華難掩。她淡淡地看著臺下圍觀的人們對著她指指點點、竊竊私語,杏眸中始終無波無瀾,無端跪出一絲頂天立地的態度。
監斬官大喊:「午時三刻已到,行刑!」
法場上,劊子手抽走秦無雙背後的亡命牌扔在地上,雙手舉起冷森森的鬼頭大刀,刀刃折射出刺眼的白光,晃得眾人睜不開眼。
秦無雙微微仰頭,看了一眼最後的蒼穹白雲,然後,緩緩閉上雙眼。
突然間,平地一聲驚雷巨響,緊接著地動山搖、震耳欲聾。只見東方狂奔而來數十匹烈馬,馬尾巴上皆綁著一串噼哩啪啦作響的鞭炮,東撞西撞、亂哄哄地衝進了法場。
百姓何曾見過這等場景,當下嚇得四散奔逃,監斬的官員也早已抱著官帽躲了起來,法場上很快只剩下秦無雙和手足無措的劊子手。
旋即,秦無雙看見了此生都無法忘懷的畫面──
她的死對頭牧斐,身穿黑衣、坐騎黑馬,劍眉星目、英氣逼人。一手拽韁繩,一手執長鞭,堂而皇之地從亂馬叢中直奔法場而來。
接近她時,手法極其俐落地揚出長鞭,將還在震驚中的她牢牢捆住,一把拽起,橫於馬背上,徑直縱馬去了。從出現到離去,不過片刻工夫,彷彿每一步都計算得剛剛好,一氣呵成。
秦無雙橫趴在馬背上,五臟六腑被顛得翻江倒海,臉色鐵青,幾欲嘔吐。
牧斐見狀,忙將她拉起坐在身前。
秦無雙這才緩過氣來,她抬眼見西門已近在眼前,終於反應過來,急問:「姓牧的,你在做什麼?」
牧斐微微俯身攏著她,雙眼直盯城門口,附耳道:「做什麼妳看不出來?小爺我在劫法場。」
劫法場?打死她都不相信,那可是死罪!
可如今事實擺在眼前,由不得她不信。
她與牧斐,從十三歲結怨,至今已有七年。
當初,她因一個誤會得罪了牧斐,之後便開始了被他百般戲弄的日子。她一忍再忍,本想息事寧人,誰知牧斐非要鬧得滿城風雨,讓她顏面盡失。
於是,她也不再裝什麼大家閨秀,乾脆讓名聲爛到底,假借牧斐外室之名,瞎編了無數和牧斐之間的風月話本,將牧斐塑造成一個喪心病狂、始亂終棄的壞男人,嚇得那些原本一心想攀上定遠侯府的女子們,一見到牧家媒人上門,立刻一哭二鬧三上吊,避之為恐不及。
也因此,即使牧斐已年近弱冠,又有一副號稱「都中三俊」之首的堂堂相貌,仍未有哪家女兒敢說與他,就連那些從不被牧家放在眼裡的薄宦寒門之女,也都對他敬而遠之。
直到四年前,聽聞牧斐要娶九公主,秦無雙想著自己已與牧斐鬥了那麼多年,彼此俱是身敗名裂,也算是出了心中惡氣,她雖名聲壞了,無人敢娶,不過倒也樂得自在,打算終其一生侍奉雙親,不再與牧斐為敵了。
豈料,她與牧斐的風月話本,不知怎地竟然落到九公主司玉琪手中,結果牧斐自然是被九公主退了婚。
緊接著沒過多久,就傳來牧斐之父定遠侯牧守業在雁門關外,輕敵冒進、吃了敗仗、身死疆場的消息。聽說皇上大怒之下,直接撤了牧斐舅爺樞密院使金長晟的職,同時抄了定遠侯府。
牧家從此一落千丈,樹倒猢猻散。
大概又過了一、兩載,她在街上偶遇落魄潦倒的牧斐被人從藥鋪裡轟了出來。原來牧家被抄後,牧老太君急怒攻心,不到一個月就去了;牧斐的母親受了驚嚇,又過了半年飢寒交迫的苦日子,身子終於支撐不住,病倒了。
牧斐為救母,四下求藥,起初那些藥鋪的掌櫃還看在當年牧老太君憐貧惜賤的份上,多以救濟,經常捨些藥給牧斐,只是久而久之,便不再相助了。
秦無雙想著若不是她的話本誤了牧斐與九公主的大好姻緣,說不定牧斐不會落得如此淒慘下場。她心裡存了幾分愧意,便暗地求師父親自去一趟牧斐寄居的破廟。
秦無雙的師父乃是汴都醫術首屈一指的民間大夫,號稱「關神醫」,可惜牧斐母親已經病入膏肓、積重難返,即使極力診治,也無力回天,沒過多久,便也去了。之後,牧斐就像人間蒸發一般,杳無音訊。
然而,今日牧斐卻突然出現,還將她從法場上劫走──牧斐的所作所為,令她百思不得其解,難不成是為了報當年害他錯失大好姻緣之仇,故來劫法場,想親手手刃她,以解心頭之恨?
這麼一想,秦無雙不由得嘆道:「牧斐,我知你怪我當初壞了你和公主的姻緣,心裡恨我恨得要死,不過我已經被判了斬刑,你只消等我人頭落地,你的仇就算報了,又何苦多此一舉劫法場親手殺我?」
「誰說我想親手殺妳了?」牧斐低下頭,語調忽軟。「茵茵,我是來救妳的。」
茵茵──是她的乳名。秦無雙震驚地睜大眼睛,不明白牧斐這是在演哪一齣,不禁反問:「牧斐,你莫不是瘋了?」
牧斐朗聲一笑,狹長的丹鳳眼裡透著幾分凜然。「我沒瘋,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當所有人都對他們避之如蛇蠍時,義無反顧出手相助的卻是素來與他不合的秦無雙,真是想不到……
忽聞身後有人飛馬來報,對城門上大喊:「有人劫法場逃往西門來了,傳令爾等速速關上城門!」
守城官兵們聞報,又見一騎飛奔而來,急忙欲將城門關上。
牧斐攏著秦無雙身體的雙臂緊了緊,語氣驟然一沈。「茵茵,別怕,我這就帶妳走。」說完,夾緊馬肚,只聞黑馬長嘶一聲,撒蹄急奔,頓如離弦之箭射向城門,就在門縫即將闔上的一瞬間,黑馬馱著他們險險地衝了過去,奔出西城門,奔向廣闊無垠的天地。
馬蹄砸地後,二人不由得長吁一口氣,只是還沒來得及開口,便聽見城樓上有人喝令。「放箭!」
耳邊立即響起咻咻的箭聲,牧斐只得策馬避讓。
秦無雙這才相信,牧斐確實是來救她的。
可她心知肚明,以牧斐今日之力,如何救得了她?就算能逃出汴都,終究逃不出祁宋。她忙勸道:「牧斐,你快將我放下,獨自逃命還來得及,倘若帶著我這個朝廷命犯,絕對逃不遠的。」
牧斐喘著氣,咬著牙,語氣堅決。「不放,死也不放!」
「你這又是何苦呢?你明知道這樣做根本救不走我!」
牧斐沒有回答,不多時,他的胸膛突然壓了下來。
秦無雙背對著他,不知發生何事,只聽見牧斐氣息不穩地說:「我知道……只是,縱有一線生機,我也想試一試……今日,若能和妳死在一起,足矣……」說著,血便從牧斐口中溢了出來,灑在秦無雙的肩上、胸前。
秦無雙低下頭,呆呆地看著身上血紅的囚衣,久久說不出話。
牧斐的手依舊緊緊地拽著韁繩,只是馬速漸漸慢了下來。
此刻,牧斐背上扎滿箭矢,徹底沒了氣息。
「……牧斐?」秦無雙顫聲輕喊,怕驚醒了他,又怕喊不醒他。
回答她的是呼嘯的冷風和咻咻的利箭聲──地面顫動,身後追兵轉瞬即至。
秦無雙勒馬停下,兩行清淚滾了下來,她緊咬雙唇,看了一眼沒有盡頭的前方。最後,她掉轉馬頭,朝向追兵飛快衝了過去……
睜開雙眼時,頭頂上方是熟悉的蜜合色海棠花撒花雲紗帳,一陣恍惚後,秦無雙驟然驚坐起。
一旁正在掖被子的蕊朱嚇了一大跳,見秦無雙坐起,又驚又喜,口中直唸佛號道:「我的好娘子,您總算是醒了。」說著,在床沿坐下,雙手合十,急忙拜天拜地了一番。
秦無雙驚訝地看著蕊朱,再看了一眼屋內,皆是她最熟悉的秦家閨房陳設,復又看向蕊朱的臉,稚嫩圓潤,是十五、六歲的模樣,然而,蕊朱明明比她大兩歲──
她試探地喊了一聲。「蕊朱?」
蕊朱忙應了一聲,開始嘮嘮叨叨地說起她前幾日夜遊時染了風寒,一回來就發起高熱,一連燒了好些日子,整日迷迷糊糊的,差點嚇壞老爺和夫人。虧得關大夫連守了她兩日,親自施針下藥,這人前腳剛走,她就醒了。喜得蕊朱又將關大夫連連誇了一番。
蕊朱叨了一長串,見秦無雙不說話,只是一臉震驚地看著她,終於察覺到不對勁。她止了話頭,緊張地喚了秦無雙一聲。「小娘子?」
「蕊朱,今朝是何年?」秦無雙突然問。
蕊朱大驚失色,忙抬手摸向秦無雙的額頭,喃喃自語道:「不得了了,小娘子莫不是被高熱燒糊塗了?」
秦無雙反握住蕊朱的手,正色道:「我沒傻,我只是想確定一下今朝是何年而已。」
「……今朝是開寶七年春。」蕊朱皺眉看著她。
開寶七年春,也就是她十三歲之際,蕊朱十五歲,瞧此光景,難道──她已重生,回到年少時?
秦無雙掀開被子就要下床,蕊朱忙按住她。「小娘子,您還病著呢,這是要去哪兒?」
秦無雙急切地說:「我要去找我爹娘。」如果她真的重生回少年時,那爹娘就一定還活著。
蕊朱道:「老爺和夫人在前廳,正為您的事情和牧家夫人鬧得不可開交呢,小娘子這會兒可不能去。」
乍一聽見牧家,秦無雙眉心一跳,忙追問。「牧家?哪個牧家?」
*欲知精采後續,敬請期待8/4上市的【文創風】870《厲害了,娘子》上。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厲害了,娘子(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25 |
華文羅曼史 |
二手書 |
$ 140 |
二手中文書 |
$ 197 |
中文書 |
$ 197 |
文學作品 |
$ 225 |
古代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厲害了,娘子(上)
這世,我不和你吵、也不和你爭,
我想挽救猝不及防的一切,
包含我們之間那道堅不可摧的牆……
祁宋第一紈袴牧斐,竟誤打誤撞討到一個智勇雙全的未婚妻,
擁有天仙之姿、靈活身手,又有聰明頭腦的秦無雙,
配上這位筆墨難以形容、劣跡斑斑的大少爺,
還被冷落、被約法三章、被敬而遠之,怎樣看都虧大了啊!
但她偏偏就是忘不了這個前世和她拚得你死我活的傢伙,
在她最危急的時候,竟不顧自己的性命救走了她,
雖然最後雙雙仍難逃一死,但也回到一切災難都還沒發生時。
這次她想保住秦家、保住爹娘,也想保住牧家、保住他……
在命運的齒輪前,她的通透和苦心顯得微不足道,
事情仍在歷經層層轉折後,絕然地奔往惡夢般的彼端。
她一邊力挽狂瀾,一邊展開「馴夫計畫」,
停止他的後援、收編他的心腹、擊潰他的放肆,
牧斐總算懂了──惹到秦無雙,最後人生只會殘留下寂寞……
但她如此大費周章整治他,究竟圖的是什麼?
作者簡介:
熹薇
筆名意為早晨的陽光,希望自己能夠像朝陽一樣積極向上,也希望自己能夠像陽光一樣照亮別人。
85後宅女,漢族,自由職業者,生於魚米之鄉,現居於上海。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劫法場
太平三年,秋。
汴都西市口處,法場周圍擠滿了看熱鬧的老百姓。
「這般模樣的女子竟要被砍頭,真是作孽啊!話說,她到底犯了什麼罪?」祁宋律法雖嚴,但對女子而言,若非十惡不赦之大罪,一般不會問斬。
「你竟不知?她乃汴都富商秦家才貌雙全的三房嫡女,秦無雙。唉,她哪是犯了什麼罪,不過是被家族連累的。」
那人恍然大悟。「我想起來了,富商秦家!說的可就是他們家的藥行……上貢的保胎藥出了問題,導致皇后娘娘一屍兩命?」提及皇室,那人刻意壓低了聲音。
另一人也低聲道:「正是他們家。」
「不過我聽說,...
太平三年,秋。
汴都西市口處,法場周圍擠滿了看熱鬧的老百姓。
「這般模樣的女子竟要被砍頭,真是作孽啊!話說,她到底犯了什麼罪?」祁宋律法雖嚴,但對女子而言,若非十惡不赦之大罪,一般不會問斬。
「你竟不知?她乃汴都富商秦家才貌雙全的三房嫡女,秦無雙。唉,她哪是犯了什麼罪,不過是被家族連累的。」
那人恍然大悟。「我想起來了,富商秦家!說的可就是他們家的藥行……上貢的保胎藥出了問題,導致皇后娘娘一屍兩命?」提及皇室,那人刻意壓低了聲音。
另一人也低聲道:「正是他們家。」
「不過我聽說,...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自序
第一章 劫法場
第二章 重生
第三章 沖喜
第四章 談條件
第五章 怎麼是妳
第六章 下馬威
第七章 管教
第八章 眾樂樂
第九章 節節敗退
第十章 下狠藥
第十一章 裝什麼裝
第十二章 說明白
第十三章 相敬如賓
第十四章 訂親
第十五章 有恩必報
第十六章 吃飛醋
第十七章 委以重任
第十八章 結拜
第十九章 阻止
第二十章 眾矢之的
第二十一章 收拾
第二十二章 不敢相信
第二十...
第一章 劫法場
第二章 重生
第三章 沖喜
第四章 談條件
第五章 怎麼是妳
第六章 下馬威
第七章 管教
第八章 眾樂樂
第九章 節節敗退
第十章 下狠藥
第十一章 裝什麼裝
第十二章 說明白
第十三章 相敬如賓
第十四章 訂親
第十五章 有恩必報
第十六章 吃飛醋
第十七章 委以重任
第十八章 結拜
第十九章 阻止
第二十章 眾矢之的
第二十一章 收拾
第二十二章 不敢相信
第二十...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