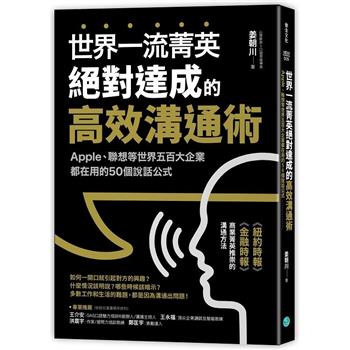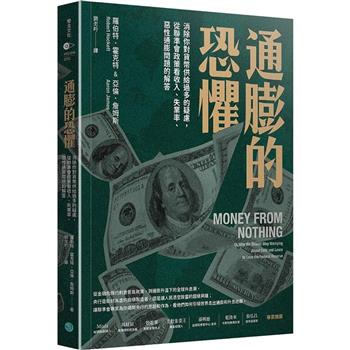第十一章
男人見槿嫿出來了,吐了一口痰,張嘴就罵道:「你們這破店賣的什麼破玩意兒,爺的女人用了你們的東西,臉都毀了。破店!操你娘的破店!操你娘的奸商!」
那些到店裡買東西的女客,此時要不躲開,要不離開,只有幾個膽大的還敢待在一旁默然圍觀。
槿嫿鎮定地走上前來,客氣地對男人道:「我是這兒的掌櫃,這位客官有什麼事儘管和我說,別嚇到了這些姑娘。」
「呵!爺找的就是妳。」男人用力地把女人扯到了槿嫿面前,指著女人的臉道:「好好瞪大妳的一雙狗眼看看,爺的女人原本長得跟朵花似的,用了妳這黑店的玉容膏,現在醜得跟癩蝦蟆一樣。」
他這話還沒說完,門外就已圍過來了不少人。
槿嫿料他是故意來找碴的,不卑不亢道:「這位客官說話可得有憑證,我家的玉容膏賣了這麼長時間,有口皆碑,還從未出現像貴夫人臉上這樣的情況。」
「憑證?爺女人的臉就是憑證,難不成這臉還是假的?」男人又噴著口水道。
槿嫿瞅了瞅那女人的臉,的確不像是妝扮上去的。
男人看向了圍觀的人,像展示什麼寶貝一樣,掐著女人的臉忽左忽右,大聲嚷嚷道:「大夥瞅瞅,都瞅瞅,我女人的臉用了這店裡的東西全毀了。」
圍觀的人見那女人臉腫得厲害,有同情的,有害怕的,有猜疑的,也有不以為然的。
正眾說紛紜中,一個圍觀的女人挺身站了出來,尖著嗓子道:「我之前也用過這家店的東西,塗完後臉又紅又癢的,當時還以為是我吃錯了東西,敢情是這家店的貨當真有問題。」
「原來還有人跟我一樣,我也是用了後發癢來著,只是看見別人用了沒事,一直沒往心裡去。」又有一個女人道。
這兩個女人煞有介事地說完後,輿論的風向瞬間一邊倒。
不僅有人開始大聲指責槿嫿賣害人的東西,更有人大義凜然地跳出來,說要幫那男人和女人討回公道,砸了槿嫿的黑店。
男人見自己占了上風,洋洋得意地對槿嫿道:「聽聽,可不止爺一個人說妳這家店的貨有問題,今天妳要不給爺一個交代,爺跟妳沒完!」
槿嫿見狀,心裡更加確定她是被人算計了,剛才說話的那兩個女人八成也是他的同夥。
而那些圍觀的百姓,都是看熱鬧的不嫌事大,又容易受人煽動,「美人妝」乍然崛起,眼紅的人不少,裡邊保不准還有同行想趁機落井下石。
槿嫿的心怦怦亂跳,手心也開始冒冷汗,但她知道她若表現出「怕」來,那些想看笑話的人只會更加得意,她豈能遂了他們的意?
她強作鎮定地對那流氓道:「你想要什麼交代?」
「賠錢!」
回答得這麼乾脆,果然是有備而來。
槿嫿冷笑。「多少?」
「一千兩銀子。」說完,那男人眼裡閃過了一絲狡黠和陰狠。
槿嫿聽到那流氓說要一千兩,瞥了一眼他身邊的女人,笑道:「這位爺就算想訛錢,也該有個限度,一千兩,按現今的行情,就算是把這姑娘剝光賣掉,也不超過六十兩吧。」
那流氓頗有些惱羞成怒地道:「操你娘的奸商,爺怎麼訛妳了?爺這些年供她吃、供她喝、供她穿不用錢嗎?如今臉腫成這樣了,叫人怎下得了嘴,一千兩是便宜妳了。」
槿嫿又是一陣冷笑,毫不退卻道:「我棠槿嫿向來不惹事,但也不是個怕事的。玉容膏自上架後賣出沒有十幾萬份,也有個幾萬份,要是這香膏真有問題,我這店早關了,哪輪得到你上門討要說法?」
她厲眼掃在了那流氓還有適才說話的那兩個女人臉上,一字一字道:「你以為找幾個人演這麼一齣戲,又煽風、又點火的,我就會怕了,就會把錢掏出來?趁早死了這分心,我棠槿嫿不吃這一套。」
「好個不見棺材不落淚,老子管妳是糖還是鹽,今天妳要不把錢拿出來,老子就砸了妳的『美人妝』。」
那流氓說著,捲起了袖子,作勢就要砸貨架上的貨品。
「好,有種你就砸,我就坐在這兒看著你砸!」槿嫿說著拉了一張椅子甩手坐了下來。「但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只要敢動手,我就立馬叫人去報官,我倒要看看進了衙門,在王法面前,你這個『老子』有多『老子』!」槿嫿說完,朝站在一旁的阿福使了個眼色。
那流氓聽到槿嫿說要報官,眼一瞇,心一橫,還是抓起了木架上的白瓷盒往地上砸去。
「千人操的奸商,老子砸了妳這爛臉的東西是給百姓除害,縣太爺見了只會誇我!」
那流氓叫嚷著,表情愈發猙獰,伸手又砸掉了好幾盒胭脂,不一會兒,地上便是一堆破碎的瓷片和散落的紅色脂粉。
阿福已偷偷地溜出去報官。
槿嫿往地上看了看,又是氣憤、又是心疼,這些都是她的心血,是她一點一點置起來的。
她示意另外兩個男夥計上前去制止那流氓的行動,但那兩個細胳膊細腿的夥計哪是這個流氓的對手,非但制不住流氓,反而被那流氓推到了牆上、架子上。
實木做的長架子受了重擊,大幅度地晃蕩了一下,大有要倒的趨勢。
架子若倒了,滿架的貨保不住是一回事,傷到人可就太罪過了。
槿嫿下意識地衝過去扶。
流氓見她過來扶,更用力地一腳踹在架子上,放在架子邊緣的貨因為傾斜,「砰」地墜在了地上,摔得個個粉碎。
槿嫿在這一瞬間已顧不得心疼,她腦海裡只有一個念頭──不能讓架子倒了。她甚至沒來得及想到,架子若這般倒下來,第一個砸中的人一定就是她。
就在這危急緊要的關頭,得到消息的穆子訓和宋承先趕來了。
他們一個箭步衝了上去,把架子扶正了。
那個流氓見來了兩個男人,心裡有些虛,這心一虛,說話聲音便更大更囂張。
「爺的女人用了這家店的東西臉都爛了,這個賤女人,十八里街最大的奸商還敢反咬爺一口,爺今天就要替天行道,為民除害!」
「一個大男人欺負一個女人算什麼東西?」
宋承先轉身打量了一下眼前這個流氓,忽發出一聲冷笑。「嘖嘖!這不是陸爺嗎?」
「你認識他?」槿嫿扶著腰道。
剛才那一扶,她的腰似是閃到了,很不舒服。
「陸爺可是老江湖了,能請到陸爺親自出馬,看來是個大主顧。」宋承先似笑非笑地說著。
有點腦子的人都聽得出宋承先是在暗示這位「陸爺」是被人收買了,特意跑到「美人妝」來鬧事的。
那流氓也認出了宋承先,只是沒料到宋承先會出現在這裡,更沒料到宋承先會把他的老底抖出來。
眼睛一轉,他乾脆死咬宋承先是在胡說八道,還故意挑撥道:「堂堂知安堂的少東家原來是這女奸商的姘頭,人家親老公都還沒急,你倒比他急。」
「瞎了你的狗眼!這是我家娘子的義兄、我的義舅,容得你在這兒滿嘴噴糞。」穆子訓破口大罵。
他今天到宋承先店裡去小坐,兩人還沒說上幾句話,便有個夥計跑進來,說是「美人妝」門口圍了好多人,似是出了什麼事。
穆子訓一聽這還得了,趕緊和宋承先趕了過來。
那流氓怎會想到宋承先和槿嫿之間還有這麼一層關係,一下子不知如何還嘴了,便又開始嚷嚷「美人妝」店大欺客,出了事只會仗著人多欺負人。
他嚷嚷著、嚷嚷著,衙門接到報案,派人來了。
那流氓遠遠地見官差往這邊走來,前一刻還理直氣壯地說要和槿嫿對簿公堂,在縣太爺面前評出個理來,後一刻卻拉了那爛臉的女人,逃也似地跳窗走了。
離開前他惡意地推了槿嫿一把,害得槿嫿為了躲他那一推,向後一閃,跌到了地上。
然後他和那爛臉的女人跳窗逃走時,也把槿嫿擺在窗下茶桌上的上好紫砂茶壺和茶杯踏碎了。
「美人妝」今日損失慘重,槿嫿的心都在滴血。
「娘子!」穆子訓扶起了槿嫿,恨自己剛才走了神,沒及時阻止那流氓推槿嫿。
槿嫿站了起來,見流氓一下子跑得沒了影子,顧不上身子疼,指著窗口的方向大罵。「狗娘養的,有種別跑呀!」
她平日裡甚少罵「娘」,這會兒吐了一句髒,心裡倒痛快──有些人就是活該被人問候「娘」的。
槿嫿出了一口惡氣,扭過頭來,見圍觀的人還未散去,正指指點點地說些什麼。
她拍了下身上的灰塵,正色道:「各位街坊鄰居,各位貴客可都看見了,這流氓就是想訛錢的,見官差來了便一溜煙跑了,明擺著作賊心虛。我棠槿嫿在這兒向大家保證,我們『美人妝』的貨絕對是沒有問題的,大家盡可放心購買使用。要是誰動什麼歪心思,『美人妝』也不怕事,縣衙府內自有公道。」
適才那幾個替流氓幫腔的,似是被槿嫿的氣勢嚇到了,都畏畏縮縮地從人群裡逃出去。
官差來了,圍觀的人漸漸散了。
店裡被流氓弄得一團糟,這一日的生意是做不下去了。
穆子訓去招待官差,宋承先則替槿嫿招呼夥計們清理店鋪。
槿嫿走到了那兩個被流氓打傷的夥計面前道:「你們兩個傷在哪兒了?我尋個大夫給你們瞧瞧。」
「不煩勞夫人了,只是些皮外傷。」一個夥計道。
「是,不打緊的,塗些藥酒就好了。」另一個夥計也道。
「這怎麼行呢!這臉還在流血呢!」槿嫿皺了皺眉,堅持要小菊去請大夫。
這附近便有位姓吳的大夫,不消多時,吳大夫便提著診箱來了。
吳大夫先給兩位夥計看了傷,說好在只傷到了皮肉,沒傷到內裡,塗上半個月的藥,傷口就會好得差不多了。
此時,穆子訓送走官差後進來了,見槿嫿把手伸到腹部揉了兩下,神色有些不自在,攔住了正要回去的吳大夫道:「大夫,我家娘子剛才跌了好大一跤,你也給她看看。」
「我沒事,就是氣得有些胃疼,剛才又閃了下腰,明兒就好了。」槿嫿道。
她素日裡若氣極了,或者緊張起來,胃就容易不舒服,想來也是小事,自認是不必看大夫的。
穆子訓卻堅決地道:「都把吳大夫請來了,就順道看看吧!我瞧娘子的臉色也不大好。」
「是嗎?都是那潑皮流氓氣的,害得我到現在氣都還順不過來。」槿嫿一想起讓那流氓逃了,不只氣得胃疼,呼吸不暢,連頭都痛了起來。
「夫人請坐吧!我先給妳把把脈。」吳大夫道。
槿嫿只好在穆子訓的攙扶下坐了下來,伸出左手給大夫搭脈。
大夫搭了左手,又搭了右手,沈著地道:「倒無甚大礙,就是有些動了胎氣,我給夫人開幾帖養胎安神的藥,吃下去便好了。」
「有勞大夫了……」槿嫿下意識地應著,見穆子訓站在一旁驚得目瞪口呆,瞬間醒悟了過來,按住了大夫的手道:「你說,你剛才說我動了什麼來著?」
「胎氣。」吳大夫被她嚇了一跳。
「啊?你是說……我、我有孕了……」槿嫿激動得說話都結巴了起來。
吳大夫拿開了槿嫿的手道:「夫人已有孕三個月。」
「三個月……」她居然已經懷孕三個月了!槿嫿簡直不敢相信,然後又覺得自己太過糊塗。
她曾經小產過,後來月事便不太準,春節時姚氏無意間和她提起孩子的事,她還尋思著等年過了再找大夫開些藥調理身子,只是事情一多,她又把這事擱下了。
「吳大夫,你確定我……我真的懷上了?」
*欲知精采後續,敬請期待1/5上市的【文創風】915《安太座》下。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安太座(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75 |
二手中文書 |
$ 205 |
中文書 |
$ 205 |
文學作品 |
$ 205 |
大眾文學 |
$ 205 |
Literature & Fiction |
$ 234 |
古代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安太座(下)
不少人說她是掃把星,剋父剋母剋公公,日後也會剋死婆婆和相公,
可夫君卻說,他如今窮了,她還願意跟著,是打著燈籠也找不著的好媳婦,
而且她生不出孩子,他也堅決不納妾,得夫如此,她還有何好求的?
眾人皆知過年安太歲為的是祈求來年平安、事事順利,
殊不知,安太座對一個男人來說,重要性可是不相上下的,
這部分,棠槿嫿就不得不稱讚一下自己的夫君穆子訓了,
畢竟他可是把整個人都給了她,娘子說的話對他而言那就是聖旨,
她讓下田他就扛起鋤頭,叫他考功名他二話不說立即發憤苦讀,
雖說他對經商一竅不通,是世人眼中的敗家子,可那又如何?
眼下不是還有她嗎?她腦子轉得快,深知自古以來女人的錢最好賺,
於是,她開了間專賣胭脂水粉的店鋪「美人妝」,生意果然大好,
夫君只要繼續疼她、寵她、尊重她,其他鶯鶯燕燕皆不入眼,她便足矣,
至於重振家業這種小事就交給她吧,她定會讓所有冷嘲熱諷的人閉上嘴!
作者簡介:
月小檀
女,天秤座。園藝愛好者,亦好文字,常覺養花種草比寫作更令人身心愉悅。認為世間的寫作者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給讀者造夢,一種是讓讀者更加清醒。
章節試閱
第十一章
男人見槿嫿出來了,吐了一口痰,張嘴就罵道:「你們這破店賣的什麼破玩意兒,爺的女人用了你們的東西,臉都毀了。破店!操你娘的破店!操你娘的奸商!」
那些到店裡買東西的女客,此時要不躲開,要不離開,只有幾個膽大的還敢待在一旁默然圍觀。
槿嫿鎮定地走上前來,客氣地對男人道:「我是這兒的掌櫃,這位客官有什麼事儘管和我說,別嚇到了這些姑娘。」
「呵!爺找的就是妳。」男人用力地把女人扯到了槿嫿面前,指著女人的臉道:「好好瞪大妳的一雙狗眼看看,爺的女人原本長得跟朵花似的,用了妳這黑店的玉容膏,現在醜得...
男人見槿嫿出來了,吐了一口痰,張嘴就罵道:「你們這破店賣的什麼破玩意兒,爺的女人用了你們的東西,臉都毀了。破店!操你娘的破店!操你娘的奸商!」
那些到店裡買東西的女客,此時要不躲開,要不離開,只有幾個膽大的還敢待在一旁默然圍觀。
槿嫿鎮定地走上前來,客氣地對男人道:「我是這兒的掌櫃,這位客官有什麼事儘管和我說,別嚇到了這些姑娘。」
「呵!爺找的就是妳。」男人用力地把女人扯到了槿嫿面前,指著女人的臉道:「好好瞪大妳的一雙狗眼看看,爺的女人原本長得跟朵花似的,用了妳這黑店的玉容膏,現在醜得...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尾聲
番外 靈兒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尾聲
番外 靈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