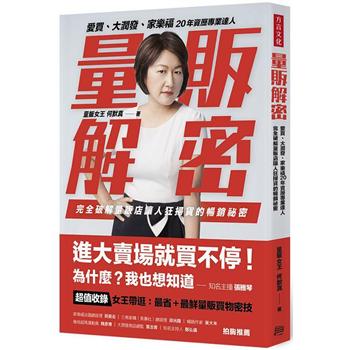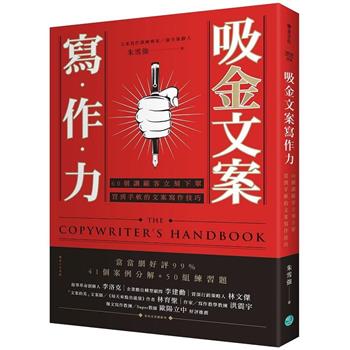第一章
臘月十一,滴水成冰。
午後天氣晴好,長安城外的官道上,行客趁著好天氣趕路,忽地有車馬聲轆轆而來。轉頭回望,車隊見頭不見尾,好事者閒來數了,竟有整整二十輛,不疾不徐地往延慶門去。
茶肆裡幾個閒坐的茶客停下交談,紛紛探頭張望,好奇是哪家的富貴之人,竟有如此派頭?
為首的青壁馬車上鐫刻著一隻銜珠金蟾,約莫是哪家世代相承的族徽,青灰色車簾被人掀起一角,露出個十五、六歲的小公子來,面如冠玉,一本正經地朝著車隊前行的方向望去。
「姑姑,就快到了。」
車輪輾過三兩枯枝,發出清脆的聲響,冷風順著窗子灌了進去,小公子隨即放下簾子,鑽回了馬車裡。
外頭天寒地凍,車裡置了暖爐,很是舒適。
他搓搓手,捧起婢子早就備下的手爐,笑道:「遠遠已能望見延慶門,再過半刻鐘的工夫便能到了。」
沈箬頷首,從元寶手裡接過香匙,舀起些微辟寒香,置於香爐之中,白霧騰起,一時間馥郁宜人。
「姑姑省著些用,父親好不容易才得了一抔,可抵萬金,妳這一路就用去了大半。」
沈箬微微轉過頭,似乎很是不信這話竟是從他口中說出。「沈綽,沈家這般富貴門戶,怎地養出你這麼個筆筒裡看天的來?不過是香料罷了,大不了讓哥哥再想法子去弄就是。」
「姑姑!」
怎麼可以說他見識短淺,何況這也不是什麼普通香料。
傳說辟寒香乃丹丹國所出,有抵禦寒氣的作用,即使有錢也難以輕易求得,就這一小抔還是沈家行商機緣巧合求來的,一應給了家裡的姑娘。
沈綽心疼得捂住胸口,望向自家姑姑,卻見她半分也不理會自己,兀自捧著手爐打瞌睡,漸漸起了細微的鼾聲。
他輕嘆一聲,轉身從身後捧過一床薄毯,輕輕搭在沈箬胸前。這幾日奔波,也難怪她入睡如此輕巧。
春闈將至,如果等到過了年再來,恐怕耽誤了課業,因而便由姑姑帶著他,趕在年關前入長安,也好早些適應此處氣候。
只是單為著這一樁事,倒也不必累得沈箬將揚州的一應財物清點,事無鉅細地帶來長安。
只因沈箬婚事近了,許的正是長安城裡炙手可熱的人物,臨江侯宋衡。
這樁婚事說來也是個巧合。
沈家世代行商,經年積累,已是杭州城裡第一大富戶,出行坐臥,用的皆是最上等。至沈箬兄長沈誠這一代時,因厭倦「士農工商」裡,商人排在最末等,抹著眼淚將幼子沈綽送往揚州薛炤薛大儒的門下,指望有朝一日鯉躍龍門,好把沈家變成世代大族。
姑姪兩人不過相距歲餘,自幼一起養在沈誠膝下,感情甚篤。一個被送往揚州,另一個哭鬧不止,只得拖拖拽拽,一起送到了揚州。
沈綽還算用功,得了薛大儒青眼,連帶著常送魚羹來的沈箬,也跟著薛大儒學了幾筆字。
如此不過四、五年光景,樹大招風,杭州太守起了謀奪沈家家業的心思,五十多歲的老頭領著人上門求娶沈箬,還將沈誠拘去坐了幾日牢。
沈箬那時心急,拎著一碗豆腐魚湯求到了薛炤面前。向來愛笑的丫頭哭哭啼啼了半日,薛炤一時犯了糊塗,竟命人傳話出去,說是沈箬早已聘給了遠在長安的宋衡。
杭州太守自然不敢跟扶立新帝的臨江侯對著幹,恭恭敬敬地把人放了,還覥著臉討喜酒喝。
待諸事落定後,薛炤索性將錯就錯,寫了封十頁的長信送往長安,沒幾日便親往杭州,當著沈家族親的面,與沈誠互換兩人庚帖,定下了一樁婚事。
沈家無人見過那位宋侯爺,只是聽來往長安的人提起過幾句,算起來比沈箬大了六歲,實在是老了些。
可沈箬只說了這麼一句話──
「總歸好過那太守大人。」
如此一來,這樁婚事倒也不算令人難以接受,畢竟六歲和三十六歲,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想到這裡,車駕忽地一頓,隨即便停在原地不動。
沈綽收回思緒,復又掀起簾子張望一眼。
已到延慶門下,車伕和幾個穿著甲胄的守城兵士交涉幾句,隨後輕叩車壁,垂手道:「姑娘、公子,已到延慶門下,還需文牒一用。」
沈綽伸手在坐凳下的暗格一按,取出文牒遞了過去,車伕稱是轉身。
大約是說話聲驚醒了沈箬,她按按雙眼,夾著濃重的鼻音問道:「出什麼事了?」
「不過是要文牒罷了,此去永崇坊大約還要些時候,姑姑可再睡會兒。」
沈箬擺擺手,坐直身子,由著銅錢為自己按壓脖頸。「言叔早幾日便來了書信,說是早備好了宅子,雖說比不得揚州住的,不過已是眼下能買到最大的了。你到時可別鬧。」
沈綽是個讀書人,對姑姑這種奢靡的作風甚是有些不齒。「君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我怎會在意這些?」
「子約言之有理。」沈箬一抬手,又往香爐裡添了一勺辟寒香。
說是一派,做的卻是另一種模樣,沈綽索性閉上了眼,不去看這揮金如土的做派,卻聽車外有個稚嫩的聲音響起。
「尊駕可是杭州沈家姑娘?」
元寶擱下手裡的活計,掀起車簾一角,將外頭風光瞧得一清二楚。因著車隊冗長,吸引不少人圍攏一處,探著頭往車裡張望,意欲窺探一二。
馬車正前方站著個總角小童,神色倨傲地又喊了一遍。「尊駕可是杭州沈家姑娘?」
「來的是什麼人?」
小童幾步走到車駕下,壓低了聲音道:「我家公子知姑娘今日入城,特命我在此等候。」
他答完話,從袖中掏出一封手書,經由元寶,遞到了沈箬手上。
花箋之上,只簡簡單單寫了一行字:知姑娘入城,特命玉筆相迎。
銅錢跪坐在一側,瞥見落款上留的名字,抿著嘴笑道:「原來是姑爺的人。」
「別胡說,姑姑還沒過門,傳出去像什麼樣子?」沈綽趕緊道。
沈箬收好字條,妥帖地置於袖中,揚聲道:「元寶,請玉筆小哥車上坐。」
車內為女眷,沈綽雖是男子,可畢竟是本家內姪,玉筆自然不敢入內,只是翻身坐在車伕另一側,兩條腿一晃一晃的。
恰巧守城的衛士也翻閱過文牒,略作檢查便抬手放行,車隊施施往永寧坊去。
「沈家姑娘,我家公子念著你們人生地不熟,特意在永寧坊替你們購置了一處宅子,這便帶你們過去。」
「不……」
沈綽還未說完,就被沈箬一把捂住了嘴,笑道:「難為侯爺破費。」
玉筆衝著車伕指路,心中暗自替自家公子不平。
先前便曉得公子定了親事,商賈之女粗鄙,今日一見,果不其然,連婢子的名字都是銅錢、元寶之流,可見滿身銅臭氣。
永寧坊離得不遠,過了延慶門,穿行兩條街巷便到了。
馬車停在一處四進的宅子門前,玉筆跳下車,回身喊了一句。「沈家姑娘,到了。」
銅錢和元寶一人捧著梅花凳下了車,另一人掀起車簾,小心扶著沈箬。
待她裹著幾層夾襖艱難地下了車,這才輕舒一口氣,打量起宋衡為她準備的宅子來。此處還算僻靜,只是牆體有些斑駁,一看就是上了年頭,牆角探出一枝紅梅來,吐著紅蕊。
還算上佳,不過到底不盡如人意。
玉筆在一旁細細介紹。「公子費了不少銀錢,可算是尋著這一處。再往外走走便是東市……」
他話音未落,跟在後頭下車的沈綽還未站穩腳跟,便不自覺驚呼。「怎會有如此小的宅院!」
玉筆的臉色一時間如醬得久了的豬肝一般青紫,元寶和銅錢在一旁捂著嘴偷笑。
「沈綽。」沈箬瞪了他一眼。這種話怎好亂說?「長安地貴,不比揚州地僻。」
沈箬大概明白了,她這位未婚夫婿大約是個兩袖清風的好官,因而囊中羞澀,可又擔心自己初來沒個落腳點,實在是用心良苦。
思至此處,她反手解下腰間別著的一個荷包,裡頭裝著些金瓜子,還能值幾個錢。「玉筆小哥,勞侯爺如此破費。這些金瓜子你拿著,替我轉交侯爺,這宅子只當是我託侯爺買的,餘下的銀錢不日便送去府上。」
玉筆皺著一張臉不收,卻被沈箬一把塞進了懷裡,面前的女人一改先前的猶疑,吩咐下人搬弄行李,提起裙襬便往裡走。
當真是個奇怪的女人。
那位奇怪的女人並不知他人所想,只覺得宋衡雖年紀大了些,可還算體貼,應當是位好夫君,日後成了婚,她更該努力賺錢,補貼家用。
不過這宅子到底還是小了些,單是帶來的一家子細軟和下人便不夠住。沈箬揮手招來銅錢,同她吩咐道:「同言叔知會一聲,我就住永寧坊了。」
隨後又將一把銅鑄小鑰匙交給元寶。「去取些銀錢,問問附近是否有賣宅子的人家,一併買了,再找人將幾處宅子打通倂成一處。」
*欲知精采後續,敬請期待1/26上市的【文創風】921《夫人萬富莫敵》上。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夫人萬富莫敵(上)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夫人萬富莫敵(上)
國家大事有侯爺擔著,
她開幾家香粉鋪和櫃坊,不只幫忙經營市井人脈,
還能當個小富婆,財源滾滾來~~
身為杭州第一大富戶家的小姐,沈箬不愁吃穿,撒錢更是不手軟,
可她沒想到,有一天竟要為自己的婚事發愁!
杭州太守欲謀奪沈家家業,五十幾歲的老頭上門求娶她,
這般不懷好意,她會嫁他才怪呢!但對方是官,不嫁總得拿出理由吧?
她求助於在朝中頗有威望的恩師,迅速就解了這燃眉之急,
恩師不知用什麼方法,竟讓堂堂臨江侯宋衡答應與她的婚事!
說起宋衡,那可是能在朝堂呼風喚雨,連皇上都要尊敬三分的人物,
她滿心好奇,趁姪子要去長安備考,她也順道去探探這位素未謀面的未婚夫。
孰知初到長安,就聽說宋衡正為了江都水患一事忙得焦頭爛額,
朝廷急需賑災物資和銀兩,但各大富戶紛紛裝窮不願伸出援手。
對沈箬來說,能用銀子解決的都不是大事,
況且這回撒錢還能行善舉、積功德,怎麼說都是穩賺不賠的生意嘛!
作者簡介:
顧匆匆
一個相信所有人都不平凡的人,僥倖能拿筆創造出一、兩個世界。人生匆匆,唯愛長留,希望能在短短幾十年裡,寫夠我所嚮往的世界。
章節試閱
第一章
臘月十一,滴水成冰。
午後天氣晴好,長安城外的官道上,行客趁著好天氣趕路,忽地有車馬聲轆轆而來。轉頭回望,車隊見頭不見尾,好事者閒來數了,竟有整整二十輛,不疾不徐地往延慶門去。
茶肆裡幾個閒坐的茶客停下交談,紛紛探頭張望,好奇是哪家的富貴之人,竟有如此派頭?
為首的青壁馬車上鐫刻著一隻銜珠金蟾,約莫是哪家世代相承的族徽,青灰色車簾被人掀起一角,露出個十五、六歲的小公子來,面如冠玉,一本正經地朝著車隊前行的方向望去。
「姑姑,就快到了。」
車輪輾過三兩枯枝,發出清脆的聲響,冷風順著窗子灌了...
臘月十一,滴水成冰。
午後天氣晴好,長安城外的官道上,行客趁著好天氣趕路,忽地有車馬聲轆轆而來。轉頭回望,車隊見頭不見尾,好事者閒來數了,竟有整整二十輛,不疾不徐地往延慶門去。
茶肆裡幾個閒坐的茶客停下交談,紛紛探頭張望,好奇是哪家的富貴之人,竟有如此派頭?
為首的青壁馬車上鐫刻著一隻銜珠金蟾,約莫是哪家世代相承的族徽,青灰色車簾被人掀起一角,露出個十五、六歲的小公子來,面如冠玉,一本正經地朝著車隊前行的方向望去。
「姑姑,就快到了。」
車輪輾過三兩枯枝,發出清脆的聲響,冷風順著窗子灌了...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文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