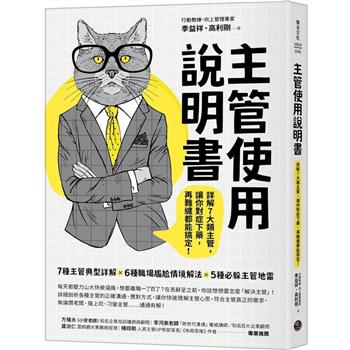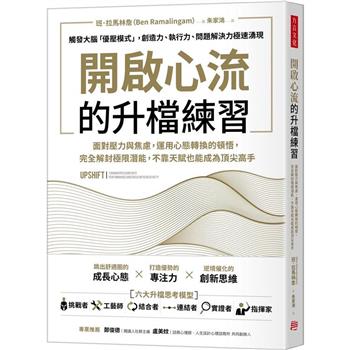第二十一章
「殺千刀的啊!好端端的人就是吃了他們家的藥才沒了,可憐我家男人,昨兒個夜裡還能說笑,今早就斷了氣。」
婦人聲音洪亮,扠腰立在門邊吵嚷,腳邊還擺著一具屍體,白布覆面,只露出一雙腳。
沈箬行至門邊,街坊成群湊在一旁,對著門裡的人指指點點,似是認定了他們的藥材有問題。至於太守府的人,不過裝個樣子,站在原地看著鬧劇發生。
「若是我家的藥吃死人,妳倒是拿出證據來,帶個死人過來算怎麼回事?」玉筆人雖小,可嘴巴倒是厲害,守在門邊硬是不讓人前進半步。「無憑無據,小心我們告妳誹謗,拖去官府打板子。」
婦人撒潑慣了,哪裡能被個小子鎮住,不依不饒道:「黃口小子,我不同你說,去把你們當家的找來,自然有人做主!」
玉筆還要再說,沈箬幾步上前,拍拍他的肩膀。
先不論這事究竟是什麼情況,眼下這麼多人圍著,只怕會耽誤之後開礦之事。
「夫人,家中的藥材都是有大夫看過的,溫家先祖以仁義立身,這種草菅人命的事,溫家自然做不出來。」
婦人聞言,自當她在推託,一屁股坐到地上,伏在屍體上,哭得抑揚頓挫。「吃死人的藥,一句仁義就想把我們打發了,真是欺負我們窮苦人家,連苦都沒地方說去。你個死人,怎麼就這麼去了,看著我被人欺負。」
沈箬冷眼旁觀,不怪她冷血無情,這婦人哭得肝腸寸斷,分明一滴淚都未曾有,單是打雷不下雨,一看便是來鬧事的。只是不知為何,太守府的人竟然半點反應也無。
「夫人這可說錯了,青天白日,若真有苦處,何不去太守府一一言明?」她掃過任憑此事發酵的太守府兵衛,若非穿著制式統一的服裝,只怕也要把他們當作圍觀人群。
「仵作手起刀落,不出一刻鐘,如何死的、何時死的,皆有定數,誰也抵賴不得不是?」
藥材裡有沒有混入烏頭草,她最清楚。交接時都有明細登記在冊,也有兩方人各自驗過,銀貨兩訖。如今即便真是藥材吃死了人,那也該去找抓藥的鋪子,而非找到這裡來。
沈箬料定她是來鬧事,氣定神閒地指點她去太守府告狀。
誰知那婦人猛地起身,帶得白布掀起一角,露出屍體慘白的臉來,兩頰凹陷,確實是吃了烏頭草的樣子。
「哪裡來的小妮子,人都死了,還要他挨上一刀,把腸子剖出來看!」
不肯去官府,那更是有蹊蹺。沈箬提裙跨出門檻,指著那些兵衛道:「三歲小兒都知,有冤自當去府衙,夫人莫非不認得太守府在何處?今日趕巧,這幾位大哥看著像是太守府的人,正好帶著夫人一同前往。」
婦人氣急,一時語塞。面前的姑娘句句緊逼,似乎是看破什麼,心下不覺有些退縮。
她本是城東一戶潑皮,和這男人無媒姘居,整日遊手好閒。昨日三更天,有人深夜造訪,遞給她一袋黃金和一張田契,足夠日後花銷;作為交換,須得毒死男人,賴到溫家頭上。
夫妻之恩,抵不過貧賤之苦。她思及男人酒後時常拳腳相向,一橫心把烏頭草放進水壺裡,人就這麼涼了。
商戶間搶生意是常事,那人的穿著像個生意人,故而婦人為著一袋金子,大清早鬧上了門。原本見著一個小姑娘出來,她還心中一喜,丫頭片子臉皮薄,定然能再訛上一筆,誰知卻遇上個難纏的。
沈箬見她不回答,又道:「夫人若不願意去太守府,那我去喊冤便是。」說著便要往外走。
婦人驚覺,太守府自然去不得!那人說了,太守那裡自會有人打點,只須她纏住溫家人,讓他們不得出府即可。
她心中一橫,面前的姑娘身形瘦弱,自然比不得她,何況身後還有太守府的人,足夠幫她攔著那些下人。
「你們不把我們當人看,就別怪我們不客氣!」
她手中不知何時握了一塊尖石,猛地撲向沈箬,死死扼住了她,拿尖石抵在沈箬頸間,獰笑著道:「小丫頭的脖子可是細得很啊!」
只是思遠善使暗器,看到變故發生,立時從袖中掏出一枚飛刀,直奔婦人肩胛而去。
只聽一聲慘叫,沈箬脖頸間有血絲滲出,被思遠一把拉回身後。
「大膽!竟敢傷人,給我捉了!」思遠怒道。
不作為的兵衛此時方如夢初醒,看著地上疼得打滾的婦人,拔刀要拿下沈箬他們,一時間便廝打在一處。
沈箬被思遠護著退後,心中卻越發不安。這婦人也好,兵衛也罷,像是串通一氣而來,沒罪也要按個罪名拿下他們。
可身分是假的,初來也不曾得罪人,是誰會花這麼大的力氣來對付他們?
何況眼下宋衡遲遲不歸,不曉得是不是遭了什麼黑手?
「思遠,公子還沒消息?」
思遠護著她,連連搖頭。
直至他們退至門內,那些兵衛不敢硬闖拿人,只是守在門口,似乎只是限制他們出府。
婦人依舊在門前叫嚷,此時更是多加了一條大庭廣眾之下殺人的罪名。
此番來的人甚多,團團圍住整個宅院,沈箬一時成了甕中之鱉。她把披風攏了攏,這下同宋衡斷了聯絡,並非好事。
「玉筆,想法子出去找公子,把事情告訴他,讓他不必急著回來。」
他們不敢進來,自然是有所忌憚,與其把宋衡一起攪進來,倒不如留個人在外頭想辦法。
玉筆的功夫甚好,趁著不注意闖出去應當不是難事。沈箬上前一步,正要同那婦人說話來轉移注意力,只聽得宋衡的聲音傳來──
「誰敢拿本侯的人?」
話音未落,他還冷哼了一聲,又是先前那個不近人情的臨江侯。沈箬恍惚,這幾日和氣的溫長風果然是錯覺。
那些兵衛見有人來,橫刀去攔。「官家辦案,閒人退散。」
宋衡冷笑一聲,劈手奪了他的刀,在空中一轉,正落在兵衛肩上。「如此辦案,當真可笑。」
那兵衛見他如此,正要開口訓斥,身後的玉劍上前一步,手中握著玄鐵製的令牌,上書「臨江侯」三字。
「臨江侯在此,爾等安敢放肆!」
玄鐵令牌只此一塊,天下還沒有誰有這個膽子敢去冒充臨江侯。想透這一層,眾人雙股顫顫跪倒在地,生怕跪得慢了,這位主子一時不高興摘了他們的人頭。
只是跪是跪了,卻想不通他何時來了廬州,竟半點風聲不露。
宋衡丟了刀,負手朝屍體走近兩步,無甚感情道:「廬州太守既不會斷案,那便歇著吧。玉劍,你去太守府盯著仵作。」他頓了頓,一字一句道:「定要查明死因,別誣衊了好人。」
玉劍領命,帶著幾個機靈的人去抬屍體,順帶要把癱倒在地的婦人一併帶走。
此處正收拾著,卻見沈箬從裡頭跑了出來,裙襬漾成一朵花。宋衡原本怕她嚇著,此時見她神色還算如常,依舊笑意盈盈。
宋衡鬆了口氣,湊近卻瞥到她頸上有傷,皺著眉頭問道:「怎麼傷的?」
還未等人回話,地上的婦人越發怕了。給她金子的人不曾說過會招來臨江侯,此時看著就是要替沈箬出氣,一時間竟失了禁,惹得周圍人捂著鼻子散開。
「玉劍,先賞她一頓板子。」
周圍人抽氣,頭卻埋得越發低了,免得殃及池魚。
沈箬看著,輕嘆一聲,本想著安安穩穩辦事,越不惹眼越好,誰知竟如此高調。宋衡說出臨江侯的身分便罷了,還雷厲風行處置了這些事,落在別人眼裡,只怕又是仗勢欺人,目無法紀了。
她皺皺鼻子,外頭氣味混雜,難聞得很。
「進去說吧。」
宋衡點點頭,與她並肩入內,並不側目去看其他人,只是吩咐玉筆去請大夫。
沈箬擺手,這點傷不必勞動大夫,哪裡就這樣矜貴了?
「不用,我沒事,你不必如此緊張。」
緊張嗎?
宋衡摸摸鼻子,方才聽到玉扇來報,怕她嚇著,特意拋下事情趕回來,卻不想她泰然自若,半點都不怕;之後又見傷口,倒是有一瞬怕她哭出來。
尋常小姑娘,不是被蚊蟲叮咬都會紅了眼圈?怎麼到她這裡,就像是掉了個個兒,似乎不是傷在自己身上一般。
「侯爺?」沈箬喊道。這人怎麼回事,不就是不讓他請大夫,怎麼還不理人了?
宋衡輕咳一聲。「何事?」
「我是想問,侯爺這樣貿貿然便把身分公諸於眾,還如此處罰他人,會不會有些不妥?」沈箬小心謹慎地補充道:「譬如未盡之事?」
先前隱匿身分而來,花了大心思布局,眼下一朝盡毀,不知會不會誤了大事?
「無妨,此舉最為簡單,免於糾纏。」
反正如今礦場位置已然選定,大大方方把身分擺出來,也讓那些人有所忌憚。
宋衡沒有多解釋什麼,只是側目問沈箬。「用過早膳了?」
那婦人來得突然,誰還顧得上吃飯。沈箬搖搖頭,眼下都已巳時過半,這時候用早膳,只怕不大合飲食規矩。
宋衡衝著思遠擺手,要她去廚房取些吃食來。時近正午,吃得多了,只怕影響午膳,到時候亂了脾胃反倒不好。
不過片刻,思遠擎著托盤而來,上頭擺著兩碗薄粥和幾碟小菜,拿來墊一墊胃正好。宋衡起身坐到桌前,一如往日般進食,半點不覺得有異。
往日兩人是兄妹,一起吃飯正常,幾日下來,沈箬也習慣了。
她跟著在對面坐下,握著湯匙喝粥,偶爾還抬眸看看宋衡,一舉一動盡是優雅,當真是秀色可餐。
看得久了,一時忘記往嘴裡餵粥,直到宋衡的碗見了底,屈指在她面前的桌上輕叩。
「再不喝就涼了。」
沈箬猛地回神,怎麼就像那些登徒子一般見色起意呢?她埋頭喝了兩口粥,又聽宋衡說話。
「日後再有急事,三餐也該是頭等重要的事。」
這是在說她忘了時候?
一碗粥下肚,有了些飽足感。沈箬挾了一小筷醋溜蘿蔔絲,細細嚼了嚥下,這才放下筷子同他說話。「今日事出突然,只好先辦事,畢竟人命關天。」
「民以食為天,吃飯也是關天的事。」
宋衡雙目灼灼,說的話也很認真,並非玩笑。沈箬盯著看了兩眼,到底還是敗下陣來,把臉移開去看堂中牌匾。
也是,何必與他爭這些,反正說得沒錯,吃飯也是大事。
沈箬托著下巴靜思,新的礦場已經找到,晨起雖被耽誤了些工夫,可看宋衡的意思,怕是不會留她在廬州,說不準很快就要把她送回揚州了。
果不其然,宋衡道:「今日啟程,恐要行夜路。明日一早,我讓玉劍送妳回揚州。」
好在還多留了她一日。
沈箬點點頭,正準備回去收拾行囊,外頭有人來報,說是陳擎之家眷綁了人前來,有要事面見臨江侯。
「請人進來。」
來者不知是何人,來得倒是快,消息放出去不過一個時辰,這便上門了?
沈箬甚是好奇,想著看一眼再走,腳下步子慢了,騰挪了半刻,連門邊都不曾挨到。
「妳若是想看,就大方坐著。」
宋衡發話,她求之不得,旋身回到廳中,在他下首坐好,端著茶盞只做看戲的模樣。
宋衡覷了她一眼,甚是無奈地搖頭,怕不是把他這裡當戲臺子了?他故意問她。「可要給妳取碟瓜子過來?」
*欲知精采後續,敬請期待1/26上市的【文創風】922《夫人萬富莫敵》下。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夫人萬富莫敵(下)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夫人萬富莫敵(下)
有人說她一個商戶女,怎配得上位極人臣的他?
有人說宋衡在朝中樹敵眾多,真是可憐了即將要嫁他的女子,
不過她早已下定決心,就算危機四伏,她都能義無反顧!
宋衡曾以為自己不會娶妻,此生唯與朝政為伍,
殊不知從天而降一個未婚妻,推翻了他的「以為」。
自從與沈箬相識,他才知道女子也可以活得這般與眾不同,
別人彈的是一手好琴,她撥的是一手好算盤,
其他貴女講求「三從四德」,她求的是「生財有道」,
就連朝廷的帳本,她都能發現其中有詐,揪出舞弊貪官,
如果是她,一生一世一雙人,有何不可?
可他也害怕,他的情意,會為她的生活掀起驚濤駭浪……
沈箬一直以為,那些朝廷紛爭讓宋衡他們去煩惱,
她這個市井小民在旁邊涼快就好,豈知一切都想得太簡單了!
她開的香粉鋪鬧出命案,此事竟與大長公主有關,
沒關係,她看得很開,經營的生意毀了重來就是,
但被誣陷賣假藥,還欲置她於死地是不是太過分了?
她沈箬可不是好惹的,她身邊那位更是不會輕易罷休的,
那些心懷不軌的人且等著,他們倆定會加倍奉還!
作者簡介:
顧匆匆
一個相信所有人都不平凡的人,僥倖能拿筆創造出一、兩個世界。人生匆匆,唯愛長留,希望能在短短幾十年裡,寫夠我所嚮往的世界。
章節試閱
第二十一章
「殺千刀的啊!好端端的人就是吃了他們家的藥才沒了,可憐我家男人,昨兒個夜裡還能說笑,今早就斷了氣。」
婦人聲音洪亮,扠腰立在門邊吵嚷,腳邊還擺著一具屍體,白布覆面,只露出一雙腳。
沈箬行至門邊,街坊成群湊在一旁,對著門裡的人指指點點,似是認定了他們的藥材有問題。至於太守府的人,不過裝個樣子,站在原地看著鬧劇發生。
「若是我家的藥吃死人,妳倒是拿出證據來,帶個死人過來算怎麼回事?」玉筆人雖小,可嘴巴倒是厲害,守在門邊硬是不讓人前進半步。「無憑無據,小心我們告妳誹謗,拖去官府打板子。」
...
「殺千刀的啊!好端端的人就是吃了他們家的藥才沒了,可憐我家男人,昨兒個夜裡還能說笑,今早就斷了氣。」
婦人聲音洪亮,扠腰立在門邊吵嚷,腳邊還擺著一具屍體,白布覆面,只露出一雙腳。
沈箬行至門邊,街坊成群湊在一旁,對著門裡的人指指點點,似是認定了他們的藥材有問題。至於太守府的人,不過裝個樣子,站在原地看著鬧劇發生。
「若是我家的藥吃死人,妳倒是拿出證據來,帶個死人過來算怎麼回事?」玉筆人雖小,可嘴巴倒是厲害,守在門邊硬是不讓人前進半步。「無憑無據,小心我們告妳誹謗,拖去官府打板子。」
...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