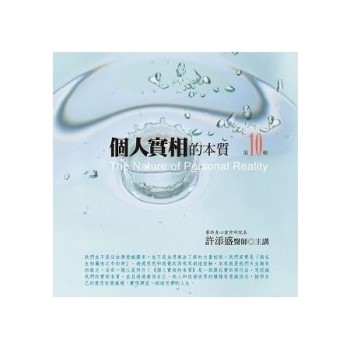心有所屬的丈夫、捂不熱的繼女、備受輕視的夫家……
這些她都不稀罕了,誰想要誰拿去,她要帶著肚子裡的孩子過自由生活!
只是怎麼和離之後,反而更多人出現,讓她的生活更「精采」了?!
她本是忠臣之後,但父母遭逢不幸、雙雙過世,她與哥哥寄人籬下,
成了家族的棋子,被安排嫁給武昌侯當繼室,卻是另一段不幸的開始……
一覺醒來,她依然是武昌侯夫人,也仍因繼女挑撥而被侯爺送到莊子上,
面對再怎麼努力也挽不回的婚姻、捂不熱的繼女,還有虎視眈眈的表小姐,
重生的她只想護住肚子裡的小生命,至於亂糟糟的武昌侯府與侯夫人位置,
哼,誰要誰拿去,她沈顏沫如今不稀罕了!
打定主意,她靜待武昌侯如前世般送來和離書,
只是這一世怎麼這麼好心,還多了三萬兩「贍養費」?
而她也發現,打從自己平靜接受和離,並著手準備自立生活後,
竟然有人暗中默默相助,連她跟著皇后進宮後也受到庇護,屢次化險為夷;
到底是誰如此關心一個和離後的平凡女子,為她打點了大小事?
難道是她那心有所屬的前夫有了悔意,還是那個揚言要納她為妾的景王爺?
怎麼離異之後,她的日子反而越來越熱鬧了……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繼母不幹了(1)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繼母不幹了(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