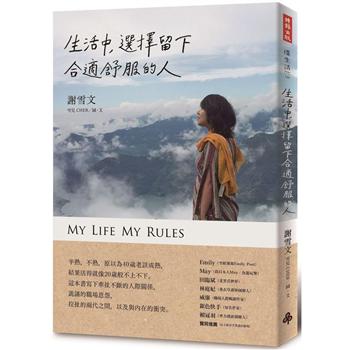第十一章
「我說,妳一大早守在這裡等我,就是為了給我送這些東西?」
四月過半,日頭熱了起來,蕓娘站在國公府外一處陰涼的角落裡,把背上的筐子卸下來,從裡面倒出來好些土春筍、鮮魚,還有隻活蹦亂跳的大鵝。
她一抹頭上的薄汗。「這都是我自己去鄉下收的,汴京城裡的東西又貴還又不新鮮,你瞧瞧這鵝……」
「行行行。」
李三郎擺了擺袖子,對身旁的僕人道:「愣著幹麼,收禮啊。」
僕人喏喏地點點頭,追著那隻大鵝滿地跑,一時間好不熱鬧。
李三郎說完,又扭頭看向蕓娘,狐疑地道:「說吧,妳無事不登三寶殿,送禮幹什麼?是不是終於覺得顧言靠不住,想就殿試那事來求求我國公府?我可跟妳說,不管顧言將來坐什麼位置,我國公府不摻和顧家那灘渾水。」
蕓娘一言難盡地看向李三郎,他們這些當官的就是心眼多,她來是為了那天譚春兒的事。
那一日在國公府,她報了前世被陸安歌算計的仇,心裡舒坦了幾天,但回頭一想,前世李三郎畢竟活得好好的,這一世卻被捲了進來,雖說也怪李三郎自己醉酒誤事,但她覺得多少有些過意不去,所以才特意從農莊費心收了些時令野味送過來。
只是她知道不能對李三郎實話實說,估計她要真說了,李三郎會更氣。
她頓了下,看了眼李三郎,清了清嗓子。
「也沒什麼,就是謝上回西李莊田的事,沒有你,田也要不回來,所以特地來謝謝你,哦,顧言也這麼說。」
「顧言也這麼說?」李三郎斜睨了她一眼。「我怎麼不太相信呢,他那性子哪可能理會這些。」
這話說得也算實在,蕓娘眨了眨眼。「顧言那個性子就是冷了些,心裡頭可熱呼著呢。」
李三郎嘴角抽了抽。
「行了行了,我也不算幫他,說到底是為了我姑母,我國公府出去的人就算人走茶涼了,也不能叫人欺負了去。」
話都說完了,禮也送了,蕓娘並不糾纏,轉身正要走,眼角餘光望到了側門處的紅轎子。
那轎子沈甸甸,晃晃悠悠的,顯然裡頭坐著人,似乎隱約還能聽見些哭聲。
「晦氣!當這是什麼地方。」
李三郎陰沈著臉正要上前,被蕓娘一把扯住。巧了不是,今天她給李三郎送東西,竟然正趕上譚春兒進府。
她目光一瞥,看到送轎的人站在一旁等著,不是那陸安歌還有誰?
她戴著帷帽正指使著下人把成箱的東西往國公府抬,畢竟譚春兒也是官家小姐出身,有些財物傍身,不然趙氏不可能收留她這麼久。
那些箱子晃晃悠悠,不知裝了些什麼,看起來倒是意外沈重。
轎子無聲無息的抬進了國公府,只見陸安歌轉身,另一輛馬車出現在側門陰影裡,從馬車上下來一個人,擺上腳凳,兩人交談了幾句,陸安歌便坐上了馬車,馬車漸漸隱沒在市集人群中。
「嘖……景王的人。」
蕓娘猛然抬頭,納悶地看向李三郎。
「什麼景王的人?」
李三郎低聲道:「她那車伕是景王的人,曾在巡撫司當過兵,我見過。」說完,悠悠看向她。「妳可知那女子和譚春兒是什麼關係?」
「按理說她是陸家的小姐,也就是譚春兒的表姊。」蕓娘給李三郎解釋道。
「陸家?景王?」
李三郎冷冷一笑。
「老子就說,那天的事哪有這麼湊巧。」
說完,他氣沖沖拔腿要走,可突然身子一頓,回身瞥了眼蕓娘。
「妳回去告訴顧言,國公府若是出了事,他殿試也考不了,待我查清楚那譚春兒在搞什麼鬼後,我自會去找他。」
蕓娘聽得心驚肉跳,上一世裕王和景王的皇位之爭鬧得翻天覆地,她臨死的時候也沒個結果,雖說這兩王爺都不是什麼好人,尤其那景王格外殘暴,有傳聞他為了討老皇帝歡心,曾下令建了個血池,只為益壽延年,陸安歌布的局要是和景王有關,怕是不會輕易善了了。
蕓娘快步走回家,想把李三郎這事告訴顧言,可剛到家門口,就見方才出現在國公府外那輛眼熟的馬車停在門外,有個人掀開簾子看向她。
「妹妹,我等妳很久了,有故人從漳州來了,正在陸府做客呢,有空妳可別忘了去見一見。」
故人?
蕓娘眼皮一跳,她的故人除了養父的爛賭棍兄弟沈海之外也沒別人了,她硬邦邦回道:「我沒什麼故人,也無舊可敘。」
這些話似乎也早在陸安歌意料之中,她下了馬車,身子傾向蕓娘,壓下一片不透氣的陰影,輕聲對她說:「蕓娘,大多數人的命,生來就不是掌握在自己手裡,尤其像妳這種,無權無勢、無依無靠的人,活著就如一粒不起眼的沙子,妳說,這世上少妳一個、多妳一個又有什麼差別呢?」
這些話劈頭蓋臉地砸在蕓娘心裡,上一世她就是把這些話聽進去了,因此自怨自艾,因著這些話畏畏縮縮,別人瞧不起她,連她也瞧不起自己。
如今重活一世,蕓娘一路同顧言從盧縣的小鄉村來到這裡,經歷了種種,也積攢了些底氣,連顧言都說了,這世上女子雖多,可她陸蕓只有一個,她不是一無是處,再說將來她還要做首輔夫人呢,那是頂厲害的。
這麼想著,蕓娘頓時心裡充滿了前世所沒有的勇氣。
她揚起臉,對著來人道:「是,我是一粒沙,可積沙也能成塔。就算妳百般貶低我,這輩子除了我自己,沒有人能替我決定命運。」
陸安歌目光幽深地看著她,像剛聽了個笑話一般,眼裡多是不屑。
蕓娘不再看她,轉身朝著家門口走去,腳下正要跨過門檻,一道嬌柔的聲音在背後響起──
「陸蕓,妳一路走來也算命大,國公府的事都叫妳逃脫了,可這回關乎妳身分戶籍之事,陸家已經上報巡城御史,到時開案審理,有沈海做人證,妳恐怕就非得回陸家不可了……啊對了,還有妳成親的事,妳戶籍有問題,成親自然也是不作數的。」那話音一頓,又一字一句道:「後日,我們官府見。」
蕓娘轉過頭,只望見那馬車漸漸隱去在西落的日頭裡。
不知站了多久,直到日頭漸漸落入雲下,霞光都看不大清了,帶著涼氣的夜風吹來,蕓娘依舊呆呆地站著,內心還在為陸安歌的話感到不安。
一陣馬車的聲音從旁邊傳來,馬蹄聲停了下來。
「怎麼站在這裡?」
蕓娘轉過頭,只見顧言下車,穿著一身青衣長衫,似帶著些春末夏初的青木香氣,撲面而來。
他垂眼看著她的神色,似乎瞧出些什麼。
「怎麼了?」
「沒、沒。」蕓娘眨了眨眼,扯出個笑。「餓了吧,我去做飯。」
夜色來臨,屋子裡,油燈的光亮映在白瓷的碗邊,蕓娘望著那燈芯明滅,只覺得彷彿跟自己現在的處境一樣,手裡的勺子攪了幾下,冒著熱氣湊到嘴邊,直到一股滾燙的觸覺從舌尖蔓延過來,火燒火燎地疼。
顧言抬眼,見蕓娘五官皺在一處,皺著眉頭,起身將帕子遞到她嘴邊。
「吐出來。」
蕓娘搖搖頭,支支吾吾半天,漲紅著臉硬生生把那口粥嚥下,含糊的說:「唔,不能浪費糧食。」
顧言瞥了她一眼,抬手從一旁壺裡倒了杯水,把杯口湊到她嘴邊。
蕓娘就著他的手抿了口,只覺得一陣清涼,剛抬眼,他的手指又伸到眼皮底下。
「張嘴。」
蕓娘下意識地張開口,他的手指擦過唇邊,她愣了下,只覺得那指腹格外柔軟,沒來由的又想到了那天顧言讓她說喜歡他的事,可還沒來得及細想,嘴裡冰冰涼涼的感覺蔓延開來。
她含糊地問:「蝦麼東西?」
顧言摩挲著指尖,一挑眉。「甘草黃連片。」
光聽名字就苦到家了,果然一陣苦澀在舌尖漫開,蕓娘皺著小臉,可還沒等這苦味過去,就被顧言捏起了下巴,固定住她的視線,她望著眼前站著的人,從高俯低看著她。
顧言這副不笑的模樣有些嚇人,不是表情的問題,是骨子裡透出來的氣勢,他這人看起來雲淡風輕的,可接觸久了才知強勢得很。
「說吧,心不在焉的,到底什麼事?」
蕓娘表情糾結起來,想到陸安歌說的身分戶籍那事,不知道怎麼開口。
顧言見她這副模樣,眉頭蹙起,眼神冷然。
「今日妳去給李三郎送東西,難道他又欺負妳了?」
「沒、沒。」
蕓娘急忙搖搖頭,這李三郎確實是招人恨的體質,凡事容易想到他身上。
不過,她突然想到在國公府門口見到的那檔事,連忙對顧言道:「對了,說來也巧,今日我去送禮的時候正好趕上譚春兒入府,是陸安歌送她去的,李三郎說陸安歌身邊似乎有景王的人。」
「景王?」顧言臉色嚴肅起來,眉頭緊蹙。「他可確定?」
蕓娘點點頭,急忙把話轉述道:「李三郎說,陸安歌的車伕曾在巡撫司當職,他見過。後來他便說要回去查查那譚春兒的底細,還讓我傳話給你,說若是國公府出了問題,恐危及你殿試。」
顧言蹙起眉頭,半晌沒吭聲,蕓娘覷著他的臉色。
「可是有什麼問題嗎?」
顧言撩起眼皮。
「妳可知,建元年初太子造反那夜,也是巡撫司先接到消息趕到的嗎?」
蕓娘一怔,一時間沒反應過來。
觸及這種秘辛,顧言似也不欲再多言,只是看了她一眼,淡淡道:「沒什麼,還是說回來妳今日到底是怎麼了,應該不是因為景王的事吧。」
她哪懂什麼這個王那個王的國家大事啊,蕓娘小臉一垮,深深嘆口氣道:「其實就還是陸家的事,剛才陸安歌特地在門口等我回來,為的就是警告我,她說沈海進京了,現在人就在他們陸家,他們還打算上告官府,強迫將我的戶籍落在陸家。」
她抿了抿嘴,連自己都沒發現自己的話音裡帶著幾分委屈。「她還說,若是改了戶籍,那我們的婚書也就不算數了。」
顧言鬆開手,微微垂下眼。
「就這些?」
蕓娘睜大杏眼望向顧言,什麼叫就這些?他怎麼聽到婚書不作數一點反應都沒有?
她兩腮氣呼呼地鼓起來,像隻炸毛了的狸貓。
「顧言,你是不是早盼著那婚書不算數呢,我跟你說,不可能!」
*欲知精采後續,敬請期待10/18上市的【文創風】1110《撿到潛力股相公》下。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撿到潛力股相公(下)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撿到潛力股相公(下)
顧言從沒想到顯赫的顧家有朝一日會落得這下場,
然而更驚人的卻是眼前的情況──
重傷清醒後,發現自己竟然有了娘子,這是怎麼回事?!
從相公的氣度及隨身玉珮,蕓娘已認出他是不可小覷的人物──
現今雖因牽連重罪遭流放,將來卻是權勢滔天、手段狠戾的首輔大人顧言!
這樣的人不會輕易被矇騙,一旦平反冤屈翻身上位,勢必也瞧不上她這等糟糠妻,
一定會要求她下堂,屆時她就乘機要一大筆和離錢,荷包滿滿的離去倒也不虧!
為了日後翻舊帳有憑有據,一心發大財的蕓娘開始了養相公的記帳日常──
從看病療傷、三餐雜支,到束脩的臘肉錢、赴考路費等,筆筆都不遺漏;
偏偏養家活口操勞之餘,還要應付糾纏不休的陸家人,簡直不得安生……
好在關關難過關關過,顧言果然連中三元一舉成了欽點的狀元郎!
本以為苦盡甘來,怎知瓊林宴上,狀元和榜眼竟然為了她而大打出手!
原來榜眼就是前世跟蕓娘有糾葛的未婚夫,因為殘存著記憶,不甘心放手,
然而顧言也擺明了無意放手,這就麻煩了,難道他想賴帳、不付她錢?!
作者簡介:
晏梨
晉江文學城簽約作者。天蠍座,貓奴,歷史劇愛好者,愛美食,愛生活。希望能用自己的筆寫出如夢的世界,也希望大家能在這個世界作一個盡興的好夢。
章節試閱
第十一章
「我說,妳一大早守在這裡等我,就是為了給我送這些東西?」
四月過半,日頭熱了起來,蕓娘站在國公府外一處陰涼的角落裡,把背上的筐子卸下來,從裡面倒出來好些土春筍、鮮魚,還有隻活蹦亂跳的大鵝。
她一抹頭上的薄汗。「這都是我自己去鄉下收的,汴京城裡的東西又貴還又不新鮮,你瞧瞧這鵝……」
「行行行。」
李三郎擺了擺袖子,對身旁的僕人道:「愣著幹麼,收禮啊。」
僕人喏喏地點點頭,追著那隻大鵝滿地跑,一時間好不熱鬧。
李三郎說完,又扭頭看向蕓娘,狐疑地道:「說吧,妳無事不登三寶殿,送禮幹什麼?是不...
「我說,妳一大早守在這裡等我,就是為了給我送這些東西?」
四月過半,日頭熱了起來,蕓娘站在國公府外一處陰涼的角落裡,把背上的筐子卸下來,從裡面倒出來好些土春筍、鮮魚,還有隻活蹦亂跳的大鵝。
她一抹頭上的薄汗。「這都是我自己去鄉下收的,汴京城裡的東西又貴還又不新鮮,你瞧瞧這鵝……」
「行行行。」
李三郎擺了擺袖子,對身旁的僕人道:「愣著幹麼,收禮啊。」
僕人喏喏地點點頭,追著那隻大鵝滿地跑,一時間好不熱鬧。
李三郎說完,又扭頭看向蕓娘,狐疑地道:「說吧,妳無事不登三寶殿,送禮幹什麼?是不...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