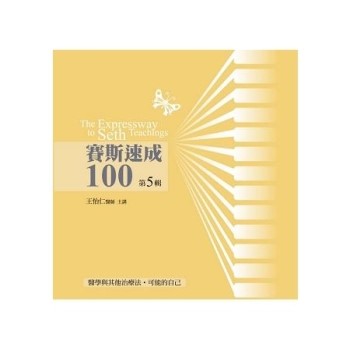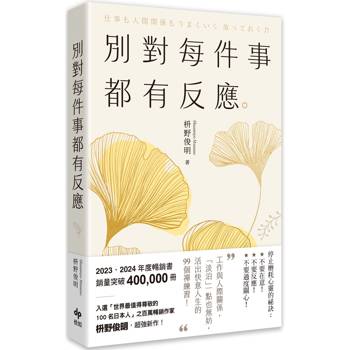應是她執念太深,病死了也無法真正放下,
只能看著未婚夫背棄諾言,成家立業,這種人生不要也罷!
重生的她,要為自己、為家人平反冤屈,男人閃邊去吧!
不能怪她孟如韞重活這一世,變得步步思量、精打細算。
前生的她身為罪臣之女,家破人亡,只得孤身上京投靠舅舅;
但世事難料,她最終落得病死,訂親的未婚夫也未能遵守承諾,
大抵是她執念太深,魂魄竟徘徊在世間看著他成家立業……
說不難受是假的,但如今因著莫名機會重新回到十六歲入京時,
既然已知道投靠舅舅後不得善終,不如趁機帶著丫鬟另尋出路!
於是她乾脆在酒樓落腳,靠著賣詞賺錢,也好避開無緣的未婚夫;
但如今的她只是個孤女,想靠一己之力為家人平反,談何容易?
而避之唯恐不及的未婚夫竟然意外找上門來,還一副情深義重的模樣,
另一頭又冒出個北郡巡檢陸明時,分明不相識,卻處處待她很特別;
她除了要想法子在京城安身立命,還得周旋於兩個男子之間,
況且靠賣詞賺錢並非長久之計,得找個真正可靠、有實力的「上司」;
唉,這重生的日子怎麼還是前途不明,一樣坎坷呀……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娘子套路多(1)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娘子套路多(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