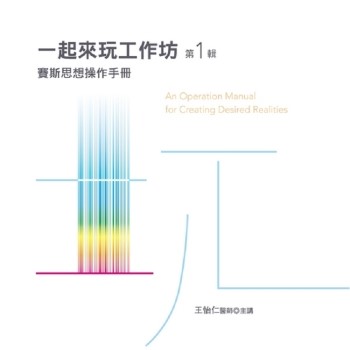與他一同打馬吊牌、行走於集市間,
花燈閃爍,宛如一場美好幻夢,
可她能與沒有記憶的他當好朋友,
不代表能給恢復前世記憶的他好臉色!
時光飛逝,清殊成了小郡主伴讀,感受了宮裡的壓抑,
卻也與晏徽雲彼此互通心意。不過二人皆非黏糊糊的性格,
不多時他便返回關外駐紮,她也兢兢業業陪伴小郡主上學。
認識的人越多,她越感受到自己的幸運,更明白世道對女子的綁縛。
到了學堂暑月假,她總算能回一趟外祖家,遠離京中是非,
卻不知她早已被腐朽的貴胄盯上,待她返京,便落入一場陰謀。
她被綁至陌生宅院囚禁,但她心裡不慌,只因明白姊姊現在的能耐,
但當她發現這宅院中不僅是自己,還有一位曾經朝氣蓬勃的女子,
女子遭強佔卻不能反抗,又在家族權衡利弊下犧牲,成為勛貴的外室。
她心中的憤怒難以言喻,分明是受害者,卻得背負傷痛一生!
於是她出逃後,在皇后的千秋宴上,當眾控告那位勛貴的種種罪行,
這一刻,她不在意世人言語如刀,也不在意晏徽雲知曉後如何看待,
眾人皆視女子為可欺的兔子,她得讓這些人明白,兔子急了也會咬人!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攀龍不如當高枝(4)(完)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攀龍不如當高枝(4)(完)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小粽
晉江文學城簽約作者,99年出生的一只小粽,愛好看書、寫字、唱歌,性格ENFP。
夢想是實現財富自由,躺平後半生。吃想吃的食物,見想見的人,看想看的書,成為快樂小狗!
之所以產生創作的衝動,是因為想寫一本完全符合自己愛好的書!
創作風格:隨心所欲,愛好廣泛,偏愛古言大女主。
小粽
晉江文學城簽約作者,99年出生的一只小粽,愛好看書、寫字、唱歌,性格ENFP。
夢想是實現財富自由,躺平後半生。吃想吃的食物,見想見的人,看想看的書,成為快樂小狗!
之所以產生創作的衝動,是因為想寫一本完全符合自己愛好的書!
創作風格:隨心所欲,愛好廣泛,偏愛古言大女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