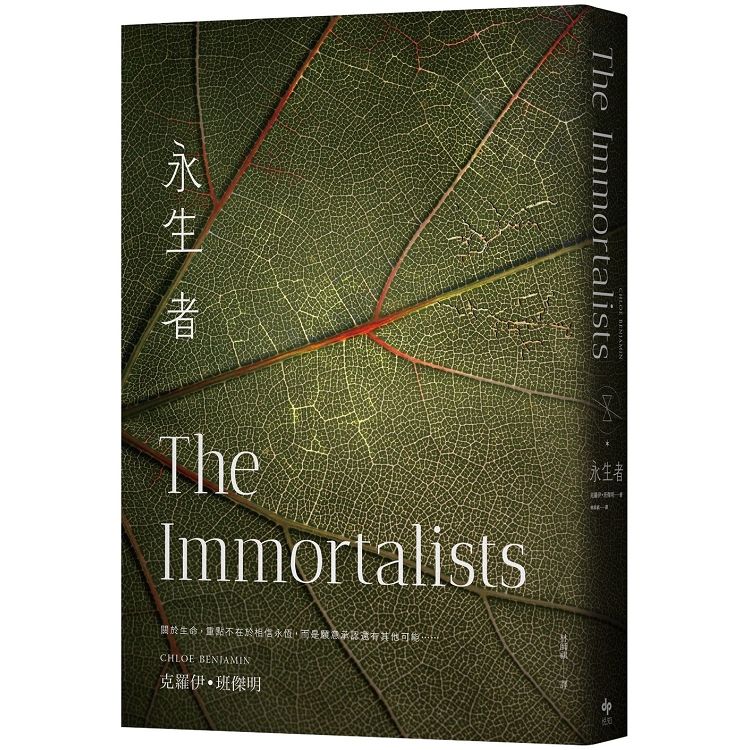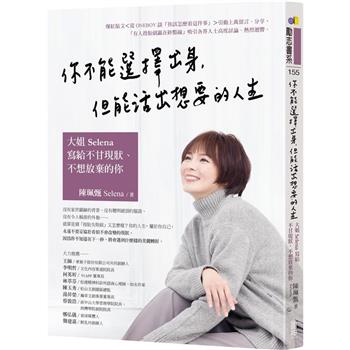如果預知自己的死期,你會怎麼過你的人生?
高踞《紐約時報》小說暢銷書榜10週以上!
即將開拍影集!
高踞《紐約時報》小說暢銷書榜10週以上!
即將開拍影集!
★★
●普立茲文學獎得主理察.羅素盛讚:「此書是文學懸疑小說最精彩的那種,懸疑氛圍來自我們真心在乎的角色們,帶著深深刻在我們人性中的意外驚喜!」
●People時人推薦,繼《金翅雀》唐娜‧塔特、《無聲告白》伍綺詩,下一位當代小說界女神!
●知名小說《吠》作者羅麗‧摩爾盛讚:「一位極為出色的新秀!」
●美國金牌製作人蓋兒.貝爾曼(Gail Berman)領導團隊The Jackal Group簽下電視影集版權!
/
關於生命,重點不在於相信永恆,
而是願意承認還有其他可能……
/
1969年,紐約下東城,一名神祕女人意外到訪,鎮民們議論紛紛。這名浪跡天涯的靈媒,聲稱能夠預知人們的死期。寇德家四個孩子決定一同窺視命運。靈媒預言13歲的長女法芮雅會活到88歲;11歲的丹尼爾將在46歲去世;9歲的克拉拉只活到31歲;而最年幼的賽門則不肯說自己的死期。
然而,靈媒斬釘截鐵的預言,卻在孩子們年幼心靈埋下恐懼的種子。時間來到1978年,16歲的賽門害怕在父親死後,承擔照顧母親的重責,於是逃家來到舊金山,過著墮落且毫不節制的生活;自由浪漫的克拉拉高中畢業,便追隨外婆而成為魔術師,遊走於現實與幻象之界;眼見弟妹遠走他鄉的丹尼爾,醫學院畢業後選擇從軍,卻也惶恐自己信奉規律生活是懦夫的表現;長女法芮雅則因恐懼無法控制生命,投身於長生不老的研究,希望減輕獨活下來的罪惡。
究竟他們的命運,是性格使然?還是被預言綁架?
一部野心勃勃且意喻深刻的小說,探究命運與選擇、信念與魔力、真實與虛幻、現在與過去、當下與明日之間的界線,動人地向我們訴說──思考的力量、美好的天性,以及家族的羈絆。
得獎記錄
●博客來八月選書/OKAPI書評/2018外文年度選書
●各媒體年度選書:華盛頓郵報.Goodreads.美國公共廣播電台NPR.新聞週刊.美國圖書館協會(LibraryReads).文學書評網站Lit Hub.哈芬登郵報.娛樂週刊.Lit Reactor文學書評網站.Book Riot書評網站.ELLE.美麗佳人雜誌.紐約公共圖書館.The Skimm網站.Bustle雜誌.W Magazine.Time Out雜誌.南方生活雜誌.Hello Giggles網站.InStyle雜誌
●美國企鵝蘭登出版社年度重點小說,法蘭克福書展授權美、英、巴、捷、法、德、匈、以、義、波、西、土、俄、韓等國家,授權出版30種語言版本,美國已售出超過25萬本,於《紐約時報》小說暢銷書排行榜榜上高踞十週以上!
各界好評
「此書是文學小說最精彩的那種,懸疑氛圍來自我們真心在乎的角色們,帶著深深刻在我們人性中的意外驚喜!」──普立茲文學獎得主理察.羅素(Richard Russo)
★ 關乎壽命長短的價值,而我們又是否為自己命運的受害者,甚至肇事者。──亞馬遜書店當月選書
★ 跨越五十年的華麗故事,每一頁都充滿作者傑出的說書技巧。──美聯社
★ 每個故事都是一個微小奇蹟,卻能一同編織成令人難以忘懷的美麗織錦,述說了家庭、愛情及失落。──Lit Hub文學書評網站
★ 人最終難免一死,但她捕捉到最動人美麗的真相。──芝加哥論壇報
★ 讓讀者深思該如何利用在地球上的其餘人生時間。──赫芬頓郵報
★ 巧妙地探索命運與選擇之間的對立。──US Weekly美國週刊
★ 解謎的過程成了這一個龐大而迷人的家族傳奇。──娛樂週刊
★ 一部完美得令人驚訝的作品。──《珍奧斯汀讀書會》作者凱倫.裘依.芙勒
★ 此書的核心是對自由意志和命運的探究。──紐約客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