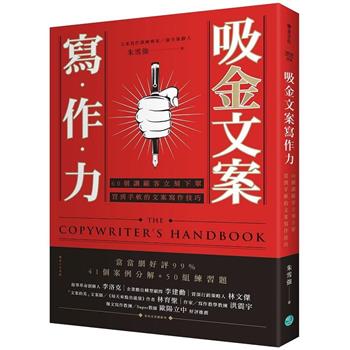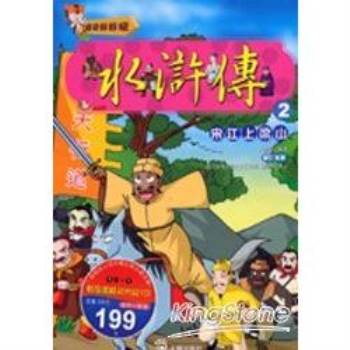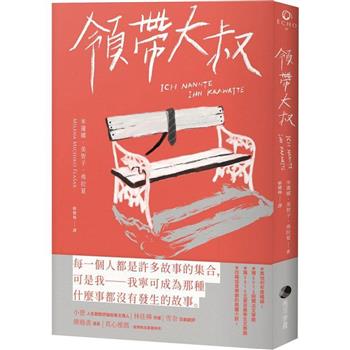圖書名稱:親愛的艾德華
總有一天,
我們將理解那些「失去」教會我們的事。
獻給身處於創傷時代的我們──
以寫實而溫柔筆觸,描寫人生無常,以及面對失去後的種種內心變化,引領我們思考生命的意義,珍惜每個當下。
//
活著,不只倖存,
而是要擁有人生。
//
讀這個故事,你不能太傷心,要有陪伴艾德華走下去的勇氣,而且得是仰望人生的那一種。
小說一開始,十二歲的艾德華,與親愛的哥哥、父母,以及一百八十三位旅客一起登機,從紐約的紐沃克機場出發前往洛杉磯。飛行中途,飛機墜毀,僅艾德華獨自生還。
故事以雙線交錯呈現,一方面以細膩筆觸,訴說機上乘客的人生故事與這趟旅程之於他們的意義;另一方面描寫艾德華劫後餘生的創傷與憂傷,對所愛之人的思念。
隨著年月,艾德華深知自己可能永遠不會好起來,但也試圖理解「為什麼是我」,從多年來泅泳其中的失落,領悟到痛苦原來是愛,而重新找回人生的定錨點。
【封面設計】
鳥兒逆風飛翔的姿態,說明有時人生壞到底了,卻也有好轉的絢爛可能,小小的艾德華被大大的鳥影(也意指飛機)遮住,身處人生的灰暗小角落仍可正視星星高掛的深藍天際,那是對想念之人的遠望,也代表著未來仍值得期許。
作者簡介
安.納波利塔諾 Ann Napolitano
紐約大學藝術創作碩士。目前擔任文學雜誌《One Story》的副主編,並在多個學校教授創意寫作課程,包括布魯克林學院、新紐約成人教育與專業研究學院、高譚作家工作坊。目前與丈夫和兩個兒子定居紐約布魯克林。
▎作者官網:annnapolitano.com/
▎作者推特:napolitanoann
譯者簡介
康學慧
英國里茲大學應用翻譯研究所畢業,從事專職翻譯多年。現居於寶島後山的小鎮,沉醉於書香、稻香與米飯香。譯作有《闇影少女:重生》、《迷幻之境》、《小鎮書情》、《只要群星依然閃耀》、《等待貝里葉先生》、《好妻子》、《要快樂,你永遠有這個選擇》、《純潔國度》,及《人生馬戲團》等(以上為悅知文化出版)。


 2021/04/17
2021/04/17 2021/01/04
2021/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