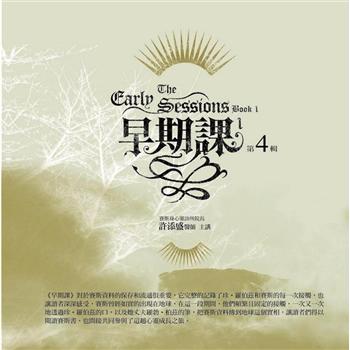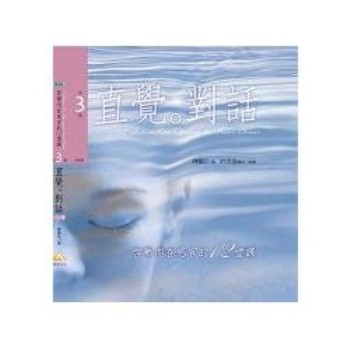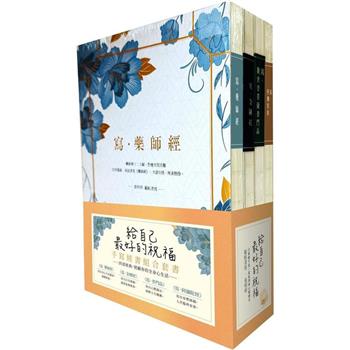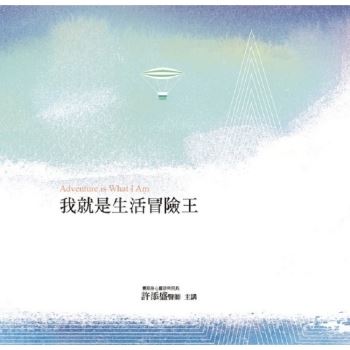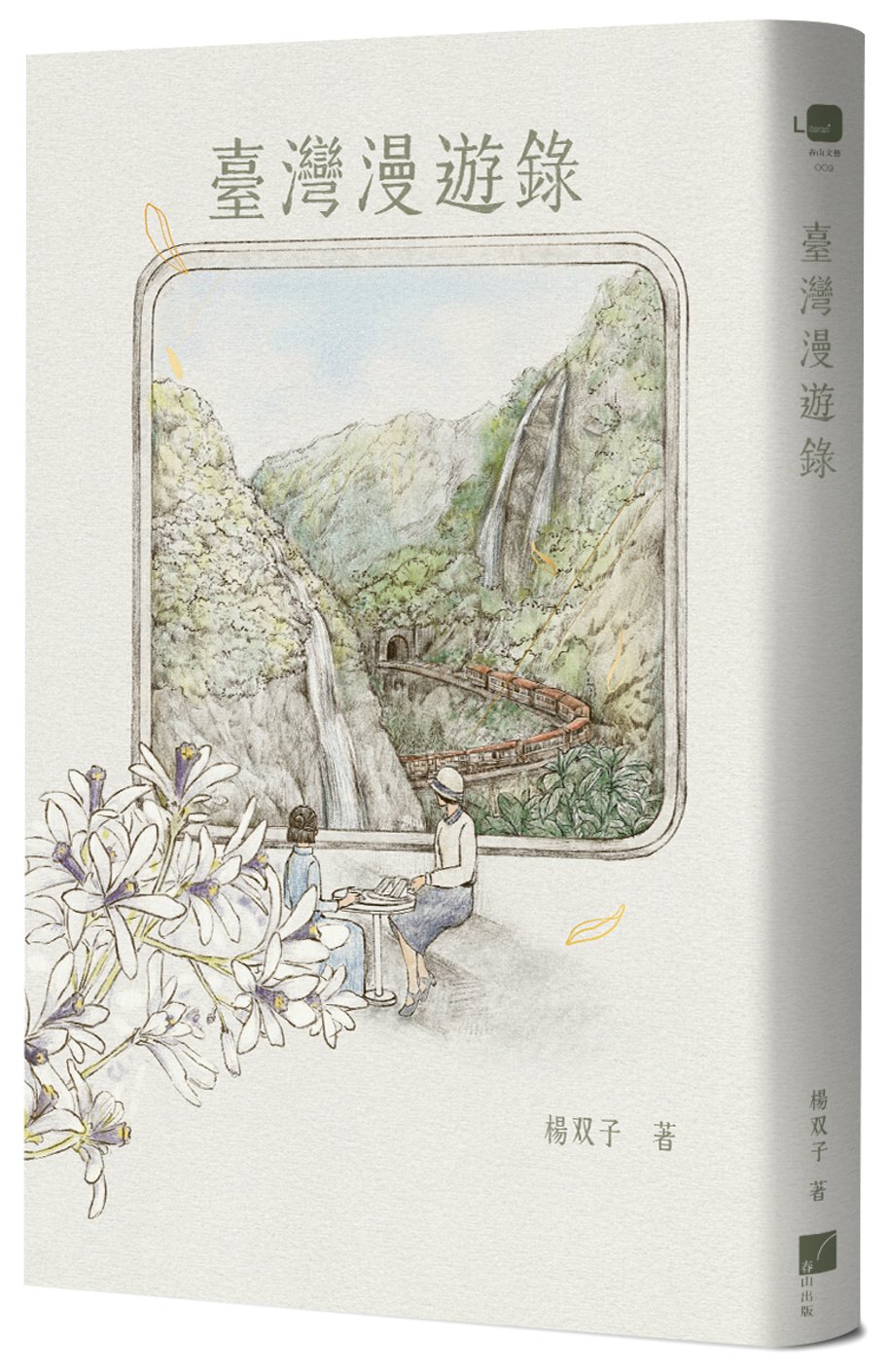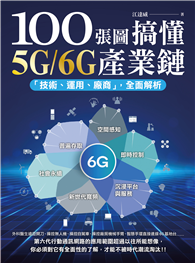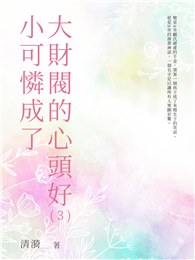第一章 步入「衰敝期」的明王朝
盧象昇,生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三月,殁於崇禎十一年(1638)年十二月,不足39週歲而亡。他一生短暫,卻在明末內憂外患的歷史畫卷上塗下了濃重的一筆。盧象昇是明末天啟、崇禎時期一位重要的地方實力派官員,歷任戶部主事、大名知府、大名兵備、鄖陽撫治、湖廣巡撫、中原五省總理、宣大山西總督(後加兵部尚書銜)等職,與明末黨爭、農民起義、明清戰爭,都有十分密切的聯繫。目前,有諸多記載盧象昇生平事蹟的較為豐富的歷史文獻資料,如《盧象昇疏牘》(有盧象昇所作近200篇奏疏和公牘),此外還有《明大司馬盧公年譜》、《忠肅集》、《茗嶺盧氏宗譜》等。然而,到目前為止,對盧象昇專門研究成果還十分缺乏,這與其在明末歷史上的地位很不相符。本書即從原始文獻的研究切入,同時結合時人和後人的研究論述,希望讀者對盧象昇的生平事蹟有個較為全面的瞭解,以深化對複雜多變的明末政治時局的認知;進一步探究是怎樣的明末大歷史造就了一代名臣盧象昇,而盧象昇之所為又如何影響和豐富了明末大歷史。同時,本書也試圖將考察盧象昇挽救時局的努力與最終失敗,作為探尋明朝最終敗亡原因的一個視角。
盧象昇之所為與之所不為,皆離不開他所處的具體的歷史環境,那麼,盧象昇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呢?
第一節 晚明皇帝怠政與黨派紛爭
一、萬曆和天啟怠政
萬曆朝後期,皇帝怠政已經十分嚴重。後人在總結明亡之教訓時,多涉及萬曆怠政,如清人稱:「明之亡,不亡於崇禎之失德,而亡於神宗之怠惰,天啟之愚騃。」孟森亦有相似結論:「明之衰,衰於正、嘉以後,至萬曆朝則加甚焉。明亡之徵兆,至萬曆而定。」當代明史學者王天有持有類似之觀點,他將明朝歷史分為四個歷史階段:開創期、腐化期、整頓期和衰敝期;他認為,「從明神宗萬曆十年(1582)至明思宗崇禎十七年(1644),是明朝的衰敝期」。
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死,萬曆帝親政,起初他還頗有些勵精圖治的態勢。當朝官員海瑞,曾對他稱頌不已:「自張居正刑犯以後,乾綱獨斷,無一時一事不唯小民之念。」然而,萬曆十四年(1586年)秋,萬曆帝竟然開始「連日免朝」。禮部主事盧洪春,質疑皇帝因身體健康之故免朝,並諷諫萬曆帝,惹惱了皇帝,遭到廷杖革職的處罰。此後,萬曆帝怠政愈加頻繁,尤其在「國本之爭」事件發生後,他甚至與群臣關係勢如水火。對於萬曆怠政的狀況,孟森曾有論:「帝既不視朝,不御講筵,不親郊廟,不批答章奏,中外缺官亦不補。」
學界對於萬曆帝長期怠政之因,已有探討。閻崇年認為,萬曆怠政原因有四:擺脫戒尺、居功自傲、沒有競爭、身體有病。米智也試圖從君臣矛盾的角度,來論述怠政之因;美籍華人史家黃仁宇,則從中國傳統道德的層面,來論述萬曆怠政之因,並提出:「中國兩千多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筆者以為頗有些可資之處。
另外,我們還可以從萬曆帝的性格和心理的角度,分析他長期怠政的原因。幼年時期的萬曆帝,生活在李太后、張居正和馮寶的交相訓教之中,個人的天性和興趣被強行壓制。比如,他曾與小太監在宮中嬉戲,被馮寶狀告至李太后處,並遭到太后跪罰。萬曆帝自然對他們三人十分敬畏,閻崇年稱這三人是懸在小萬曆頭上的「三把戒尺」。萬曆帝少年時的天性和愛好遭到扼殺,在其內心深處便產生了一種叛逆心理。[而一旦「三把戒尺」的威力不存,萬曆帝可能就會井噴式地自我放縱,甚至會對曾限制其自由的人實施報復。同時,親政的萬曆帝要有一番作為,也必須徹底消除「三把戒尺」的影響。或許,親政後的萬曆帝就是基於這種複雜心理的影響,才最終決定清除張居正、馮寶集團的政治影響。當然,萬曆帝不可能對自己的母親痛下狠手;更何況,他親政後,李太后也逐步放鬆了對兒子的管教。然而,「倒張運動」的結局卻事與願違,萬曆帝對朝臣道德說教的虛偽產生了很大的厭惡。不久後,爆發的立太子的國本之爭,最終使萬曆帝與朝臣的矛盾激化了。他無法擯棄歷史形成的傳統道德觀念和封建宗法制度,只好採取了逃避群臣的做法:深居內宮,不問朝政。正如為《萬曆十五年》寫書評的歐蒲臺所言:「在其皇帝角色裡表現活力的所有嘗試遭到普遍反對後,萬曆走上了罷工的道路,全身心地去陪伴鄭貴妃。」
同樣,天啟帝的怠政也絲毫不亞於乃祖萬曆帝。諸多史籍都稱其嗜好工匠造作之事,而將朝政委於寵宦魏忠賢等人。對此,明人筆記《先撥志始》、《酌中志餘》、《曠園雜志》和《三朝野紀》皆有記述。如《三朝野紀》有云:「上性好走馬,又好小戲;好蓋房屋,自操斧鋸鑿削,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內官監、御用監辦進,日與親近之臣涂文輔、葛九思輩朝夕營造。造成而喜,不久而棄;棄而又成,不厭倦也。當其斤斫刀削,解衣盤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窺視。王體乾等每伺其經管鄙事時,即從旁傳奏文書。奏請畢,即曰:『爾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忠賢輩操縱如意,而呈秀、廣微輩通內者,亦如袍鼓之捷應也。」陳登原更稱天啟帝為「頑童」,「熹宗好走馬、好水戲、好起造,凡此等等,皆是頑童行徑」。既然熹宗如此愛玩,那就無心朝政了,朝中出現的權力真空自然就由他寵信的閹黨集團來填補了。而魏閹集團趁機鞏固自己的政治勢力,拉攏原東林黨官員的敵對派,打擊以東林黨為核心的正直官員,使業已存在的門戶黨爭進一步激化。
二、門戶黨爭的形成和延續
萬曆怠政,加之其他因素,朝野出現了門戶黨爭,而天啟怠政則加劇了黨爭的激烈程度,使明末朝政更加混亂,社會危機急遽加深,加速了明王朝的覆滅。
張居正被清算後,那些曾經因上諫忤逆而被貶官的官員們,皆先後被萬曆帝重新重用;朝中也沒有權臣再嚴控言路。因此,朝廷的諫言之風再次高漲。起初,有些官員對張居正一黨進行參劾,同時向皇帝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萬曆怠政後,他們又對萬曆帝違背帝王之道的諸多做法進行諫諍,以表忠貞。例如,在「爭國本」中,不少朝臣都涉入其中。總體來看,對於這些諫諍,起初,官員們或許是堅持封建倫理綱常,較少摻雜派系的利益之爭,但後來則出現了門戶之爭。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事件,則成為引發明末門戶之爭的火藥桶。明末文人文秉曾評說「癸巳京察」事件:「門戶之禍堅固而不可拔,自此始也。」門戶之爭亦有愈演愈烈之勢。
朝中官員在議事中,往往依籍貫、師承關係等,按照各自的利益需求,結成相對穩定的不同利益集團,便形成了所謂的「黨」,如宣、崑、浙、楚、齊黨和東林黨。一般來說,前者五黨實為官場利益而形成的不同的政治集團;後者則是有正義感的在野士大夫,以無錫東林書院為聯絡基地,形成的群眾性組織,後來朝中一些正直的官員也與之相呼應,便演變成一個有政治利益訴求的政治集團,後被政敵稱為「東林黨」。東林黨不僅代表了江南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甚至還始終支持並參與市民階級反對封建特權的鬥爭。
萬曆末,黨爭激烈,周嘉謨出任吏部尚書後,吏治狀況才有所好轉。《明史》載:「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為政,黜陟之權,吏部不能主。及嘉謨秉銓,唯才是任。光、熹相繼踐祚,嘉謨大起廢籍,耆碩滿朝。向稱三黨之魁及朋奸亂政者,亦漸自引去,中朝為清。」從此,三黨官員利盡而散,轉而投靠權勢方熾的魏閹集團。所以,啟、禎年間的朝中黨爭主要在閹黨和東林黨之間進行。
由於東林黨官員的積極努力,明熹宗終於順利地入繼大統。所以,天啟初年,朝中的東林黨官員勢力大盛,出現了「東林勢盛,眾正盈朝]的局面。然而,東林黨人卻專注於以「三案」為焦點,打擊政敵,以報萬曆末年所遭受其他黨派迫害之仇,反而矯枉過正,樹敵更多。不久,羽翼漸長的魏閹集團利用熹宗的恩寵與昏庸,代替東林黨人掌握了朝政大權。從天啟四年(1624年)至天啟末,閹黨集團與東林黨人之間的黨爭十分慘烈。結果,東林黨人遭到沉重的打擊,朝野出現了閹黨一派獨大的局面。
崇禎帝即位不久,開始欽定逆案,對閹黨勢力進行清算,魏忠賢等人被遣戍甚至處死,東林黨官員再次受到重用,原來被魏閹集團排擠的東林或親東林官員相繼歸朝任事。然而,崇禎帝卻是一位勤政嗜權的皇帝,他希望朝野臣工能「化異為同」,共濟時局,並嚴禁臣屬結黨相爭。據《明史》載:「陛下明旨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曰『化異為同』,曰『天下為公』。」所以,雖然東林黨人重返朝政,但未再形成天啟初「東林盈朝」的局面。同時,閹黨勢力雖遭清算,但還有不少殘黨隱而不發,甚至得到了與東林黨人有隙的首輔大臣溫體仁的保護。終崇禎一朝,東林黨及有「嗣東林」之稱的復社,與閹黨集團仍然明爭暗鬥。然而,由於崇禎帝馭下甚嚴,門戶黨爭並沒有發展至左右朝政的地步。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明末名臣盧象昇:被世人所遺忘的抗清英雄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明末名臣盧象昇:被世人所遺忘的抗清英雄
他的一生,是一段慷慨激昂的抗清史詩;
他的功蹟,足以與悲劇英雄袁崇煥比肩;
他的名字,卻長久地被淹沒在晚明混亂的馬蹄聲中──
他叫盧象昇。
盧象昇是明末天啟、崇禎時期一位重要的地方實力派官員,歷任戶部主事、大名知府、大名兵備、鄖陽撫治、湖廣巡撫、中原五省總理、宣大山西總督(後加兵部尚書銜)等職,與明末黨爭、農民起義、明清戰爭,都有十分密切的聯繫。然而,到目前為止,對盧象昇專門研究成果還十分缺乏,這與其在明末歷史上的地位很不相符。
本書即從原始文獻的研究切入,同時結合時人和後人的研究論述,希望讀者對盧象昇的生平事蹟有個較為全面的瞭解,以深化對複雜多變的明末政治時局的認知;進一步探究,盧象昇如何影響和豐富了明末大歷史,又是怎樣的明末大歷史,造就了一代名臣盧象昇。
作者簡介:
龍騰,歷史學博士,曾參編《經濟研究導刊》、《中國史研究動態》等多家期刊,公開發表論文多篇,參與多項社科基金。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步入「衰敝期」的明王朝
盧象昇,生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三月,殁於崇禎十一年(1638)年十二月,不足39週歲而亡。他一生短暫,卻在明末內憂外患的歷史畫卷上塗下了濃重的一筆。盧象昇是明末天啟、崇禎時期一位重要的地方實力派官員,歷任戶部主事、大名知府、大名兵備、鄖陽撫治、湖廣巡撫、中原五省總理、宣大山西總督(後加兵部尚書銜)等職,與明末黨爭、農民起義、明清戰爭,都有十分密切的聯繫。目前,有諸多記載盧象昇生平事蹟的較為豐富的歷史文獻資料,如《盧象昇疏牘》(有盧象昇所作近200篇奏疏和公牘),此外還有《...
盧象昇,生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三月,殁於崇禎十一年(1638)年十二月,不足39週歲而亡。他一生短暫,卻在明末內憂外患的歷史畫卷上塗下了濃重的一筆。盧象昇是明末天啟、崇禎時期一位重要的地方實力派官員,歷任戶部主事、大名知府、大名兵備、鄖陽撫治、湖廣巡撫、中原五省總理、宣大山西總督(後加兵部尚書銜)等職,與明末黨爭、農民起義、明清戰爭,都有十分密切的聯繫。目前,有諸多記載盧象昇生平事蹟的較為豐富的歷史文獻資料,如《盧象昇疏牘》(有盧象昇所作近200篇奏疏和公牘),此外還有《...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自序
本書是在我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完成的。博士畢業後,我就計劃完成這部專著。然而,近年來公司和家庭事務繁多,故終未能如願。這年春季趁工作不太忙,我便開始著手本書的寫作,之後寫作時斷時續,十月中旬終於完成初稿的提交。
專注於本書的寫作,首先是希望以此來紀念自己的博士學習生涯,並對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和總結。在盧象昇研究過程中,我對盧象昇生平事蹟和明末歷史興趣漸濃。寒冬月夜,北風凜冽,胯下五明驥、孤軍抗清的盧象昇戰殁的歷史畫面不時地縈繞在我的腦海。我常常在思索:倘若盧象昇、孫傳庭等一代名臣果受...
本書是在我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完成的。博士畢業後,我就計劃完成這部專著。然而,近年來公司和家庭事務繁多,故終未能如願。這年春季趁工作不太忙,我便開始著手本書的寫作,之後寫作時斷時續,十月中旬終於完成初稿的提交。
專注於本書的寫作,首先是希望以此來紀念自己的博士學習生涯,並對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和總結。在盧象昇研究過程中,我對盧象昇生平事蹟和明末歷史興趣漸濃。寒冬月夜,北風凜冽,胯下五明驥、孤軍抗清的盧象昇戰殁的歷史畫面不時地縈繞在我的腦海。我常常在思索:倘若盧象昇、孫傳庭等一代名臣果受...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
自序
第一章 步入「衰敝期」的明王朝
第一節 晚明皇帝怠政與黨派紛爭
第二節 萬曆帝的貪婪與斂財
第三節 起義和遼患日趨嚴重
第二章 盧象昇的生平(上)
第一節 重孝有宏志的青少年時代
第二節 督理臨清倉
第三節 知府大名
第四節 兵備畿南三郡
第五節 撫治鄖陽
第三章 盧象昇的生平(下)
第一節 由巡撫湖廣到總理五省
第二節 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第三節 傾力主戰殞命疆場
第四章 盧象昇的軍事策略
第一節 用兵籌餉之策
第二節 ...
自序
第一章 步入「衰敝期」的明王朝
第一節 晚明皇帝怠政與黨派紛爭
第二節 萬曆帝的貪婪與斂財
第三節 起義和遼患日趨嚴重
第二章 盧象昇的生平(上)
第一節 重孝有宏志的青少年時代
第二節 督理臨清倉
第三節 知府大名
第四節 兵備畿南三郡
第五節 撫治鄖陽
第三章 盧象昇的生平(下)
第一節 由巡撫湖廣到總理五省
第二節 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第三節 傾力主戰殞命疆場
第四章 盧象昇的軍事策略
第一節 用兵籌餉之策
第二節 ...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