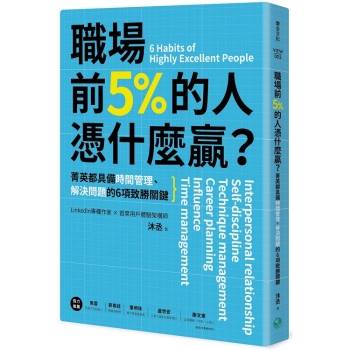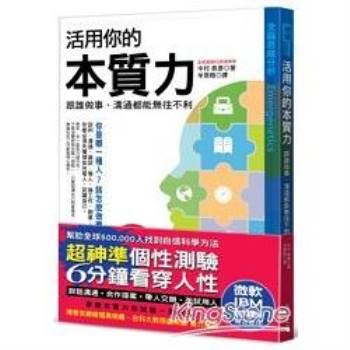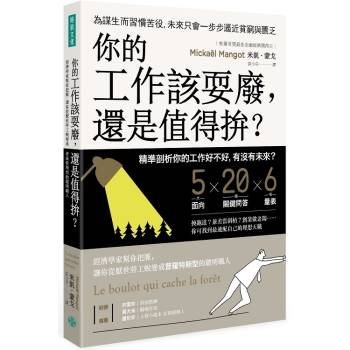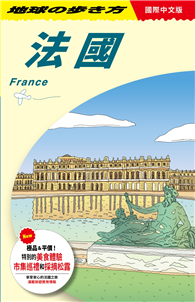第二節 〈大象〉與〈易象〉
〈易象〉最早見於《左傳》一書。《左傳·昭公二年》載:「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什麼是〈易象〉?傳統觀點認為〈易象〉即是《周易》。而首倡此說者,是晉代的杜預。他在注解上段文字時說:「〈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
〈易象〉即是《周易》古經的觀點,對後世影響很大,傳統學者多從此說,如孔穎達等。清惠棟在《春秋左傳補註》卷四中明確提出:「古謂易為象,故曰〈易象〉。左氏稱〈易象〉,猶不失古意。」與惠棟同時代的易學家胡煦,也直接以〈易象〉指稱《周易》。
直到現當代,還有很多學者仍然沿襲〈易象〉即是《周易》古經的觀點。如高亨先生就稱:「〈易象〉為書名,乃講《易經》卦爻之象,維護周禮,無可疑者。」陳居淵先生亦稱:「所謂〈易象〉,僅是當時《周易》的另一種稱謂而已,它並不神祕。其與今本〈象傳〉沒有直接關係。」
姜廣輝先生認為,在先秦時期,流傳有兩種不同內涵的《周易》,一為祕府《周易》,一為方術《周易》。祕府之《周易》為文王、周公所作,方術之《周易》與文王、周公無關。韓宣子聘魯所見〈易象〉,當是由文王創製、周公完成的今本《周易》。並引蘇蒿坪《周易通義·附錄》說:「〈易象〉屬周,故號《周易》,宣子以周公與周並言,原非專美周公也。」
正如李學勤先生指出的:「《左》、《國》屢次提到《周易》,有的全稱《周易》,有的簡稱為《易》,絕沒有稱之為〈易象〉的。由此可見,把〈易象〉說成《周易》並不合適。」而且在韓宣子之前,晉國也有用《周易》占筮的記錄。以此可知,《周易》一書在當時並不稀奇,而韓宣子也沒有必要在魯國見到被稱為《周易》古經的〈易象〉時,而發出「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王也」的感慨。因此,將〈易象〉解作《周易》,並不合乎常理。他由此得出以下的結論:
在《易傳》中,有專述卦象的〈說卦〉等篇,為說《易》者所必讀。可以推想,在《易傳》撰成以前,已經存在類似的講卦象的書籍,供筮者習用。這種書是若干世代筮人知識的綜合,對《易》有所闡發,是後來《易傳》的一項來源和基礎。《左傳》韓起所見〈易象〉,應該就是這樣一部書,係魯人所作所傳。
李學勤雖然認為〈易象〉「是後來《易傳》的一項來源和基礎」,但並沒有直接點明〈易象〉與〈大象〉的關係。
〈易象〉與〈象傳〉之間有無關係,一直是近現代易學研究專家重點思考的問題之一。學界兩種觀點並立,或明確否定〈易象〉與〈象傳〉有關,或認為〈象傳〉中的〈大象〉與〈易象〉的關係極其密切。
明確否定〈象傳〉與〈易象〉有關的學者,有高亨、黃沛榮、陳居淵等先生。高亨先生就此問題曾作過詳細的說明:
〈易象〉為書名乃講《易經》卦爻之象,維護周禮,無可疑者。《左傳》之〈易象〉與《十翼》之〈象傳〉其名同。《左傳》之〈易象〉與《十翼》之〈象傳〉皆講《易經》卦爻之象,其內容又同。但《左傳》之〈易象〉維護周禮,而《十翼》之〈象傳〉則兼有儒法兩家思想,其中無「周禮」字樣,其實質不同。況魯昭公二年(周景王五年、公元前五四〇年),孔丘僅十二歲,此時儒法兩家思想尚未形成,不可能出現反映儒法思想之〈象傳〉。
黃沛榮先生也否認〈易象〉與〈大象〉有關。他認為韓宣子所見之〈易象〉,「其內容如何,已難稽考,然絕非今傳之〈象傳〉。因〈象傳〉主要為孔門思想,從學術史言,絕不能早於孔子之世。而魯昭公二年,孔子年方十二,絕不可能有此作品」。
而陳居淵先生也明確指出:「〈易象〉與今本〈象傳〉沒有直接關係。」
但是當前學界,亦有不少學者認為〈易象〉與〈大象〉的關係極其密切。如廖名春先生就認為:「〈大象傳〉源於魯太史所藏之〈象傳〉。」他不僅對兩者之間的關係進行了細緻的分析,還對高亨先生的相關觀點進行了回應:
筆者認為,就像《魯春秋》與已修《春秋》一樣,〈易象〉與〈大象傳〉是有淵源關係的。第一是名稱一致。司馬遷稱:「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此「象」亦可稱為〈易象〉,它與《左傳》所載之〈易象〉名同,絕非偶然。第二是內容有關。所謂「周公之德」、「周之所以王」,就是敬德保民、謹慎戒懼的思想,認為「天命靡常」、「治民祗懼,不敢荒寧」、「無以水監,當於民監」,這從《尚書》的〈酒誥〉、〈無逸〉、〈召誥〉等篇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這些思想在〈大象傳〉中盈篇累牘,如「君子以反身修德」、「君子以恐懼修省」、「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等等。高亨先生認為,韓宣子所見之〈易象〉,絕非〈象傳〉。其理由是韓氏所見之〈易象〉,乃維護周禮之書,否則韓宣子就不會發出「周禮盡在魯矣」的感慨;而《十翼》之〈象傳〉無「周禮」字樣,又兼有儒法兩家的思想。且魯昭公二年,孔子僅十二歲,此時儒法兩家尚未形成,不可能出現反映儒法思想之〈象傳〉。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即使〈易象〉並非〈大象傳〉,但既然認為兩者「皆講《易經》卦爻之象,其內容又同」,那麼,絕對否認魯史所藏之〈易象〉與傳說中孔子所作之〈大象傳〉的淵源關係,是輕率的;第二,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源於周代的禮樂文化,是對周代禮樂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孔子甚至做夢都常夢見周公。因此,魯史所藏之〈易象〉有〈大象傳〉那樣的儒家思想,並不值得奇怪。〈大象傳〉有法家思想,就是所謂「明罰敕法」說、「折獄致刑」說,這些思想絕非法家的專利品,我們只要讀讀《尚書·呂刑》篇就會明白;第三,〈大象傳〉無「周禮」字樣並不能說它與周禮沒有關係,所謂「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君子以非禮弗履」、「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云云,能說它們與周禮毫無聯繫嗎?所以,韓宣子所見之〈易象〉絕非〈象傳〉說,是難以成立的。
鄧立光先生在廖名春先生觀點的基礎上,作了更進一步的探討。他認為《論語·憲問》中的「君子思不出其位」,「並不是孔子的教說,而是引用古語,此當為《艮卦·大象傳》,或即韓宣子所見的〈易象〉」。就〈大象傳〉與〈易象〉的關係而言:「應是〈大象傳〉源於魯太史所藏的〈易象〉」,「〈大象傳〉應當源出商末周初的周王室,而保存於魯國太廟。孔子應該讀過〈易象〉,因而改變了《周易》的觀點」
對於〈大象〉創作的時間研究,從德性的角度,並不能提出一個非常明確的答案,最重要的角度,應當以政治哲學為切入點,因為,政治變革有著非常鮮明的時代特色。我們知道,周人重德,從政治領域到個人的德性修養的要求,一直是周人的主流觀念。透過《尚書》中〈周書〉部分,以及出土的西周時期的彝器銘文,我們可以發現,當時上層統治者對於「德」的重視是一個非常普遍的情況,「德」不僅關乎天子王位的穩定性,同時「德」也是公卿士大夫獲復周王或諸侯冊命的重要標準。從現有的文獻我們可以看到,「德」在西周時期,是政治生活中的一個核心範疇,如果說儒家對於道德哲學的闡發,擴展到了人之為人的普遍性地位,那麼西周時人對於「德」的闡發,則貫通了上承天命,下及萬民的一個核心概念。「德」的重要性,比之於儒家單純的作為一種道德原則,更是關係到王權的合法性,關係到王位的傳承,諸侯之位的世襲,世卿家族的延續,是主宰西周政治生活的一個核心。周人制定的刑法制度,其核心思想是「明德慎罰」。而這一點,儒家並沒有關注的並不充分,儒家主張仁政,對於刑法的問題,甚少探討,以至於有些學者看到〈大象〉談「法治」思想就將其與法家結合起來,認為受到法家的影響。這些學者很少注意到,〈大象〉所提到「明德慎罰」思想在周初的典籍中,反覆出現。僅就文本的比較而言,〈大象〉與周人的法治思想更為密切,甚至可以說,〈大象〉的思想就是周王室法冶思想的直接承現,二者之間並沒有實質性的差別。因此,從制度的層面,結合〈大象〉所體現的治國理政思想與周王室治國思想的密切關係,我們認為〈大象〉與反應「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的〈易象〉一書關係,非常緊密。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君子觀象以進德修業:易經之《易大象》導讀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94 |
哲學 |
$ 439 |
中文書 |
$ 439 |
中國哲學 |
$ 439 |
Books |
$ 449 |
易經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君子觀象以進德修業:易經之《易大象》導讀
一種〈象傳〉與《周易》的全新解讀
〈大象〉原本單獨成篇,不與《周易》古經相合,鄭玄、王弼等易學家為研《易》方便,將其與古經及《易傳》其他諸篇合併起來研究。在易學史上,關於〈大象〉作者、創作年代、思想旨歸、與《易傳》其他諸篇的關係等問題,歷來眾說紛紜,至今尚無定論。主流觀點認為,〈大象〉是典型的儒家作品,或是孔子所作,或是出自儒家後學之手。但也有少數易學家認為,〈大象〉並非源自儒家,或是出自周公之手,或是出自周王室史官之手。
本書以先秦時期的典章制度、傳世文獻為據,認同〈大象〉與周王室關係密切的觀點,並試圖以這一觀點為指導思想,爬梳史籍、遍查出土文獻,探究〈大象〉與周王室之間的密切關係。
作者簡介:
彭鵬,國際易學聯合會學術部委員、周易研究會會員等,主要研究方向為易學史、儒家哲學。著有《解構與重建:胡煦易學研究》(博士學位論文),並在《哲學與文化》、《周易研究》、《孔子研究》等核心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
章節試閱
第二節 〈大象〉與〈易象〉
〈易象〉最早見於《左傳》一書。《左傳·昭公二年》載:「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什麼是〈易象〉?傳統觀點認為〈易象〉即是《周易》。而首倡此說者,是晉代的杜預。他在注解上段文字時說:「〈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
〈易象〉最早見於《左傳》一書。《左傳·昭公二年》載:「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什麼是〈易象〉?傳統觀點認為〈易象〉即是《周易》。而首倡此說者,是晉代的杜預。他在注解上段文字時說:「〈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代序
《象傳》以獨特的言說方式,對於《周易》古經的卦爻符號和文辭進行了系統解釋,成為易學家解《易》系統《十翼》中之一篇。易學史上,《象傳》被分為〈大象傳〉、〈小象傳〉。〈大象傳〉主要是從卦象來闡釋卦辭的社會倫理道德意義,即天道;然後措之於人事,即所謂「以物象明人事」,即人道。故就思維方式而言,〈大象傳〉反映的是古代「天人合一」的法象思維。〈小象傳〉則主要是以爻象的陰陽、剛柔、居位及其內在關係來解釋卦辭,即透過「觀象繫辭」將爻象與爻辭聯繫起來,揭示爻辭形成的依據,從而將言說具體事物的爻辭抽象化、...
《象傳》以獨特的言說方式,對於《周易》古經的卦爻符號和文辭進行了系統解釋,成為易學家解《易》系統《十翼》中之一篇。易學史上,《象傳》被分為〈大象傳〉、〈小象傳〉。〈大象傳〉主要是從卦象來闡釋卦辭的社會倫理道德意義,即天道;然後措之於人事,即所謂「以物象明人事」,即人道。故就思維方式而言,〈大象傳〉反映的是古代「天人合一」的法象思維。〈小象傳〉則主要是以爻象的陰陽、剛柔、居位及其內在關係來解釋卦辭,即透過「觀象繫辭」將爻象與爻辭聯繫起來,揭示爻辭形成的依據,從而將言說具體事物的爻辭抽象化、...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代序
上編:〈大象〉通論
第一章 〈大象〉概述
第一節 〈大象〉單獨成篇,不應與〈小象〉合為〈象傳〉
第二節 〈大象〉作者的歸屬
第三節 〈大象〉思想旨歸的多重解釋
第二章 〈大象〉與其他經典的關係
第一節 〈大象〉與〈彖傳〉
第二節 〈大象〉與〈易象〉
第三節 〈大象〉與「四書」
第四節 〈大象〉與〈月令〉
第三章 〈大象〉的擬辭體例
第一節 卦象擬辭
第二節 卦象與卦名
第三節 卦義與卦象、卦名
第四章 ...
上編:〈大象〉通論
第一章 〈大象〉概述
第一節 〈大象〉單獨成篇,不應與〈小象〉合為〈象傳〉
第二節 〈大象〉作者的歸屬
第三節 〈大象〉思想旨歸的多重解釋
第二章 〈大象〉與其他經典的關係
第一節 〈大象〉與〈彖傳〉
第二節 〈大象〉與〈易象〉
第三節 〈大象〉與「四書」
第四節 〈大象〉與〈月令〉
第三章 〈大象〉的擬辭體例
第一節 卦象擬辭
第二節 卦象與卦名
第三節 卦義與卦象、卦名
第四章 ...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