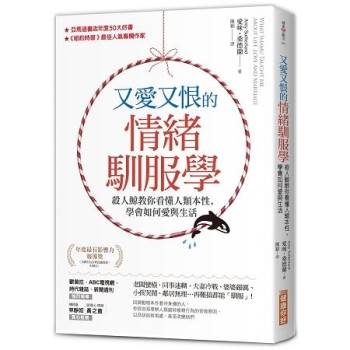本書旨在透過對視錯覺的解說,來探究大腦是怎樣知覺這個世界的。作者仔細說明各種視覺戲法與奇異現象,解釋科學家如何運用這些異象,來反推一般正常的知覺過程;並揭示大腦是如何運用精巧的技藝,來精準呈現我們這個真實世界─而這些都是我們每日體驗到,且視為理所當然的經驗。尤其特別的是,這些錯覺不僅說明了大腦目前怎樣運作,它甚至揭露了大腦過去的演化史─早期演化的痕跡像層次分明的地層仍深植在大腦中,經過演化的歲月而沉積下來;本書更指出各種錯覺研究是如何揭開這些地層面貌的。此外,本書在科學中還融入了對藝術與哲學的深刻思考,以及許多引人入勝的心理學實驗,更有一些讓人驚異的視覺現象。總之,本書闡釋了許許多多大腦的問題,這些都是長久以來困擾著無數科學家與哲學家的重要議題。
作者簡介:
Richard Gregory(1923-2010)
英國皇家學會院士。其著作有Eye and Brain、The intelligent Eye、Mirrors in Mind等;他是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Mind一書的編輯,也是期刊Perception的創始編輯。他先後任教於英國劍橋大學實驗心理學系、愛丁堡大學人工智慧與認知學系、以及布里斯托大學醫學院與心理學系,教授課程包括:知覺、神經心理學、實驗心理學、認知科學、人工智慧和科學研究法等。2010年5月去世前他是布里斯托大學神經心理學的榮譽教授。他另一名著《眼與腦:視覺心理學》(Eye and Brain: The Psychology of Seeing)被翻譯為十四種文字(中譯本由五南書局2006年出版,瞿錦春與張芬芬合譯)。《透視錯覺:由錯覺看世界》(Seeing Through Illusions)是這位大師去世前一年(2009)的最後力作。
譯者簡介:
瞿錦春
現職:
瞿眼科診所負責人
學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學士
中華民國眼科專科醫師
美國ECFMG考試及格
經歷:
臺北榮民總醫院眼科總醫師、專科醫師
空軍總醫院眼科主任
國防醫學院眼科臨床講師
張芬芬
現職: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教授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Ph. D.)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訪問學者
經歷:
國民中學、教育部、淡江大學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所長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主任
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秘書長8年、理事長4年
《課程與教學季刊》(TSSCI期刊)副總編輯(8年)、總編輯(4年)
學術專長:
質性研究方法論、教育研究法、課程與教學、潛在課程、教師專業發展、師資培育
章節試閱
第一章 知覺的派典
事實的真相是難以捉摸的;
哲學只是假像嗎?
對你是無意義的東西,
對我可能是真相,
這使得每件事都變得不確定了。
為何談錯覺?
奇怪、不尋常的東西或事件常讓人想知道答案,所以科學研究往往聚焦在這些怪異現象上。不僅是實體世界的怪現象引人探究,心理上的怪現象也會吸引人。錯覺(illusions)是一種知覺(perception)上的怪異現象,它挑戰了我們對現實的感覺。以往我們很少以科學的態度去看待錯覺;因為我們總認為錯誤是一個要避免的麻煩,而不是一個有趣的現象,但其實錯覺的發生正可以告訴我們知覺是如何作用的,同時也透露了大腦與心智的祕密。
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列舉各類錯覺,並探究它們的意義是什麼,以幫助我們瞭解大腦與心智。其中有一個中心議題,即對觀察及實驗結果的詮釋(interpretation)。詮釋與實驗發現(discovery)一樣重要,因為意涵來自詮釋而非來自現象本身。例如:將打雷與閃電視為來自諸神的憤怒,或只是凡德格拉夫放電機(Van de Graaff generator)上電荷的移動,兩者對雷聲與閃電賦與了截然不同的意涵。在某種程度上,現象必須詮釋為具有某種意義,且最好能連結到其他現象。而分類在科學中確實很重要,例如:對動物、植物、化學元素、天體等的分類,因為分類可以將現象與理論連結起來,而現象與理論的斷裂處則需要我們去尋求答案。本書將藉種類與原因來對錯覺現象做分類,並嘗試對錯覺現象賦予意義。
這本書名原文《Seeing Through Illusions》,它有雙重涵義,兩者間可以轉換,就如大家熟悉的「鴨-兔錯覺」(圖十六)。第一層意義是「由錯覺」看世界,這是將錯覺當做視覺的一種輔助方式,就像望遠鏡是一種補助工具,人們可透過望遠鏡去觀看世界;第二層意義是「透視錯覺」,這是將錯覺當做一種會騙人的把戲,本書想要看穿這些把戲。
心智無法同時持有兩種知覺或兩種意義。文字的諸多涵意或各感官的諸多知覺卻可以同時存在,或藉由上下脈絡來加以定奪。「由窗戶去觀看」(Seeing through a window)只意味一個大家熟悉的動作,但「監看一個計畫」(seeing through a project)所意味的動作就完全不同了,它意味著要從頭到尾一直看著。這本書的名稱意味著雙重涵意,因為錯覺會激發許許多多的知覺與想法,本書將逐一予以透視。
在「鴨-兔錯覺圖」中,大腦改變了我們的知覺,圖畫本身並沒有轉變。知覺不僅會隨著圖片轉變,也會隨著正常物體轉變。如此一來,對某些東西,我們看到的與知覺到的,是很不一樣的。這也表示知覺與外在物體並無直接關聯。因此,經由視覺看起來栩栩如「真」的東西,也許實際上全部都是錯覺。「看見」似乎是一件簡單而容易的事,但我們大腦皮質的功能卻有一半與解讀視網膜影像有關,這些功能耗掉了我們每日進食所產生能量的百分之四。
很明顯地,一直到十七世紀初,我們才知道視覺係源自視網膜影像。眼睛僅提供神經訊號,讓腦子去解讀外在世界。視覺訊號起自視網膜,視網膜乃由三層神經細胞所構成,它們均屬於大腦的突出物。起自視網膜的神經脈衝,沿著百萬根的視神經纖維傳到大腦,再由分工良好的組織結構加以解讀,而解讀必須利用腦子對物體所儲存的知識,所以我們看到的當下,其實是透過已往的知識來理解的,這其中有可能出現誤導。
經由視覺產生的錯覺現象,可能源自生理的(physiological)錯誤訊號,也可能源自知識的誤導,而造成了認知上(cognitively)的錯誤。生理的與認知的錯覺兩者起因不同,但有些看起來卻很相似,兩者常被混淆。生理的錯誤與知識的誤導,兩者的影響有時有驚人的相似性。但對於人們理解究竟發生何事,兩者的涵意卻截然不同,所以將它們做適當的分類是非常重要的。
對醫療工作而言,分類的重要性顯而易見。如果對生理或心理引起的頭痛分不清楚是可能會要人命的。就認知科學而言,混淆了「生理」或「認知」的知覺,將導致研究誤入歧途,並使得研究結果毫無意義。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應用上,科學的分類實在太重要了。
許多科學研究的重心是對現象做分析,做深入且細緻的分析。而把現象放在適當的位置去瞭解也同等重要。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與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的理論改變了天文學界與物理學界的想法,靠的是以新觀點聯結到大家熟悉的現象。愛因斯坦為了解釋一顆在顯微鏡下的花粉為何會持續亂竄,而開啟了一門新科學。這門科學起源於看似微不足道的觀察,愛因斯坦假定:花粉亂竄是被肉眼看不見的原子持續撞擊所致,愛因斯坦告訴了我們,原子不僅僅是數學上的概念,而且是活生生能產生作用的東西。從花粉的移動,愛因斯坦估計出原子的大小,進而導出了量子力學,對科學界產生的重大影響直到今日仍未稍減。愛因斯坦於1905年發表了現在大家熟知的「布朗運動」(Brownian movement),這讓他後來得到了諾貝爾獎。常常,一些微不足道的現象,藉由適當的觀念聯結到其他現象後,就變得非常重要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錯覺現象應該也不例外。
就如同美國的科學哲學家孔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中所說的,科學家常會接受當時盛行的假說,而不去質疑它。這就是孔恩所謂「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的基礎。就生物學而言,達爾文的物競天擇理論當然是主要的派典(paradigm),該理論對生命的每個嚴酷現實都賦與了意義。但心理學比較特殊,它不是個「常態科學」,因為它沒有眾議僉同的派典,它有的是彼此對立的「思想流派」,這些流派有著非常不同的假說與研究方法,彼此差別極大,可以從著重內省(introspection)到著重行為。
我們已指出:視覺牽涉到光學、生理學、訊息處理、解決問題、機率等因素。考量這種種因素,我們可以嘗試去找出一個派典,來瞭解我們是如何看東西,以及為何出現錯覺現象。當然,這不是件簡單的事,而且仍有揣測的成分在內。
用眾所周知的事實去挑戰另類派典,是一件有趣的事。我們可以對幾種相抗衡的派典打個分數,看看這些派典吸納每個待考驗的事實/現象(Gregory 1974)的能力有多強。然而這裡有個「循環」(circularity)弔詭—因為對事實與現象做了詮釋(interpretations)而產生含意,但詮釋根據的又是該派典。可見循環在科學裡的地位非常重要,但很明顯地,科學本身並不如它看起來的那麼「客觀」。
知覺是什麼?
有關知覺(perception)的各個派典,其間差異很大,例如:視覺是對實體世界的被動感應(passive reception);還是主動建構(actively construct)(如同探員以片段的證據拼湊出事件的全貌)?這兩者的觀點天差地別。本書的觀點是:知覺與行為的發展乃是從被動反應(我們稱之為感應〔reception〕),演化到主動建構出的成熟知覺(perceptions),然後再去猜測所看到的事物為何,這有點像科學研究中的預測性假說(predictive hypotheses)。
把知覺想成科學研究裡的假說,藉此說明知覺與有形世界的關係(間接也夾帶了許多猜測),這是相當不錯的解說方式;但這並未說明:經驗(experience)究竟是怎麼回事?科學裡的假說並無意識可言(我們只是假想成這樣)。我們認為大腦是一部極度複雜的、能產生假說的計算機,但這不能幫助我們思考有關意識的問題,因為人造計算機是沒有意識可言的。大腦是一部獨一無二的、具有意識的機器,世界上卻沒有一種人造機器,類似於知覺中感覺的感質(qualia)。因此意識是獨立自存的,在我們用科學的結構與意義去做類比時,意識乃是外在於這些類比的。就因為對意識沒有好類比可用,這便驅策我們進入哲學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希臘哲學家至少和我們同樣聰明。
有一個流行的說法:知覺就是腦子裡的圖像(pictures in the head)。這個說法合理嗎?
視覺的大腦是一本圖畫書嗎?
當我們看到一棵樹,此時在腦子裡會有一張像樹的圖片嗎?這個想法的問題出在:似乎腦子裡需要有一個像眼睛的東西去看這張圖片。而這又需要另一隻眼睛來看這個眼睛所看到的圖片,如此一個接一個的眼睛與圖片,不知將伊於胡底。雖然我們都有「心像」(mental images)這種經驗,但這並非意味者腦裡有圖像。
無論如何,眼睛裡確實有一圖像,但它從來沒被看到。視網膜上的影像為看提供了訊息,但這並不是影像本身被看到了。而更像一台電視攝影機將訊號傳到機器人的電腦裡,機器人可依這些訊息產生動作,但機器人腦子裡並沒有圖像。舉例來說,電腦裡的元件可以重現綠葉,但這些元件並不會是葉狀的,更不會在春天時變成綠色!同樣的,我們不能把聽到聲音,想成是腦子裡有聲音被聽到,否則這又會陷入腦內有聲音與耳朵的那個無限循環裡。
這個腦子裡既沒有這樣的聲音被聽到,也沒有這樣的圖像被看到。但這也無妨,如果機器人裡的電腦,對於攝影機傳來的畫面,可用簡單的特徵來做描述,並且用某種語言符號來做記錄,如此即可避免內在眼睛與圖片之間無盡循環的問題。然而這個大腦能像書中文字那樣,去進行表述(represent)或描述(describe)嗎?書是需要人眼去讀的,但一項描述並不像內在圖片那樣需要無數的眼睛與圖片—尤其是當這項描述已足夠清楚,而不需進一步描述即可運用之時。
大腦其實並未接收外界物體的影像,它接收的只是零碎的跡象,而可以讓人用這些跡象去推測或猜想外界的東西是什麼。大腦從各種感官接收到一些簡單特徵的訊號,從而創造出一些描述(description),再利用一些特殊腦神經細胞將此描述予以表述(representation)。所做的表述可能存在記憶裡,事實上,知覺與記憶的關係是很密切的。這裡有一重要的問題:眼睛和其他感官發出的訊號,具有什麼特徵,而能顯示外物的樣貌?科學家用極細的微電極來記錄腦神經的活動,他們發現大腦的迴路真的會對簡單特徵做回應(Hubel & Weisel 1962)。以英文字元A為例,這個圖形的表述可能由三種特殊神經迴路來進行:一是對右上斜線做反應,二是對左上斜線做反應,三是對水平線做反應。當然,對三條線的彼此相關位置也要予以表述。對電腦而言這並非難事,即使簡單的電腦也能辨認印刷或手寫字體,因為在其文字處理器中有一種光學特徵辨識系統(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OCR)。這種對所辨識的特徵做表述的觀點,並不會引發人腦或電腦內部圖像「無限循環」的問題。
文字可以表述物件,雖然它跟圖像表述有所不同。文字與它要表述的東西,無論是形狀、顏色、大小都很不一樣。CAT這個字的樣子與它所要表述的那種動物的樣子完全不同。當然,文字還能表述一些沒有形狀的抽象概念,如:「美麗」、「真實」、「聰明」、「有趣」。此處即引入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這是三百年前的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想過的問題:如果文字(words)本身的形狀、顏色與所要表述的東西可以大不相同,那麼感覺(sensation)(如:紅色、大聲)與它所要表述的東西為何不能大不相同?夏日天空的藍,一定要與天空本身的顏色一樣嗎?對天空的感覺所做的表述(represent),可能與實際截然不同,就像CAT這個字的形狀、顏色與大小,與它所要表述的動物是完全不同的。
洛克與牛頓(Sir Isaac Newton, 1643-1727)在十七世紀就已明瞭:顏色是被腦子創造(created)出來的。他們也知道光線與物體本身不是有顏色的—這在現在還是蠻讓人驚訝的。我們現在知道感覺(sensation)是在腦子何處產生的,但對於身體的大腦如何產生意識上的感覺(即感質〔qualia〕)仍然並不理解。
如果顏色與聲響不存於實體世界,而且它們與我們的經驗也大不相同,那麼所有知覺都是錯覺嗎(are all perceptions illusions)?湛藍的天空與震耳的雷聲都是錯覺(illusion)嗎?顏色與聲響確有其物理基礎,它牽涉到光的波長與空氣振動的能量,但這些物理現象與感覺卻完全是兩回事。
有時我們會說所有的知覺都是大錯覺,但這對知覺的瞭解沒有幫助。我們也可能被引導而說出:「每件事都是錯覺」。這樣說也沒有意義,就好像我們說「每件事都只是一場夢」。如果以「夢」或「錯覺」來形容每件事,「夢」與「錯覺」這些字也就無法產生意義了。我們需要一個與「看見」(seeing)相對的東西,也需要一個與描述(describing)及思考(thinking)相對的東西。如果我們宣稱此處有一種錯覺,則必然有一個相對的非錯覺(non-illusion)的東西存在。這種想法對其他領域也適用。如果每樣東西都是紅色,那麼我們說看到紅色的東西;甚或用「紅色」這個字,也就沒什麼意義了。
錯覺是什麼?
我們也許會說:錯覺是脫離真相(illusions are departures from reality)的,但真相是什麼呢?表面外觀與物理的深層真相是很不一樣的。如果將表面外觀視為真相,那麼我們就必須說:所有的知覺都是錯覺。但這與說「知覺是夢」一樣,對於知覺的認識並無助益。
錯覺可以用物理學的簡單常識來判斷,也可以用廚房裡的工具來測量,如:尺、時鐘、秤、溫度計等等。所以或許我們可將錯覺定義為:廚房物理學角度的誤差(deviations from kitchen physics)。
這種誤差是腦子在表述外物時所造成的。本書的主旨就是在闡明大腦對外物的表述只是一種假說(hypotheses),就好像科學裡的一種預測性假說一樣。如同做科學研究一樣,知覺根據現有的證據去猜測最可能的事實;同時也藉最可能的事實去評估該證據。除此之外,我們沒有其他任何確定性可言。
就科學與知覺而言,現象本身不能為自己說話(phenomena cannot speak for themselves)。現象必須經由詮釋(interpret)才能產生意義。推論並非直接根據現象或資料,而是根據詮釋(interpretations)。如此看來,科學並不如它所宣稱的那麼客觀。
就知覺而言,其中常常有許多的猜測以及超乎現有證據的作為。由此觀之,我們對外物最可能的認識,是倚靠著某種不確定的假說,而這一假說是根據現有的證據以及過去的知識。有些知識是遺傳而來的,它是經由物競天擇的統計式過程而習得,並儲存在物種的基因裡。其餘的知識,則是大腦從個人經驗中習得,這一部分對人類尤其重要。
我們應該簡要回顧一下知覺的演化史。我們談演化史,不僅僅「只是學術上」的興趣,而是因為這些過往的演化仍然留存在我們的神經系統裡。古老的行為模式仍深植於大腦中,只是某些已過時而不再被運用,於是它們被壓抑而不再活躍。一旦壓抑失效,它們便會被釋放出來,而喚起古老的知覺,此時出現的行為模式在現今生活裡會顯得有些怪異。由於這類行為模式起自遠古的老祖宗且未完全消失,所以認識它們是很重要的,藉由它們,我們也可瞭解神經學及相關疾病的症狀。對這類由於演化而在神經系統裡形成層層堆疊的行為模式,所進行的探究,被我們稱為神經考古學(neuro-archaeology)。
最簡單的生物體會對一組刺激做出反應,我們大致上可對這種反應做出預測,而它們所做的趨向或反射,在過去長久以來都算恰當—雖然現在看來未必恰當。較「高等的」生物,尤其是人類,比起低等生物來說,我們對其刺激的反應就較難預測了,而且也不太有規律性。這使得許多哲學家和科學家把人類—至少把人類的心靈—劃歸在科學之外。笛卡兒(Rene Descartes,1596-1650)在十七世紀時有一個著名的主張:我們的身體雖然是部機器,但我們的心靈卻沒有任何科學可以解釋。笛卡兒看見人類心靈與身體的差異是如此之大,所以他認為無法藉概念將兩者連接起來,也無法藉由科學上可被接受的類比來連結兩者。
上述看法最近有了改變,這無疑來自我們對電腦更瞭解了。因為電腦有著心靈所具有的許多不可思議的特質,諸如:電腦並不對輸入做出直接反應;有些電腦會啟動行為,像下棋電腦會選擇要移動哪一棋子;而且電腦會學習。有些電腦會看東西—雖然一點也不像人類的看;電腦也會用不同方式去聽、去摸、去嚐、去聞。而電腦的計算能力比人類快速得多,也更為精確。尤有甚者,某些電腦還能藉由習得的法則及內建的知識,而做出決定。從此,生物的大腦不再孤獨無伴了。
1830年Charles Babbage製造出機械式計算機,從此隨著數位科技的進步,人們越來越知曉「機器有其心靈」的觀念。即便是簡單的齒輪也能做「心算」(ental arithmetic^,這個理解從十七世紀中葉就有了,直到如今我們也仍然在談心(mental)算,這確實是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雖然在細節處,大腦跟現有的電腦還是很不一樣,但由於我們對兩者的認識,已使我們比過去更容易接受「心靈住在機器中」、「大腦是個機器」這類的想法。不過,電腦軟體與聰慧心靈仍然帶著鬼魅般讓人驚嚇的特質,這些特質會縈繞在人們心頭而令人害怕。
什麼是認知知覺
簡單生物是對刺激做出直接反應,而「高等」生物則是對刺激的原因(cause)先做猜測,然後才有行為反應。物種從對刺激直接做出反應,到對可能的原因做出計畫性的行為,再到對結果進行預測,我們可以說:這一過程是物種從原始的感應(reception),進步到成熟的認知知覺(cognitive perception)。稱其為認知,是因為這種知覺需要知識,亦即對外物世界的知識。
這種知識是默會內隱(implicit)的,我們可從知覺與行為的試驗中辨識出來這種內隱知識,某些誤導的幻覺可以為內隱知識的存在提供證據。這些知識可能是關於某特定(particular)物件(如:某人的大門鑰匙),也可能是適用所有物件的通則(general rules)(如:透視性的內聚線條代表物件在空間中的某種距離)。我們可以用一張圖(圖一)來顯示大腦的認知過程可能是如何組織完成的。此圖引介了一些非標準化的專有詞彙(但仍與現在所瞭解的大腦解剖相符合),這些詞彙主要係根據知覺與行為的現象而產生的。
我們可以將視知覺(visual perception)定義為影像的歸屬物(attributing objects to image)。此歸屬物來自知識、以往的經驗,及其相關機率(probability)。如果觀看者覺得看見的機率是零,我們是看不見該物件的。而嬰兒天生就有一些知識,這使得他/她的知覺有了一個最初的起點。
第一章 知覺的派典
事實的真相是難以捉摸的;
哲學只是假像嗎?
對你是無意義的東西,
對我可能是真相,
這使得每件事都變得不確定了。
為何談錯覺?
奇怪、不尋常的東西或事件常讓人想知道答案,所以科學研究往往聚焦在這些怪異現象上。不僅是實體世界的怪現象引人探究,心理上的怪現象也會吸引人。錯覺(illusions)是一種知覺(perception)上的怪異現象,它挑戰了我們對現實的感覺。以往我們很少以科學的態度去看待錯覺;因為我們總認為錯誤是一個要避免的麻煩,而不是一個有趣的現象,但其實錯覺的發生正可以告訴我們知覺...
目錄
致 謝
第一章 知覺的派典
為何談錯覺?
知覺是什麼?
視覺的大腦是一本圖畫書嗎?
錯覺是什麼?
什麼是認知知覺
貝葉斯機率
認知的演化
由感應到知覺
現象不會為自己說話
第二章 神經考古學
Jean-Baptiste Lamarck:大腦的知識是遺傳而來的嗎?
John Hughlings Jackson:大腦層狀結構的功能考古
Ernst Haeckel :演化的重演
Arnold Gesell :行為的胚胎學
與過時的遺傳知識共生
演化心理學
什麼是先天遺傳?
語言
看到過去
動作與觀看
第三章 開光
各種眼與腦的起源
達爾文的寒顫
從觸覺到視覺
是主動與被動的觸覺造就了單眼與複眼嗎?
掃描式的眼睛
人眼
第四章 解讀洛克
意義
重要性
第五章 種類與起因
生理—心理學之間的連字號
來自錯覺的真相
圖片
感覺
錯覺的種類與起因
第五之一章 目盲:由無感到無意義
從盲眼到重獲視力
嬰兒知道了什麼?
適應
消失的條紋
心盲
忽略或拒絕看到
對改變的視而不見
大腦皮質引起的目盲
訊息理論
資訊的極限
知識是什麼?
第五之二章 惱人的曖昧不明
閾值
對比錯覺
暗黑
顏色對比
第五之三章 翻轉的曖昧不明
圖形-背景
翻轉的物體
深度的翻轉
Mach角落
凹陷的臉孔
視網膜對抗
口語變化
翻轉現象的意義為何?
繪畫中的曖昧
第五之四章 不穩定
歐普藝術與所有的眩目畫
幻影乒乓球
搖晃的鉛筆
搖擺的風車
視網膜對抗
光澤
等亮度
移動的經驗
自體運動效應
被引發的移動
移動階梯效應
運動視差
深度相反視差
偽視差
實景中的移動錯覺
OHO臉孔與上下顛倒的書寫
柴契爾錯覺
第五之五章 扭曲錯覺
訊號錯誤
認知扭曲
第五之六章 虛構
後像
輪廓
幻想的輪廓
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
赫曼方格
看到自己的盲點
第五之七章 矛盾
不像與不可能
經驗上的不可能
知覺上的矛盾
知覺訊號的矛盾
冷與熱
Shepard音調
認知矛盾
動物的錯覺
第六章 結語:從知覺到意識
標示當下
一項自我實驗
某些能「證明規則」的例外
參考書目
附錄 錯覺分類總表
索引
致 謝
第一章 知覺的派典
為何談錯覺?
知覺是什麼?
視覺的大腦是一本圖畫書嗎?
錯覺是什麼?
什麼是認知知覺
貝葉斯機率
認知的演化
由感應到知覺
現象不會為自己說話
第二章 神經考古學
Jean-Baptiste Lamarck:大腦的知識是遺傳而來的嗎?
John Hughlings Jackson:大腦層狀結構的功能考古
Ernst Haeckel :演化的重演
Arnold Gesell :行為的胚胎學
與過時的遺傳知識共生
演化心理學
什麼是先天遺傳?
語言
看到過去
動作與觀看
第三章 開光
各種眼與腦的起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