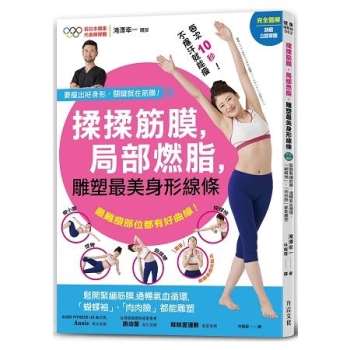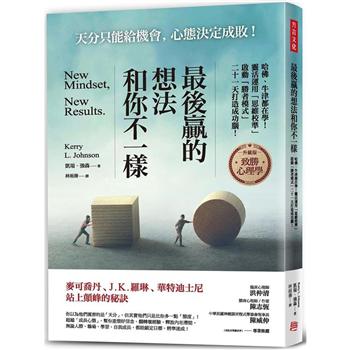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瞧,這個人!:尼采自傳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03 |
西方哲學 |
$ 203 |
哲學 |
$ 213 |
西方哲學 |
$ 213 |
Books |
$ 243 |
德奧哲學 |
$ 243 |
社會人文 |
$ 251 |
中文書 |
$ 257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瞧,這個人!:尼采自傳
內容簡介
德國哲學家尼采深深地影響了二十世紀的文學、哲學、文化、乃至政治的發展,不僅成為不同領域中崇拜的對象,也是思想史上無法繞過的存在。尼采曾預言:「將來有一天,人們會需要一些機構,在裡面生活,並傳授我對生活與教導的理解;也許還會設立專門的教職教人怎麼詮釋《查拉圖斯特拉》。」回顧尼采身後的整個世紀,他的這段預言顯然早已應驗。1888年,44歲的尼采在陷入瘋狂之前完成了本書,為自己的思想與著作做了總結性的解說。看似狂妄自大的字裡行間,埋藏著許多狡黠的觀察與思辨,時而精辟入理,時而辛辣諷刺,不斷透過排山倒海的重磅轟炸貫徹尼采自己的核心思想:「重新評價所有的評價。」在尼采面前,一切的既定價值──包括德意志精神──皆免不了灰飛煙滅。如果想要了解尼采其人與其著作,一定不可不「瞧,這個人!」,瞧他如何獨立於世,瞧他如何完成自己的使命,在虛無中奪回人性的價值。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
德國著名哲學家、語言學家、文化評論家、詩人和作曲家。尼采的思想對在其之後的哲學有非常大的影響。
尼采在1867年曾經自願從軍,一年後因為車禍退出軍隊。1869年獲得瑞士巴塞爾大學的古典哲學教授職務。
尼采在1879年因為健康問題辭去在瑞士巴塞爾大學的教授職務,此後為精神疾病所困,在1889年精神崩潰後沒有再恢復健康,直至1900年因肺炎去世。
尼采最著名的著作除了《瞧!這個人》,《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以外,另有《悲劇的誕生》、《不合時宜的考察》、《人性的,太人性的》等多本著作。
譯者簡介
萬壹遵
1985年生,德國波鴻大學德語文學博士,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專任副教授。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
德國著名哲學家、語言學家、文化評論家、詩人和作曲家。尼采的思想對在其之後的哲學有非常大的影響。
尼采在1867年曾經自願從軍,一年後因為車禍退出軍隊。1869年獲得瑞士巴塞爾大學的古典哲學教授職務。
尼采在1879年因為健康問題辭去在瑞士巴塞爾大學的教授職務,此後為精神疾病所困,在1889年精神崩潰後沒有再恢復健康,直至1900年因肺炎去世。
尼采最著名的著作除了《瞧!這個人》,《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以外,另有《悲劇的誕生》、《不合時宜的考察》、《人性的,太人性的》等多本著作。
譯者簡介
萬壹遵
1985年生,德國波鴻大學德語文學博士,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專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