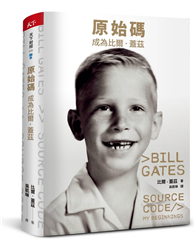闡述巫術和宗教起源的權威之作
人類學的的百科全書
本書自1890年問世以來,就受到了來自各方的質疑,但它經受了時間的考驗。《金枝》緣起於一個古老的地方習俗:金枝是柏樹或橡樹上帶有金色樹葉的斷枝,該樹在女神戴安娜(Diana)建造的庇護所,位於奧爾本山(Alban Hills)附近的古代火山湖周圍。在古羅馬神話中,有了金枝可以幫助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Aeneas)出入地下世界。那些大樹也被認為是在羅馬人之前統治這個地方的古拉丁人的神。
在拉丁人的古老習俗中,金枝是僧侶王的權利象徵。任何人即使是奴隸或囚犯只要摘取了該金枝就可以和國王決一死戰。而在決鬥中,如果戰勝並殺死國王,那麼他就是該部落新的首領。這個古老習俗的緣起與存在疑點重重,為此,作者目光遍及世界各地,收集世界各民族的原始信仰等資料,進行系統的梳理,從中抽繹出一套嚴整的體系,並對巫術的由來與發展進行比較分析,並揭示了人類思維進化的共同軌跡。西方知識界普遍認為,《金枝》對學術的貢獻,足以媲美修斯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
作者簡介:
詹姆斯‧喬治·‧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1854年1月1日—1941年5月7日),出生於英格蘭的格拉斯哥,是英國著名的人類學家和民俗學家、神話學和比較宗教學的先驅。
弗雷澤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神話和宗教。他進行研究工作的主要來源是浩如煙海的史料文獻,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調查表。弗雷澤在人類學上的啟蒙者是人類學開創者愛德華·伯內特·泰勒,還有泰勒的那本名著《原始文化》(1871)。弗雷澤一生的研究盡在金枝一書。《金枝》第一版出版於1890年,包含兩卷內容, 1915年第三版出版時擴充到十二卷。
譯者簡介:
徐育新(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人員,已故)。
汪培基(1926年12月─2012年9月)出生於安徽省繁昌縣 ,中國藝術研究院譯審、資深翻譯家。曾就職於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對外部。
翻譯該書中的原作者《前言》、第7章至第22章、第29章、第43章、第60章至第69章、索引;又補譯了徐育新譯稿中漏譯的約四萬字。此外,還對全書進行了統一的校譯和潤色,撰寫了絕大部分的注釋。
張澤石(1929年7月-),生於上海,四川廣安人。1951年隨軍入朝鮮參加抗美援朝,因部隊陷入重圍負傷被俘,被俘後曾任志願軍戰俘總代表總翻譯。
章節試閱
第五十八章 古羅馬、古希臘的替罪人
第一節 古羅馬的替罪人
現在,我們可以來考察古羅馬時期用人來替罪的做法了。每年的3三月十四14日,一個披著獸皮的人被領著在羅馬街上遊行,用白色的長棍子打他,把他趕出城外,人們稱他為馬繆裡里烏斯.維圖里裡烏斯,意即「老瑪爾斯」。 瑪爾斯是羅馬神話中的戰神和農業之神。既然這個儀式是在舊羅馬年((3三月1一日開始))頭一第一個月圓的前一天開始,披獸皮的人想必是代表舊年的瑪爾斯,在新年開始時被趕走。而瑪爾斯在起初是植物的名稱,並非戰神。古代羅馬農民就是向瑪爾斯祈求穀物、葡萄、果樹和樹林豐收繁茂的,阿爾沃兄弟神學院578所做的工作就是為穀物的生長向神祭祀,他們幾乎完全是向瑪爾斯進行祈禱,據我們所知,為了獲得豐收每年10十月都向瑪爾斯獻祭良馬一匹。而且,農民為求牲畜興旺也是用「林中瑪爾斯」((Mars Silvanus))的名義祭祀瑪爾斯。我們已經說過,通常認為牲畜特別受到樹神的保護。而且,把春天的3三月獻給瑪爾斯似乎表明示他是發芽的植物之神。如果我們對斯拉夫民族「送走死亡」的風俗的看法是正確的,那麼,羅馬在新年之初驅除舊瑪爾斯的風俗與斯拉夫「送走死亡」的風俗就是同一回事。有些學者已經說過羅馬與斯拉夫風俗的類似,不過,他們好像是把馬繆里裡烏斯.維圖里裡烏斯同與斯拉夫儀式中與之相應的偶像都當作舊年的代表,而不是舊植物神的代表。很可能後世奉行這種儀式的民族也是這樣理解的。但是,只是在某一段時期內的擬人化,這種觀念太抽象了,不可能是原始人的觀念。不過羅馬儀式和斯拉夫儀式一樣,不僅把神的代表當作植物神,而且也當作替罪羔羊。驅除神的代表就暗示著這一點,因為除此之外沒有理由把這樣的植物神從城裡趕走。如果他又是替罪羊,那就不同了,就必須把他趕出城區,使他把負擔的罪惡帶到別處去。事實上,馬繆里裡烏斯.維圖里裡烏斯似乎是被趕到羅馬的敵人奧斯塔人古代奧斯塔人住在義大利南部地區坎帕尼亞。 住的地方去了。
第二節 古希臘的替罪人
古希臘也熟知利用替罪人的做法。在普盧塔克的故鄉凱羅涅亞城,由行政長官在市鎮廳內主持這種儀式,各家家長則在自己家裡主持,這種儀式叫作「驅除饑荒」。做法是用西洋牡荊的枝子鞭打一個奴隸,把他趕出門外,並且說道:「饑荒滾出去,財富健康請進來。」普盧塔克擔任故鄉的市鎮長官時,在市鎮廳裡主持這種儀式,他還記敘了後來這個風俗引起的爭論。
但是,後來在開化了的文明的希臘,替罪的風俗比溫和、虔誠的普盧塔克主持的替罪儀式顯得更陰森一些。希臘最熱鬧、最明媚的殖民都市之一——馬賽,一遇到瘟疫流行就有一個出身窮苦階層的人自願來做替罪羔羊。人們用公費整整養他一年,拿精美的食物給他吃。一年期滿時就讓他穿上聖衣,用神枝裝飾起來,領著他走遍全城,同時高聲禱告579讓人們把全部災害都落在他一人頭上。然後把他扔出城外,或在城牆外由人們用石頭把他砸死。雅典人經常用公費豢養一批墮落無用的人,當城市遭到瘟疫、旱災或饑荒這一類的災難時,就把這些墮落的替罪羔羊拿出兩個來獻祭:一個為男人獻祭,另一個為婦女獻祭。;前者在頸上圍一串黑無花果,後者圍一串白無花果。有時候獻祭的為婦女,而殺祭的人犧似乎也是個婦女。先領他們走遍城裡,而後殺祭,顯然是在城外利用石頭砸死的。但是,這種祭祀不限於大規模災禍的特殊場合,似乎每年5五月薩格裡里亞節都要把兩個人犧((一個為男人,一個為婦女))領出雅典城外,用石頭砸死。色雷斯的阿蔔卜德拉城每年大規模地清城一次,並為這個目的專門選出一個市民用石頭把他砸死,作為替罪羊,或代替所有其他人作出生命奉獻。在砸死他的六天前先除去他的市民資格,「以便讓他一人負擔全市民眾的罪孽,而不至連累其他市民」。
盧卡迪人每年從他們島上南端一堵白色懸崖「情人崖」上把一個囚犯扔到海裡去,作為替罪羔羊。但是,為了減緩他的降落,人們在他身上拴上幾隻活鳥和羽毛,崖下有一隊小船,等著接他,把他送出邊界。這些仁慈的預防工作也許是早先把一個替罪羔羊扔到海裡去淹死的緩和做法。盧卡迪人的儀式是在祭祀阿波羅時舉行的,那裡有一座阿波羅的廟宇或神殿。在其他地方,慣例是每年把一個年輕人扔到海裡去,咒他一句:「你是我們的廢物。」據說這種儀式是解除人們所受邪惡的困擾,或者,根據另一略有不同的說法,這個儀式是為人們贖罪的,償還人們欠下海神的債務。紀元前6六世紀小亞細亞希臘人中流行替罪羔羊風俗是這樣的:當城裡受到瘟疫、饑荒或其他規模災害時,就選一個相貌醜陋或畸形的人,讓他承擔擾亂整個社會的一切邪惡。把他帶到一個適當的地方,把幹乾無花果、大麥麵包和乳餅交給他手裡,讓他都吃掉。然後用綿棗、野生無花果的枝子和其他的野樹枝,隨著笛子吹奏的一種特殊的曲調,抽打他的生殖器官七遍,然後用林中的木料搭起一個火葬堆把他燒掉;他的骨灰扔到海裡。亞洲的希臘人每年在薩格裡里亞收穫時似乎也有與此類似的風俗。
在方才描述的儀式中,用綿棗、野生無花果枝子等等抽打人犧,其目的不可能只是為加重他的痛苦,否則,580用任何棍子打他都成。W. 曼哈德解釋過這一部分儀式的真正意義。他指出古人認為綿棗有抵擋邪氣的魔力,因此他們把它掛在家的大門上,在潔淨儀式中應用綿棗。所以,在某個節日上,或在獵人空手回家時,阿卡迪人有一個用綿棗抽打潘的塑像的風俗,這不是要懲罰神,而是要清除它身上的一種邪氣,這種邪氣妨礙它行使聖職,它本是給獵人供應獵物的神。同樣,用綿棗等物打人身替罪羊,其目的想必也是為了解放它的生殖力,使它不受魔力或其他邪氣的束縛或影響,每年殺祭它的時日是薩格裡里亞節,是在5五月舉行的早期收穫節,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它是代表增殖植物神的。每年殺神的代表,目的是我已指出過的要保持神靈生命永遠精力充沛,不受年老體弱的沾染,在將他處死之前,刺激他的增殖力,使之充分活躍地傳給他的繼承者、新神或老神的新的體現者,這也是很自然的。毫無疑問,人們認為他立即取代被殺者的地位。類似的推理導致在旱災或饑荒的特殊時節對替罪羔羊的類似處理。如果收成不符農夫的期望,那就把這一點歸咎於某神失去了增殖力,這個神的職能就是要產生大地的果實的。人們可能以為他是邪氣附體或年老體弱,因此舉行上述種種儀式,通過透過殺死他的代表人來把他殺掉,使他重生,年輕力壯,可以把他的旺盛精力轉輸給精疲力竭的自然。按照同樣的原則我們就能夠理解用樹枝抽打馬繆裡里烏斯.維圖里裡烏斯的原因、在卡羅尼亞儀式上用西洋牡荊((據說該樹有魔性))抽打奴隸的原因、歐洲某些地方用棍子和石頭攻打死亡偶像的原因,以及在巴比倫代表神的囚犯在釘死前受到抽打的原因。抽打的目的並不是要增加神靈受難者的痛苦,恰好相反,是要驅除邪氣,在臨死前的這個重要時刻,他很可能受到邪氣糾纏。
我一直假定薩格里裡亞節的人犧一般是代表植物的精靈的,W. R. 佩滕先生也早就說過:這些可憐蟲似乎專門扮作無花果樹的精靈。他指出所謂的人工授粉((也就是說,拿一串串野無花果掛在栽培的無花果樹枝上,581進行人工授粉))的過程是在6六月裡,大約在薩格裡里亞節後一個月左右。這在希臘和小亞細亞都很流行。他提出,兩個人犧,一個代表男人,一個代表婦女,把黑的和白的無花果掛在兩個人犧的脖子上,可能是根據巫術的類比原則,直接仿效人工授粉來説明無花果樹受粉的。事實上,授粉既然是雌雄無花果樹的接配,所以佩滕先生進一步假定,根據同樣的巫術類比原則,樹木的婚配可以通過透過仿效婚配而得到促進,甚至可以得到兩個人犧((其中一位有時似乎是女的))的真正婚配的促進。按照這種看法,用野生無花果樹的枝子和用綿棗抽打人犧的做法就是一種巫法,其意圖是要促進男人和婦女的生殖力,他們當時是分別代表雌雄無花果樹的,通過透過他們的兩性結合,無論是真正結婚或是假結婚,都能夠幫助這些無花果樹結出果實。
有許多類似的例子可以證實我們提出的對用某種植物抽打人身替罪羊的風俗的解釋。如在德屬新幾內亞的卡伊族人中,某人如希望他的香蕉樹苗快快長出香蕉,他就從已經結果的香蕉樹上砍一根枝子打這些香蕉樹苗。這個例子很明顯,他是相信豐產力灌注在從已結果的樹上砍下的枝子上,由於接觸而傳給了幼小的香蕉樹。同樣,在新赫里多尼亞,有人用枝子輕輕敲打芋頭,邊敲邊說道:「我打這棵芋頭是使它快生長」,然後,他把枝子插在田頭的地上。亞馬遜河口的巴西印第安人中,有人想要自己的生殖器長得形體很大,就用河岸邊盛長的白色水生植物蓮花((aninga))敲打自己的生殖器。這種果實形狀很像香蕉,並不能吃,之其所以選用它來敲打,顯然是取其形狀碩大肥美。敲打的儀式必須在新月前三天或三天之後進行。在匈牙利的貝凱什州,人們用第一次打散正在交配中的公母狗的棍子敲打不孕婦女。這種做法清楚地表明現出人們以為狗的生殖力傳到打她的棍子上,婦女接觸到那棍子,也就獲得了生殖能力。中西里裡伯斯的托拉傑人認為朱蕉(Dracaena terminalis)有一個強壯的靈魂,因為它修剪過後,它立即又長出來。所以,有人病了,他的朋友有時就用朱蕉的葉子打他的頭頂,為的是要用其強壯的魂魄來增強他虛弱的魂魄。
上述這些舉例證實了繼我前輩W. 曼哈德和W. R. 佩滕先生之後,我對於希臘薩格裡里亞收穫節上的抽打人犧那種做法所作的解釋。把用新鮮的綠色樹苗或枝子抽打人犧生殖器官的做法解釋為一種巫術,是再自然不過的了!那樣做的目的就是要增加男人或婦女的生殖力,或是把植物的增殖力傳給他們,582或是消除他們身上的邪氣。這個解釋也為下述情況所肯定:代表兩性的兩個人犧中,一個代表一般的男人,另一個代表婦女。舉行節日的季節也就是穀物收穫的時候,正好與儀式具有農業意義的理論相符合。而且,人犧的頭上掛著成串的黑白無花果,以及用野生無花果的樹枝鞭打他們的生殖器,也強烈地表示了儀式的意圖是要使無花果樹增殖,這種做法與古代和近代希臘土地上的農夫的做法極為相似。農夫常常採取這種辦法,想使他們的無花果樹真正授粉豐產。椰棗的人工授粉不僅在美索不達米亞的農業中而且在它的宗教中都似乎佔占據很重要的地位,我們如果還記得這一點,那就似乎沒有理由懷疑無花果人工授粉也可以在希臘宗教的莊嚴儀式中占一席地位。
如果這些考慮正確的話,我們就必須明確地得出結論:古代羅馬希臘的後期,薩格裡里亞節上出現的人犧的確是以公眾替罪羊的身份身分為主,他們把全民的罪過、災難和憂愁隨身帶走,而在更早的時候,人們可能把他們當作植物精靈的化身,也許是穀物的化身,尤其是無花果樹的化身,鞭打他們、殺死他們的目的主要是加強和更新當時希臘夏天酷熱下已經開始衰謝的植物的生長力。
這裡對希臘替罪羊所持的看法如果正確的話,他可以預先防止對於本書主旨的反對意見,這種反對意見如不加以防止,是很可能提出來的。關於阿裡奇亞阿里奇亞的祭司是以樹林精靈的代表而被殺的理論,可以提出反面的意見說:這種風俗在古代希臘羅馬並無旁證。但是現在已經提出令人相信亞洲希臘人定期地或不定期地殺祭的人,照例是被當作植物神的替身看待的。雅典人養的一批供作獻祭的人犧可能也同樣被當作神靈。至於他們是社會渣滓這一點並沒有多大關係。在原始人的觀點看來,選擇某人作為神的代言者或替身並不因為他有高尚的道德素質或社會地位,神的諭言對於人不分好壞貴賤都是一樣。如果那時文明的亞洲希臘人和雅典人一貫殺掉他們認為是神化身的人,那麼,我們假定在歷史的啟蒙時期,阿裡奇亞阿里奇亞叢林中的半野蠻的拉丁人也遵行類似的風俗,並不是一定不可能的。
但是要確定這個論點,顯然還需要證明,583在古代義大利,除了阿裡奇亞阿里奇亞的聖林而外,其他地方也有殺死神的人身代表的風俗,別處也有並且也遵行這樣的風俗。下面我就將提出這方面的證據。
第三節 古羅馬的農神節
我們談到過,許多民族曾經每年都有一個放肆的時期,這時法律和道德的一貫約束都拋開了,全民縱情地尋歡作樂,黑暗的情欲得到發洩,這些在較為穩定、清醒的日常生活中,是絕對不許可的。人類天性中被壓制的力量這樣突然爆發,常常墮落為肉欲罪惡的狂歡縱飲,這種突然爆發大都是在一年結束的時候,而且像我所指出的,常常與農業季節相關聯,特別是在播種和收穫的時候。所有這種放縱時期中最著名的一個,也是在現代語言中為這種時期擬定的總名稱,就是薩圖納裡里亞——農神節。這個著名的節日是在每年的12十二月,即羅馬曆一年的最後一個月裡,民間認為這是紀念薩圖恩的歡樂盛世的。薩圖恩是播種和收穫的神,在很古的時候他活在人世上,是義大利的一個為人正直、予人福澤的國君。他把崇山中粗獷零落的住戶聚集起來,教他們種地,為他們制定法律,他的統治是個太平盛世。他在位期間就是傳說中的黃金時代:大地出產豐富,沒有干戈爭執之聲驚動這個幸福世界,沒有貪財愛利之人的欲望像毒藥一樣侵害勤勞、知足的農民的血液。奴隸制和私有財產都不存在,一切東西大家公有。後來,這位好神,這位仁君突然不見了,人們感于於它的恩澤時時刻刻都在懷念它,立了祭壇供奉它,義大利的許多山、許多高地都用它的名字命名。不過,關於它的統治的光輝傳說故事,後來竟蒙上一道陰影:據說,他的祭壇沾染著人犧的鮮血,直到後世也說仁慈的時代才用偶像代替了人犧祭獻。在古代作家流傳下來的關於農神節的描述中,對這位神的宗教方面的這個陰暗面卻沒有留下什麼痕跡,甚至毫無痕跡。宴會、飲酒、種種瘋狂的尋歡作樂,似乎特別標示出這個古代狂歡節的特點,這個節日在古羅馬的街道上、公共場所和住宅中舉行,一連七天,從十二12月十七17日到十二12月二十三23日。
但是,節日中最引人注意的特點,使古人自己都覺得最驚人的,莫過於允許奴隸放任自由。自由民階級和奴隸階級之間的區分暫時廢除了。奴隸可以罵他的主人,可以像他的上司一樣醉酒,可以和他們同坐一起吃飯,奴隸有些行動在任何別的時候都會使他受到鞭打、囚禁或死刑,584但這時連罵都不罵他一句。不僅如此,主人實際和他們的奴隸互換位置,主人在吃飯時侍候他們,要等到奴隸吃好喝足之後,才清理飯桌給主人擺飯。等級的倒換對調竟達到這種程度,每家暫時成了一個小共和國,國家的最高職務由奴隸掌管,他們發號施令,制定法律,好像他們確實具有政權、軍權、司法權的一切尊嚴。農神節期間自由民也可以抽籤拈鬮、假充國王,享受一點微弱權力,跟奴隸們節日期間從奴隸主那裡獲得一點權力一樣。中鬮籤的人暫時擁有國王的稱號,對他們的臨時臣民發出的號令具有玩笑取鬧的性質。他可能命令某人伴酒、某人喝酒、某人唱歌、某人跳舞、某人責備自己、某人把一個吹笛的姑娘女孩背著繞屋走一圈。
人們認為在這個節日允許奴隸自由是模仿薩圖恩時代的社會狀態,一般人覺得薩圖納裡里亞節((農神節))不多不少,恰好是那個快樂君主統治的暫時復活或恢復,我們如果記住這些情況,就不由得要假定主持吃喝笑鬧的假王起初是代表薩圖恩本人的。在馬克西米安和戴克裡里先統治的時代,有一些羅馬士兵駐紮在多瑙河上。有一篇非常奇怪、有趣的記載,記述這些士兵是怎樣過農神節的。這篇記載如果沒有把上述假定當作事實,那也是極高度地肯定了這個假定。這些記載保存在一篇關於聖達修斯殉道的記述中,這篇記述是由根特的弗朗茲.庫蒙特教授從巴黎圖書館的一批希臘手稿中翻檢出來而發表的。在米蘭和柏林保存的手稿中也有關於這件事和這個風俗的較短描述。其中一段已經在一七二七1727年烏爾比諾印行的一本不知名的書中刊印問世,但是這段記敘對於古代和現代羅馬宗教史的重要性一直被忽視了,直到庫蒙特教授在幾年前將這三篇記述同時發表了,才引起學者們注意。這三篇記述從各方面看都是真實的,其中最長的一篇可能是根據官方文獻寫出的。根據這些記述,駐紮在下莫西亞的杜羅斯托羅姆地方的羅馬士兵每年是用下述方法過農神節的。節日前三十天,他們用抽籤的辦法,在他們當中選一個漂亮的年輕小夥子,於是他學薩圖恩的樣穿上皇服,由一群士兵陪他上街遊逛,他有充分的自由,放縱情欲,領略各種樂趣,不論其有多麼卑鄙可恥。他享受王權統治雖然很快樂,但為時不長,且下場悲慘,因為三十天的時間一到期,農神節來到,他就得在他所扮演的神的祭壇上刎頸自殺。在西元三○三303年,有一個基督教徒士兵達修斯中了簽籤,但是他不願意扮演異教的神,讓淫樂污汙染他最後的一段生命。他的長官巴瑟斯又是威脅又是論述,585終究不能無法動搖他的堅定意志,因此將他斬首。基督教殉教史的作者詳細準確地記述道:十一11月二十20日,即陰曆二十四日,星期五,淩凌晨四點鐘,在杜羅斯托羅姆鎮,由士兵約翰行刑。
(文中阿拉伯數字是書中的注文編號)
第五十八章 古羅馬、古希臘的替罪人
第一節 古羅馬的替罪人
現在,我們可以來考察古羅馬時期用人來替罪的做法了。每年的3三月十四14日,一個披著獸皮的人被領著在羅馬街上遊行,用白色的長棍子打他,把他趕出城外,人們稱他為馬繆裡里烏斯.維圖里裡烏斯,意即「老瑪爾斯」。 瑪爾斯是羅馬神話中的戰神和農業之神。既然這個儀式是在舊羅馬年((3三月1一日開始))頭一第一個月圓的前一天開始,披獸皮的人想必是代表舊年的瑪爾斯,在新年開始時被趕走。而瑪爾斯在起初是植物的名稱,並非戰神。古代羅馬農民就是向瑪爾斯祈求穀物、葡萄、...
推薦序
導 讀
《金枝》蔚成巨木:弗雷澤的學術影響及啟示 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楊玉君
詹姆斯.喬治.弗雷澤爵士(Sir James George Frazer)是一位英國人類學家、民俗學家、古典學家,他所著作的《金枝》是二十世紀初的人類學、民族學名著,其影響力歷久彌新,至今依然是許多相關學科指定閱讀的材料。因為他對人類學的貢獻,弗雷澤在一九一四年獲得「爵士」稱號的榮譽,一九二○年獲選為英國皇家學會院士。
《金枝》的卓絕地位,與弗雷澤爵士的家庭背景及學術養成過程有密切關係。詹姆斯.喬治.弗雷澤於一八五四年一月一日於蘇格蘭最大的城巿格拉斯哥出生,是四名子女中的長子。父親Daniel F. Frazer是Frazer and Green藥商的合夥人;母親Katherine Brown來自海倫斯堡,她的娘家先祖George Bogle(一七四六-一七八一)是蘇格蘭探險家,也是第一位代表西方與西藏建立貿易及外交聯繫的外交官,據說小詹姆斯自幼就著迷於這些遠方探險的故事。藥商的家庭財務優渥,不但父親重視他的教育,也讓他得以追求學術生涯而無後顧之憂。在思想方面,一般咸認煉金術(alchemy這個中譯詞可能遠遠不足以正確反映這個詞的複雜歷史)是近代藥學(chemistry) 的源流之一。《金枝》中將近代科學視為魔法/巫術的進化,這與弗雷澤作為藥劑師子弟的家庭背景應不無關係。弗雷澤一家也是虔誠長老教會家庭,《金枝》內容中不但經常引用《聖經》,整本書的理念中也包含了對基督教文明的省思,可以想見早年的家庭教育濡染深遠。
弗雷澤原本在海倫斯堡的預科學校Larchfield Academy就學,隨後入學格拉斯哥大學,就學期間曾隨著名的物理學家克耳文勛爵(Lord Kelvin)修習物理學,他很早就受到古典學的啟蒙,並且精通拉丁文及希臘文,在這兩處受教育的過程中,又研讀古代哲學與文學,於一八六九年取得碩士學位。並到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持續深造古典學tripos學程,於一八七八年考試獲得學位,次年即任教於劍橋大學。弗雷澤在《金枝》當中所引用的古典文獻展現他的學識淵博,這主要來自他深厚的希臘羅馬古典學的造詣。雖然弗雷澤顯然具有學者傾向,他卻也曾因為父親希望他能有個「真正」的職業,而至倫敦的中殿律師學院(Middle Temple)修習法律學,並獲得了律師資格。但他從未真正執業,而是在獲得律師資格後又回到劍橋大學,從事他深愛的研究工作。
弗雷澤當時的研究專案是翻譯、註釋西元二世紀時的希臘地理學家、旅遊作家保薩尼亞斯(Paesanias)的著作《希臘志》。這本書卷帙浩繁,共計十冊(弗雷澤的註釋本分為六集),廣收希臘各城巿的風土、名勝、傳說等訊息,本書中記錄的神話和傳說日後對弗雷澤撰寫《金枝》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資料。從他投入此書的過程中,我們也可理解他如何以同樣的勤勉與毅力從事大量民族志的閱讀及整理。在同一時期,弗雷澤也因為受到泰勒的《原始文化》(一八七一年)之比較研究法的影響,而開始關注非西方民族的習俗及信仰。不過,真正讓他踏進人類學領域的關鍵,是他另一位劍橋大學的同仁、教授阿拉伯語的威廉.羅伯遜.史密斯(William Robertson Smith),史密斯是舊約學者、神學教授,一八八三年起任教於劍橋大學,他不但鼓勵弗雷澤研究宗教文化及儀式,更在自己擔任大英百科全書第九版編輯時(一八八八年),邀請弗雷澤撰寫兩篇詞條專文〈禁忌〉與〈圖騰主義〉。很快的,弗雷澤就開始發表人類學主題的論文,並且深信人類學的知識也將有助於他對古典文獻的理解。終其一生,他都以結合神話及儀式研究為職志。
弗雷澤是個非常勤奮的學者,他長期、規律的在書房裡工作,閱讀大量的資料,勤作筆記,擅長分類。《金枝》中廣博的巫術案例,有一大部分來自當時尚未完全接受現代文明洗禮的印度、大洋洲、印尼群島、南美洲、非洲等地的記錄。這些記錄除了來自既有文獻外,也包含了弗雷澤主動與海外的外交官、醫生、傳教士、殖民地官員等人通信的結果。當時他廣發問卷給這些與各地居民、部族有接觸的人士,以蒐集來自不同民族、文化的風俗與信仰,再參照研讀文獻、報告以及探險家的遊記等材料,並據此發表他的研究成果。而且他持續毫不懈怠的閱讀及筆記,使得《金枝》在發表第三版時,新增了更豐富的資料,篇幅從初版的兩冊遽增為十三巨冊!長年高強度的閱讀研究工作,讓弗雷澤的視力逐漸衰退,又因意外受傷,到一九三一年時完全失明。失明後他仍然在祕書及助理的協助之下,堅持研究工作。弗雷澤於一九四一年五月七日在劍橋去世,享年八十七歲。
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歐洲,正是社會進化論萌生、發展的時期。弗雷澤多少也受到進化論的影響,但他將生物基礎的進化理論應用到人類心靈上,於是在他的理解詮釋下,《金枝》中呈現的人類文明發展便是「巫術→宗教→科學」的過程。亦即原始人所認知的自然規律有一因果關係,此因果關係依循著「相似律」、「接觸律」兩種原則而建立,巫術就是人類依此因果關係而發想出操控自然規律之實踐。而介於巫術和科學之間的宗教,是在人們意識到巫術操控自然的現象效果有限時,轉而相信自然與人類生命的進程間乃受到一超自然的力量所支配,並且這超自然的力量可以被迎合與撫慰。宗教進化的下一階段是科學,科學同樣認定萬物有其內在規律,甚至對自然現象的理解也是建立在因果論上。但相較之下,弗雷澤認為巫術認定的因果關係是一種曲解的規律,因此他將巫術視為一種「偽科學」。
弗雷澤雖然被視為現代人類學之先驅,但他並未親自從事田野調查。除了西班牙及希臘外,他從未造訪過其他國家。偏偏比他晚一輩的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一八八四-一九四二)所提倡的參與觀察的田野調查方法,被主流人類學視為圭臬。弗雷澤所代表的老派學者在書齋裡的研究,因而被後輩譏為「扶手椅上的人類學家」。而他所引用在《金枝》的異文化風俗信仰的案例,也被批評是去脈絡化的理解與引用。更有人直指弗雷澤對異文化的認知,以及他對文明進化的理論,都帶著白人至上的殖民主義觀點的階級偏見。現代人類學家的學科基礎極為重視長期實地參與、觀察的研究調查,並且對自我研究的態度提出反省分析,在這些條件的審視下,弗雷澤及他的《金枝》毋寧是令人羞愧的存在,許多當代的人類學家也慣性的攻擊弗雷澤是帝國主義、父權主義、菁英主義等等。
儘管如此,弗雷澤在二十世紀仍是數一數二影響力深遠的學者,那又是為什麼呢?
首先,弗雷澤的散文書寫充滿詩歌般的魅力,《金枝》提供了人們浪漫的想像基礎,可能從來沒有哪一部人類學著作曾擁有這麼多非學院派的讀者。《金枝》獲得來自各方的肯定,除了內中淵博的知識外,經常也包含對弗雷澤優美文采的稱譽。他的寫作風格形成與讀者之間的親密氛圍,好似一位牧師既溫和又半帶權威的侃侃而談。相對於社會人類學家對他保持敬慎疏遠的距離,弗雷澤在文學家和藝術家之間的影響力甚至超乎他的學術成就,舉凡James Joyce、William Butler Yeats、D. H. Lawrence、Ezra Pound等詩人都曾受到他的啟發。T. S. Eliot的〈荒原〉把《金枝》列為主要參考材料,詩句中多處用典均指涉到書中的植物衰敗與新生,艾略特也直言《金枝》對他的世代有深刻的影響。佛洛伊德、榮格發展他們的精神分析理論時,以及神話學大師Joseph Campbell發展他的神話理論時,都受益於《金枝》中對文學及象徵的詮釋。
另一個與《金枝》攸關至鉅的,則是宗教研究這個領域。弗雷澤屬於最早一代將宗教視為社會活動,並且可以運用科學方法加以比較研究的學者。在過去,宗教是神學家對信仰本身神性的研究,而弗雷澤將它變成了世俗學問的研究對象。雖然弗雷澤用來討論的文獻及案例多半為非西方世界的異教信仰,但書中所呈現出來的宗教概念及習俗可能讓他的讀者──特別是他同屬基督教文明的同胞們──清楚的認知到不同的文化之間有著宗教及神話的類同點。例如,弗雷澤分析了古典時期的各種神祗的信仰,像Adonis、Osiris、Dionysus,不可避免的討論了他們都有死亡及復活的神話。即使弗雷澤並未將《聖經》故事也放到同一平台上審視比較,明眼人應不難看出拿撒勒的耶穌復活與上述信仰神話間的共同點,甚至繼續上推,還可以自問,在這些案例的對比之下,基督教信仰是否有其獨特性,是否與「原始人」的信仰有足夠差別?即使是要面對這些問題,都已經是前所未有的巨大衝擊。對抱持傳統敬畏宗教觀念的人而言,《金枝》毋寧是離經叛道的。而《金枝》的重大價值之一,恰恰在於這一點:它鼓勵讀者藉著多元文化的宗教現象的對比,反過來自我省察,從而更深化了對己身所屬文化的了解。
身在廿一世紀,深受漢文化影響,對原住民風俗一知半解的臺灣人,閱讀《金枝》也能夠加深我們對本身文化的了解嗎?
答案是肯定的。
《金枝》的第一章陳述了一個傳說。據說在古羅馬時代,內米湖旁的叢林中有一間黛安娜的神廟,廟旁一棵神樹,守護神樹的祭司被視為「森林之王」。如果有逃亡的奴隸折下了神樹的樹枝,就取得與祭司決鬥的資格。一旦殺死祭司,就可以接任祭司的職位成為森林之王。這枝決定命運的神樹樹枝就被稱為金枝。弗雷澤引用這則傳說為本書揭開序幕,為了解答為何要折下金枝才能挑戰祭司,以及為何得殺掉前任祭司才能成為森林之王這些問題,弗雷澤旁徵博引古往今來世界各地的原始信仰資料,以比較研究法系統化的歸納,使得許多民俗的涵意逐漸清晰。
例如在第九章〈樹神崇拜〉中,弗雷澤援引雅可布.格林(即格林兄弟之一)的說法,指出日耳曼語的「神殿」語源與自然森林相關,推測古日耳曼人的聖地可能就是自然森林。這讓我們連想到《詩經》〈桑中〉的詩句「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聞一多在解此詩句時指出,桑中(據語意是茂密的桑樹林)及〈溱洧〉等詩所描述的故事,即是昭示古代祭祀先妣、高禖的風俗。以及《呂氏春秋.順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雨乃大至」,商湯祈雨的地方也是在桑林。 可知在信仰發展的初期,以密林作為聖地具有普遍性,這都是相信樹木有靈的樹木崇拜的案例。
許多樹木崇拜的外顯形式已經不易看出樹形,而與內米的黛安娜聖殿一樣,主要以樹枝或是草本植物的植株作為代表。例如在《金枝》中多次提及的仲夏節、五朔節的習俗,與中國的端午習俗有許多平行現象,其中很明顯的植物運用就是歐洲的聖約翰草和中國的艾草,二者是同屬不同種的植物,其生物、民俗屬性均十分的相似,也都被當成具有驅逐邪祟的植物來懸掛門上或佩戴在身上。
又如說明交感巫術中的模擬巫術,《金枝》所舉的是「模擬生產」的例子。據說弗雷澤同時代的保加利亞和波士尼亞有此習俗,「一個女人把她要收養的孩子放在她的衣服裡,又推又拉地從衣服裡鑽出來,從此以後,這孩子就被認定是她的真正兒子。」這是以模擬分娩的方式將非親生的孩子透過模擬巫術「生出來」成為自己的親生子。有此一說來對照,我們忽然便理解了傳說中唐玄宗和楊貴妃「收養」安祿山為義子時,為何會在宮中「貴妃以繡繃子繃祿山,令內人以彩輿舁之」。 貌似荒唐胡鬧的洗兒會,仍有其民俗思維的邏輯。甚至,當代臺灣民間信仰中拜認女神為契子、契女的習俗中,有類似鑽轎腳的儀式,讓拜女神為契母的孩子自女神的神桌下匐匍而出,很可能也是在模擬自女神的裙下分娩而出的「收養」巫術。
同屬生養習俗的埋胞衣(胎盤)也是一樣,《金枝》中羅列各地民俗來說明臍帶和胞衣普遍被認為在離開人體之後仍保留了交感的聯繫,因此一個人的禍福安危都與它的胞衣是否安全儲藏有關。臺灣民間也有埋胎衣罐的習俗,認為胎衣與嬰孩的元神相關,故此要深藏於居宅的地下,以免遭到破壞。 也因此,客家人以「胞衣跡」一詞用來指稱人出生的地方,也就是故鄉。
關於國王具有巫術或能使土地肥沃的超能力這個概念,弗雷澤認為是從印度到愛爾蘭等所有亞利安人的祖先們共有的信仰。荷馬時代的希臘人認為國王的統治能使「大麥、小麥長滿沃野,水果碩大壓彎枝條,六畜興旺,魚滿海洋」。在類同的思維上,中國人對帝王統治則再加上了「仁君」的倫理條件,亦即在聖王仁君的統治下,才會出現嘉禾一莖多穗、地出甘泉等太平瑞應。
在誓約的民俗方面,我們得知婆羅門教的入教儀式、結婚儀式都要踩著一塊石頭說出誓詞;馬達加斯加的人也會將石頭埋在房基之下,因為他們相信石頭能使誓約更加有力、堅固不毀。這與我們所知的原住民「埋石立約」也是基於一樣的原理。
以上略舉數例來證知弗雷澤如何在《金枝》中以豐富的民俗信仰的系統化呈現,引領讀者了解自己熟悉的民俗現象的內在思維。長久以來,太多人類學家提起《金枝》時都語帶貶抑,急著指出它的方法論及理論的缺失。殊不知所謂的缺失,實在瑕不掩瑜。人類文化中確實有相當的思維共通點,不應一概摒棄不論。所幸這種矯枉過正的趨勢已漸有人試圖導正,陸續有學者呼籲重新評價《金枝》。 《金枝》的初版距今已有一百三十餘年,至今仍然是值得研究者參考的寶庫,它也持續的在啟迪著初初接觸民俗信仰的讀者,這正是本書恆久不衰的價值。
導 讀
《金枝》蔚成巨木:弗雷澤的學術影響及啟示 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楊玉君
詹姆斯.喬治.弗雷澤爵士(Sir James George Frazer)是一位英國人類學家、民俗學家、古典學家,他所著作的《金枝》是二十世紀初的人類學、民族學名著,其影響力歷久彌新,至今依然是許多相關學科指定閱讀的材料。因為他對人類學的貢獻,弗雷澤在一九一四年獲得「爵士」稱號的榮譽,一九二○年獲選為英國皇家學會院士。
《金枝》的卓絕地位,與弗雷澤爵士的家庭背景及學術養成過程有密切關係。詹姆斯.喬治.弗雷澤於一八五四年一月一日於蘇格蘭最大的...
作者序
前言
本書的主要目的在於闡釋有關繼承阿里奇亞 義大利最古老的城鎮之一,位於羅馬東南16英里阿爾巴諾群山中,盛產酒和蔬菜。其附近叢林幽美,以崇奉女神狄安娜馳名遐邇。[本書注釋星號均為原注,圈碼均為譯注。]狄安娜黛安娜 狄安娜(Diana),羅馬神話中的女神,相當於希臘神話中月亮和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Artermis),又是繁殖女神。她是拉丁人的女神,古羅馬時期在羅馬城內七丘之一的阿蘭丁山上就建有她的神殿,受庶民和奴隸們崇奉,特別受婦女崇奉。最初原是森林與自然之神,以「林中的狄安娜」(Diana Nemorensis)著稱。祭司職位的奇特規定。三十30多年前,我剛開始研究這個問題時,原以為可以簡要地予以解釋,但不久我就感到,有必要研討一些更為一般且其中有些是迄今未曾提出的問題,這樣才能把這個問題解釋得比較合情合理,易於瞭解了解。本書的前此前的各版,對於這個問題以及與此有關的一些問題,增寫的篇幅越來越愈來愈多,涉及的範圍越來越愈來愈廣,最後全書由原來的兩卷增加到十二卷。這期間,許多讀者表示希望本書同時另出節本。現在這部節本就是為了滿足這種希望,以饗更廣大的讀者。著者在壓縮原著篇幅時,儘量保留了書中重要原理和足以說明每一問題的充分例證。儘管做了節縮,但絕大部分文字仍依照舊著,,未加改動。為多保留原文起見,書中注釋及所依據的準確引證材料,只好全部割愛。讀者如欲查明某一論述的依據,請參考本書十二卷版,那裡該處附錄了有關的詳細文獻和詳盡的參考書目。
這部節縮本,既未增寫新問題,也未改變原書十二卷所闡述的觀點。在原書出版之後我所得的新的資料,大體上都印證了我以前所作的結論,vi或作為過去所提原理的新例證。譬如,在有關為王者到一定時期、或到其精力開始衰退之時必須被處死這個極其重要問題上,凡能說明這一習俗確實廣泛流行的證據,這部節本都大量採用。俄羅斯南部喀薩爾人 或譯可薩。我國《經行記》中稱為可薩突厥,《新唐書》中稱為突厥可薩,系韃靼人的一支。在中世紀建立的強大王國,就是這類有限君主制政體的突出例證。在喀薩爾人的王國裡,國王在任期屆滿時,或遇旱潦饑饉、戰爭失敗等標誌象徵其精力已經衰退之情況時,都得被處死。古代阿拉伯人遊記裡記載過喀薩爾國王們被有組織、有步驟地處死的情況,這些證據我都彙集在一起,另編成文。 見弗雷澤(J. G. Frazer):《可薩人弑君記》(The Killing of the Khasar Kings),載《民俗》(Folk拟lore)xxviii(1917),第382407頁。此外,非洲也新發現了好些不少與此相類似的弑君習俗的事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要算布尼奧羅 在今烏干達境內。地方曾經遵行的習俗:每年從部落中選出一人假扮為王,把他當作已故國王的化身,讓他與已故國王的遺孀在其陵廟中同居,為王七日,然後絞殺。 見羅斯科(Rev. J. Roscoe):《中非的靈魂》(The soul of central Africa),倫敦,1922,第200頁,比較弗雷澤(J. G. Frazer):《麥基中非民族學考察》(The Mackie Ethnological Expedition to Central Africa),載《人》(Man),xx(1920),第181頁。這習俗同與古代巴比倫人的撒卡亞節習俗非常近似。古巴比倫人在撒卡亞節期間有一位假扮為王的人,身穿王袍,享受真王的姬妾,五日後即被剝去衣衫,鞭笞至死。最近發現亞述人的一些碑銘季默恩(H. Zimmern):《巴比倫人的新年節目》(Zunbabylonischen Neujahrsfest)(萊比錫,1918)。比較薩伊恩發表在《皇家亞洲學會學報》(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文章(1921年7月,第440442頁)。 提供了有關上述節日的新線索,進一步證實了我以前的闡述,即:撒卡亞節乃是慶祝新年的節日,猶太人的普利姆節 見《金枝》(The Golden Bough),第六部分,「替罪羊」(The sapegoat),第354頁以下及412頁以下各頁。即淵源於此。最近還發現有和阿裡里奇亞祭司之王相似的習俗,如非洲的祭司或國王常在7七年或2兩年任期屆滿時被處死,並且在任職期間也可能被強有力的對手刺殺身亡,而由刺殺者繼任其祭司職位或王位。 見阿毛利.塔爾博特(P. Amaury Talbot)文章,載《非洲社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frican Society),1916年7月號,第309頁以下;《民間文學》(Folk拟lore),xxvi,(1916),第79頁以下:帕麥爾(H. R. Palmer)文章,載《非洲社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frican Society),1912年7月號,第404頁,第407頁以下。
上述有關這種習俗的事例及其他事例,都表明顯示出我們不能再把阿裡里奇亞狄安娜黛安娜祭司職位的繼承問題看作一種奇特的規定,它其實只是這種普遍存在的習俗的一個很好例證。而到目前為止,發現此類習俗最多的地方則是非洲。這些事實是否可說明古代非洲對義大利甚有影響,甚至說明南歐非洲人口之存在的影響,對此,我不擬在這裡不妄加臆測。vii歷史記載以前的歐、非兩大洲的相互關係,迄今仍不太清楚,尚待調查研究。
我對這種習俗所作的闡述是否正確,只有留待未來裁定。如有更好的解釋,我準備隨時放棄現在這些看法。在將這部節本奉獻于於讀者鑒定指正之際,我希望借此機會指明一個早就想要指明,且至今似乎仍然相當普遍的誤會,以免它繼續蔓延,這那就是:假如我在這部節本中以較多篇幅談到樹木崇拜問題,這並非是我有意誇大它在宗教史上的重要性,更不是我想要從它演繹出一套完整的神話體系來,只是因為在試圖解釋擁有「林中之王」稱號的祭司(他又必須在摘下聖林中一棵樹上的一枝——金枝——之後才能接任)的意義時,對此現象不容忽視而已。其實,我也只是把樹木崇拜這一現象作為宗教發展過程中極其重要的現象之一來看待,認為它應該完全從屬於其他因素,特別是害怕死者這一因素。我以為,總整體來說而言,後者可能是形成原始宗教的最有力的因素。我希望通透過這樣的說明,今後不再受到非難,說我想建立某種神話體系云云。其實,我不僅認為那種神話體系是虛假的,而且還認為那是愚蠢、荒謬的。我深知,誤解有如九頭之蛇, 希臘神話:九頭蛇,名叫海德拉(Hydra),它的頭砍掉一個,又會長出一個。難以期望一次說明便能徹底消除,或不再產生。我只能信賴讀者的公正和才智,他們會通透過我本人所作的聲明,加以參照比較,以糾正對我的觀點的嚴重誤解。
詹姆斯.喬治.弗雷澤
一九二二年六月,倫敦
前言
本書的主要目的在於闡釋有關繼承阿里奇亞 義大利最古老的城鎮之一,位於羅馬東南16英里阿爾巴諾群山中,盛產酒和蔬菜。其附近叢林幽美,以崇奉女神狄安娜馳名遐邇。[本書注釋星號均為原注,圈碼均為譯注。]狄安娜黛安娜 狄安娜(Diana),羅馬神話中的女神,相當於希臘神話中月亮和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Artermis),又是繁殖女神。她是拉丁人的女神,古羅馬時期在羅馬城內七丘之一的阿蘭丁山上就建有她的神殿,受庶民和奴隸們崇奉,特別受婦女崇奉。最初原是森林與自然之神,以「林中的狄安娜」(Diana Nemorensis)著稱。祭司職位的...
目錄
下冊
第二十九章 阿多尼斯的神話
第三十章 阿多尼斯在敘利亞
第三十一章 阿多尼斯在賽普勒斯
第三十二章 阿多尼斯的祭祀儀式
第三十三章 “阿多尼斯園圃”
第三十四章 阿蒂斯的神話和祭祀儀式
第三十五章 阿蒂斯也是植物神
第三十六章 阿蒂斯的人身顯現
第三十七章 西方的東方宗教
第三十八章 奧錫利斯的神話
第三十九章 奧錫利斯的祭祀儀式
第四十章 奧錫利斯的屬性
第四十一章 伊希恩
第四十二章 奧錫利斯和太陽
第四十三章 狄俄尼索斯
第四十四章 德墨忒耳與珀耳塞福涅
第四十五章 北歐的五穀媽媽和五穀閨女
第四十六章 許多國家都有五穀媽媽
第四十七章 裡提爾西斯
第四十八章 穀精變化為動物
第四十九章 古代植物之神的動物形象
第五十章 神體聖餐
第五十一章 吃神肉是一種順勢巫術
第五十二章 殺死神性動物
第五十三章 獵人撫慰野獸
第五十四章 以動物為聖餐的類型
第五十五章 轉嫁災禍
第五十六章 公眾驅邪
第五十七章 公眾的替罪者
第五十八章 古羅馬、希臘的替罪人
第五十九章 墨西哥的殺神風俗
第六十章 天地之間
第六十一章 巴爾德爾的神話
第六十二章 歐洲的篝火節
第六十三章 篝火節的涵義
第六十四章 在篝火中焚燒活人
第六十五章 巴爾德爾與槲寄生
第六十六章 民間故事中靈魂寄存於體外的觀念
第六十七章 民間習俗中靈魂寄存於體外的觀念
第六十八章 金枝
第六十九章 告別內米
詹姆斯‧喬治·‧雷澤 年表
索引
下冊
第二十九章 阿多尼斯的神話
第三十章 阿多尼斯在敘利亞
第三十一章 阿多尼斯在賽普勒斯
第三十二章 阿多尼斯的祭祀儀式
第三十三章 “阿多尼斯園圃”
第三十四章 阿蒂斯的神話和祭祀儀式
第三十五章 阿蒂斯也是植物神
第三十六章 阿蒂斯的人身顯現
第三十七章 西方的東方宗教
第三十八章 奧錫利斯的神話
第三十九章 奧錫利斯的祭祀儀式
第四十章 奧錫利斯的屬性
第四十一章 伊希恩
第四十二章 奧錫利斯和太陽
第四十三章 狄俄尼索斯
第四十四章 德墨忒耳與珀耳塞福涅
第四十五章 北歐的五穀媽媽和五穀閨女
第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