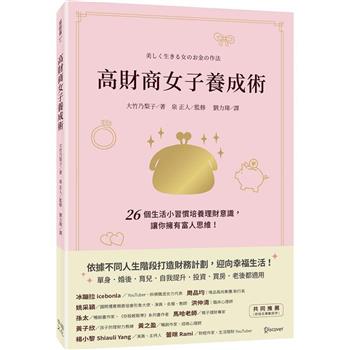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語法動起來 2的圖書 |
 |
語法動起來 2 作者:邱新富、戴金惠、姚瑜雯、于麗萍 出版社: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4-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20 |
二手中文書 |
$ 237 |
教師教育資源 |
電子書 |
$ 240 |
語言學概論 |
$ 270 |
語言 |
$ 279 |
中文書 |
$ 279 |
中文 |
$ 285 |
華語教學 |
$ 285 |
中文寫作 |
$ 300 |
Books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本書特色
《語法動起來2》是為從事華語教學的老師,和有志參與這項工作的讀者,所編寫的關於教案設計與方法的專書。
人類母語能力的發展從一開始就在有「語境」的情況下開始,為此,華語教師在面對初、中級的句本位教學也好,高、優級的段落篇章教學也好,須盡可能、大幅度地擺脫機械式、枯燥乏味的語法教學,並深刻理解到「語境」在各個教學環節中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教學過程中,教學任務、活動可以五花八門,但總體來說,不外乎理解詮釋、人際互動、表達演繹三大類型。在《語法動起來2》中,四位資深華語教師分別闡述了如何在上述三種教學型態中,適切納入對語境的思考,以提供初、中、高級學習者在符合人性、本能、認知的華語學習過程中,培養語言使用的能力。
藉由提供教學步驟與範例的手法,《語法動起來2》旨在強調「語言結構」與「使用情境」的不可切割性,希望華語教師無論在編寫、選擇教材內容、講授語言知識、操練語言結構的過程中,都按此原則活絡抽象的語法概念,讓學習者能走出課堂,與外界人士交流。
作者簡介
邱新富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現代語言文學系副教授。政大英語系畢業,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應用語言學系碩士暨博士。曾任教於美國明德中文暑校語言部及碩士班、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洲語言文化學系、美國波莫納學院亞洲語言文學系、文藻外語大學、聯合大學、台中教育大學等單位。著有《Language Socialization in Chinese Diasporas: Indexicality of Confucian Ideologies in Family Talk》、《前進中文:中級課程》等。
戴金惠
旅居加州的台北人,輔仁大學英國文學系畢,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學語言學碩士暨博士。曾於德國海德堡大學交換研究,加州伯克萊大學進修研究,曾任教於加州聖塔芭芭拉大學、賓州大學、明德中文暑校語言部及中文碩士研究生項目、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研所客座、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華語教學組兼任副教授等。現任蒙特雷國際研究學院口筆譯及語言教育所有中文項目教授。著有《生活、認知與中文教學》、《創新中文教育:生態語言教育觀》等。
姚瑜雯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中文講師。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曾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華語中心、淡江大學華語中心及臺灣師大國語中心等,2000年開始每年暑假任教於明德大學暑期中文學校至今。
于麗萍
旅居美國的北京人。1988年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後,在中國人民大學外語系任教,1995年開始在美國大學教授漢語的工作,先後執教於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現任華盛頓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教學教授,著有《文學中的現實》。
前言
邱新富
針對第二語言習得的研究,在過去二十年間,衍生了一個新興理論──社會文化理論(sociocultural theory; Lantolf, 1994),而這個學派的出現,有很大部分呼應了Lave和Wenger(1991)所主張「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理論根基。Lave和Wenger(1991)認為學習、發展必須建基於學習者親身參與一系列的社會活動。在參與的過程中,當學習者為了適應當下情況、活動內容的改變,而不斷地做調適時,學習者也正一步一步地將參與過程中的種種,內化成自身對世界的認知以及知識。在學習者建構的過程中,相關的人(如:教師、同學)、事(如:各式學習任務)、物(如:教材、教具)皆對該學習者認知/知識的建構都產生了Vygotsky所謂的「協調(mediation; Vygotsky, 1978)」功能。Lave和Wenger(1991)將前蘇聯著名心理學家 Vygotsky(1978)知識建構(social constructivm)的概念進一步延伸,將學習過程中的教學者與學習者間一對一的單一活動模式,擴大範圍至教學者、學習者、學習同儕間的多元、多方互動模式。此外,學習的過程是一連串的活動參與,學習者對活動的主動參與是建構知識的必經之途。學習者在初學時期僅能生疏地參與「邊緣性參與(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Lave & Wenger, 1991)」,但隨著經驗的累積,以及團體成員的指導和輔助,學習者進而能獨當一面地從事「核心任務(full participation; Lave & Wenger, 1991)」。簡言之,認知/知識是在一連串社會參與(participate)、實踐(practice)中所激盪出來的火花、積累下來的結果。
Lave和Wenger的「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很快地對第二語習得研究產生了蝴蝶效應。在九十年代中期,應用語言學界興起了一波針對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的學術改革風潮(Block, 2007)。相較於當時主流研究導向,在語言實驗室測試語言習得的「結果」,以Firth和Wagner(1997)為首的應用語言學家則轉而主張將社會學、社會語言學等領域的見解作為理論根基,採用「主位觀點(emic,當地/事人觀點)」來重新詮釋語言發展,進行習得研究。無論在第一、第二,還是外語語言學習過程中,學習者的發展都不被認為是獨立於語境、情境,甚至是社會文化結構的單一過程;語言習得也不再只聚焦於學習者不足的語言能力和母語人士完美能力之間的差異;相反地,語言習得是一種學習者內在與外在一切有關人、事、物多元交相影響的「過程」,而這個動態的過程就是我們熟知的溝通、互動。
伴隨著人類天生具有的互動本能(interactional instinct; Lee et al., 2009),語言能力就在嬰兒出生的那一天起,開始在與這個世界互動的過程中展開。在親身參與成人世界的過程中,小嬰兒語言能力也同時穩定發展,這也就是人類學家Ochs和Schieffelin(1984)所主張的「從社會參與到語法成形(socialization to language)」。然而,人類的發展並不僅止於語法的成形。當個體有了基本的語言能力(linguistic skills)後,其與外在環境的溝通交流仍持續著,進行著所謂 「從語法成形到社會進化(socialization through language)」:在與外界永不停止地互動、反思、修正的過程中,人類個體對於這個世界的認知與意識形態也同時逐步建構,而文學素養能力(literacy skills)的發展就是其中之一。從社會環境到語言能力發展,從語言能力到人文素養,人類所屬的社會性(sociality)就在個體的主導力(agency)與外界各種型態的符號資源(semiotic resources)交相影響中,逐步揭示。
人類的行為模式無法跳脫外在環境而產生或理解,對於人類語言行為、語言發展的研究,也同理需要所謂的情境/語境(context)來佐證、詮釋。以上述論點為理論基礎;語境為導向的華語教學(focus on form; Long, 1991),貫穿了本書九個篇章的主軸。
如同白建華教授所示(本書第一章),合格的華語教師在面對初、中級的句本位教學也好,高、優級的段落篇章教學也好,須盡可能、大幅度地擺脫機械式、枯燥乏味的語法教學(範例請見本書第九章),並深刻理解到胡壯麟(1994)所提到的語篇語境(linguistic context)、情景語境(situational context),甚至是文化語境(cultural context)在各個教學環節中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教學過程中,教學任務、活動可以五花八門,但總體來說,不外乎是理解詮釋型(interpretive)、人際互動型(interpersonal)、表達演繹型(presentational)三大類。在本書接下來的八篇文章中,四位資深華語教師分別闡述了如何在上述三種教學型態中,納入對語境的思考,以提供學習者符合人性、貼近本能的華語教學。納入語境的教學,在初(elementary)、中(intermediate)、高(advanced)、優(superior)各個級別的課堂中,都有顯著的功效。
一、語境與理解詮釋型教學(Context in Interpretive Teaching)
理解詮釋型的教學經常是講述課(lecture)中主要任務:老師帶領學生與文本上的文字內容、文章作者做單向的溝通。認讀文字、理解文意是這個階段的主要目的。在華語教學的課堂中,老師與學生分別來自於不同的國家,也正因為如此,彼此必然存在著文化、認知上的差異。當學習者(特別是成人學習者)腦子裡已建構了其母語文化中的認知系統,這個系統在他們學習華語的過程中,或多或少會造成負面的影響(即負遷移,negative transfer)。在建構學生語言元知識(metalinguistic knowledge)時,教師必須提醒自己,學生的認知與己身有一定程度的差異。認知上的重大歧異,就是學習上的主要困難點,也就是教學端要費盡心思設計、檢討的地方。本書第七、八章中,姚瑜雯老師就以師生間的認知差異為基礎,提醒老師們在為學生剖析華語的語序、動詞/形容詞分類的過程中,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並應該如何進一步為學生解惑。本文雖以北美大學生為例,但在面對東北亞、東南亞,或其他來自各個語系的學生時,文章中所提出的觀點都需要納入教案的設計參考中。
在中高級,以及高、優級的教學中,建構學生篇章認讀方面的能力,是主要的教學目標之一,而這個階段的教學材料往往會以篇章段落的形式呈現在學生的面前。趨近真實,甚至全然真實的語料,也就因而被收入成為有用的教學材料。當教材從對話體提升到敘述、議論題材時,文章探討的議題也會從基本的食衣住行延伸到人文風俗、家國時事。本書第五章中,戴金惠教授以實際的教案為例,教導讀者如何有效地利用真實語料中具有意義、能理解的「篇章語境」和「文化語境」,來為高級班的學生提供建構文學素養能力的素材。相同的教學法並不僅限於高級班的學生,在本書第六章中,戴教授沿用相同的邏輯,以一篇趨近真實的課文為例,教導讀者如何將課文中延伸而來、符合真實情況的「文化語境」,帶入中級語法教學中。
二、語境與人際互動型教學(Context in Interpersonal Teaching)
語言產生是藉由人際互動開展,人際互動的過程也是人類社會性的展現。語言教學的終極目標,理應是幫助學習者成為能輸出目標語言、文字的使用者,而不是語言能力考試的得分者,或是善於分析語言的語言學家。為此,教學的任務必定不能缺少讓學生實際演練、使用目標語的機會。這個教學環節對於語言點的鞏固,以及提升學習者語言表達能力都具有相當正面的效果。本書第二、三、四章,邱新富教授結合了社會學中對話分析的理論框架為本,提供讀者一套符合人類行為模式的語法操練互動,讓初、中級的華語學習者能在教師有層次、有邏輯的帶領之下,融合語篇語境和情景語境,自信、得體地開口與人做即時(spontaneous)的溝通互動,並在反覆使用目標語同時,逐步將抽象的元語言知識轉化成能自在、自主使用的語用能力。
三、語境與表達演繹型教學(Context in Presentational Teaching)
當抽象的元語言知識內化(internalize)成能靈活運用的技能後,下個階段的教學目標,就是訓練學習者將接收、理解、內化了的語言能力/知識,組織成段落、篇章的型態;能向假想、虛擬文章讀者,或演講聽眾做溝通,表達個人對事物的見解與看法。這也就是本書最後章節的重點。在本書第九章中,于麗萍老師分享了如何在初、中級以句子為本位的語法教學中,合宜地融入語篇語境,讓學生理解到單一語法的使用是如何離不開對上下文的理解。另外,當學習者的語言輸出應提升到段落、篇章的層次時,關聯詞與標誌詞的運用,是使篇章連貫、通順的關鍵。文中,于老師將北美學習者篇章謬誤中的真實案例一一列舉,再剖析篇章謬誤與篇章語境之間的關聯性後,提供了讀者篇章教學的實際教案,作為增進學習者篇章能力建構的方法。
人類母語能力的發展從一開始就在有語境的情況下開始,為此,華語教師無論在編寫、選擇教材內容、講授語言知識、操練語言結構的過程中,皆必須思考如何讓語法的教與學能在各種型態且「有意義」、「以學生認知為本位」的語境「協調」下進行,筆者以為,此層的思考是幫助學習者有效習得語言知識、培養語用能力的必經之路。這個概念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困難,而本書的目的就在幫助讀者解決、突破這方面的教學困難處。
目錄
第一章 專家的話:語境研究與高年級漢語教學(白建華)/001
第二章 對話分析與華語教學(邱新富)/013
第三章 對話分析與華語教學:操練課堂應用(上)(邱新富)/029
第四章 對話分析與華語教學:操練課堂應用(下)(邱新富)/047
第五章 跨學科篇章閱讀教學與成語連用的篇章分析:以高級《河西走廊》真實語料為例(戴金惠)/071
第六章 對話語篇教學:以《Intermediate Spoken Chinese》課堂實踐為例(戴金惠)/085
第七章 從語序看語法(姚瑜雯)/101
第八章 從動詞看語法(姚瑜雯)/119
第九章 篇章教學始於初級(于麗萍)/ 133
參考文獻/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