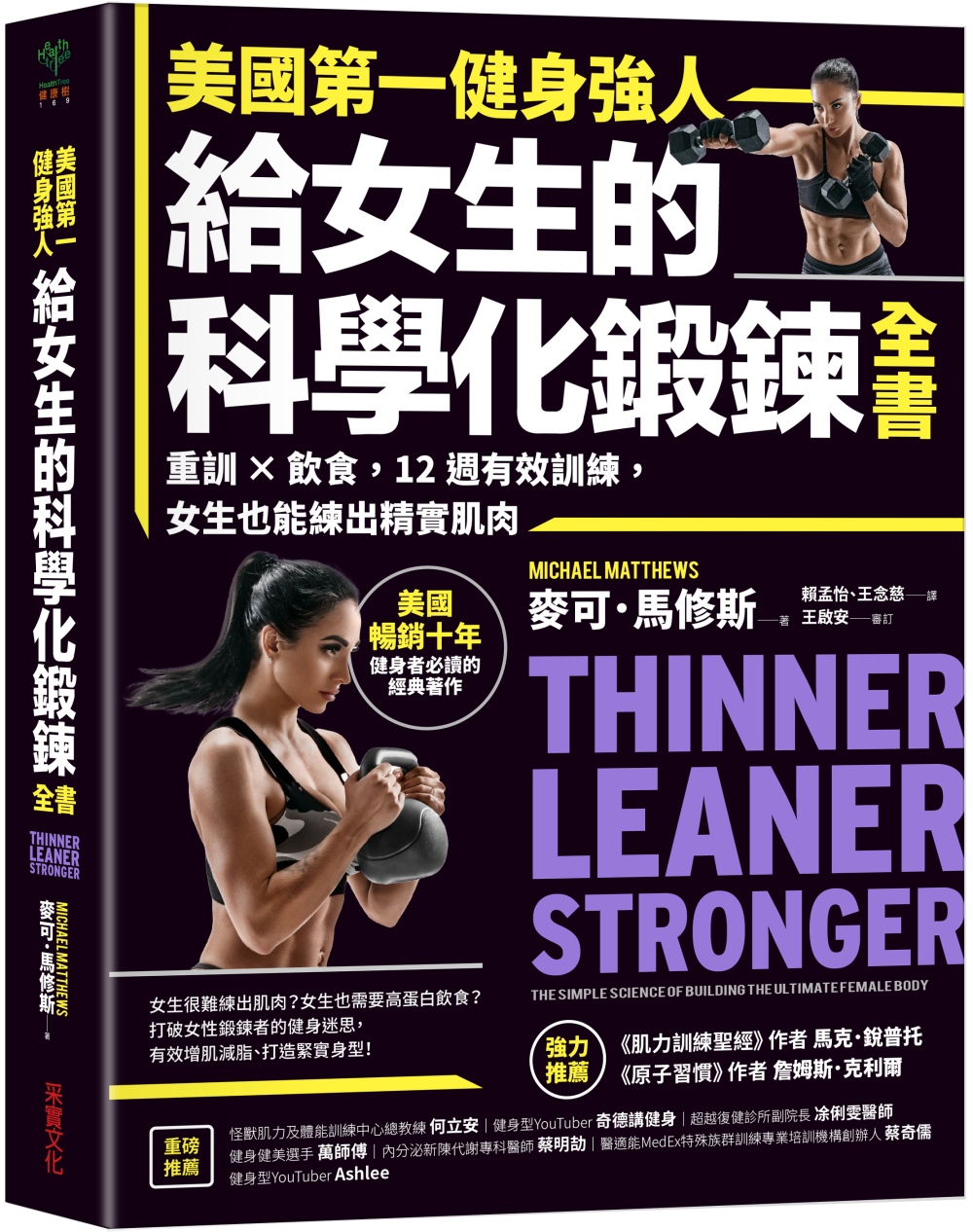圖書名稱:雪花蓮的慶典
《雪花蓮的慶典》是赫拉巴爾在1970年代,以克爾斯當地的風土人情為背景,自己化身為書中的作家,用日記形式寫成的短篇小說集,共21篇。如同《過於喧囂的孤獨》、《河畔小城三部曲》,《雪花蓮的慶典》也是赫拉巴爾鼎盛時期的作品。
赫拉巴爾在一九六六年回到他的第二故鄉寧布卡,在克爾斯森林附近定居,他認為在與鄰居互動的過程當中,讓他彷彿回到故鄉,重溫童年時期的種種,於是,林區的眾生相成為他創作靈感的來源。
小器的餐廳老闆、美麗優雅的夫人、萬年影痴、活在昔日榮光的自負畫家、喜好囤積舊貨的怪人、一心想擺脫專橫妻子的膽小丈夫、頭戴白色禮帽的神祕客、為一頭被射殺野豬的歸屬而爭執不下的兩個狩獵協會……典型赫拉巴爾式的誇張人物形象,加上鮮明的鄉村場景,搭配口語化的對白和方言俚語,赫拉巴爾寫出一篇篇令人難以置信或捧腹大笑的幽默人性故事,來反應他對生命的熱愛。
捷克導演日依.門澤爾(Jiří Menzel)在一九八四年將本書改編為電影,赫拉巴爾曾表示:「這部本土色彩濃郁的捷克喜劇,是令人傷感的當代民謠,是傷人的幽默曲,一部具有悲劇內涵的怪誕作品。」
作者簡介
博胡米爾.赫拉巴爾(Bohumil Hrabal)
捷克作家,生於一九一四年,卒於一九九七年。被米蘭.昆德拉譽為「我們這個時代最了不起的作家」,四十九歲才出第一本小說,擁有法學博士的學位,先後從事過倉庫管理員、鐵路工人、列車調度員、廢紙收購站打包工等十多種不同的工作。多種工作經驗為他的小說創作累積了豐富的素材,也由於長期生活在一般勞動人民中,他的小說充滿了濃厚的土味,被認為是最有捷克味的捷克作家。
赫拉巴爾的作品大多描寫普通、平凡、默默無聞、被拋棄在「時代垃圾堆上的人」。他對這些人寄予同情與愛憐,並且融入他們的生活,以文字發掘他們心靈深處的美,刻畫出一群平凡又奇特的人物形象。赫拉巴爾一生創作無數,作品經常被改編為電影,與小說《沒能準時離站的列車》同名的電影於一九六六年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另一部由小說《售屋廣告:我已不願居住的房子》改編的電影《失翼靈雀》,於一九六九年拍攝完成,卻在捷克冰封了二十年,解禁後,隨即獲得一九九○年柏林影展最佳影片金熊獎。二○○六年,改編自他作品的最新電影《我曾侍候過英國國王》上映。
譯者簡介
徐偉珠
江蘇無錫人。1990年畢業於布拉格查理大學哲學院語言文學專業。在捷克學習工作十餘年,現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捷克語專業副教授。出版譯著《洪水之後》、《終極親密》、《嚴密監視的列車》、《雪花蓮的慶典》、《布拉格故事集》等十餘部。2019年9月被捷克外交部授予揚.馬薩里克銀質獎章,同年10月28日由捷克總統親自頒授一級功勳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