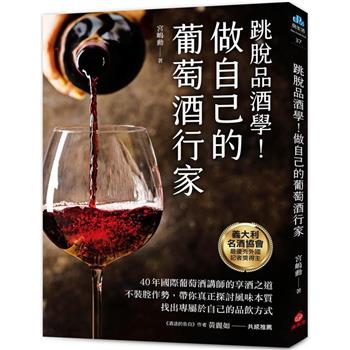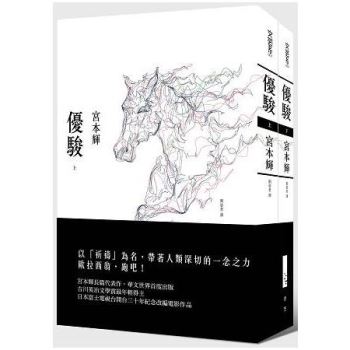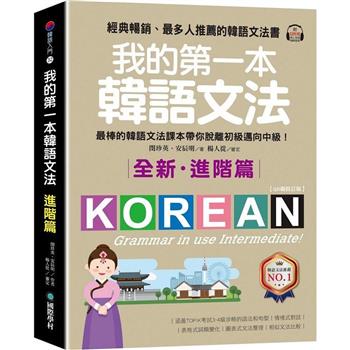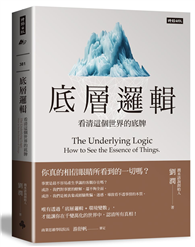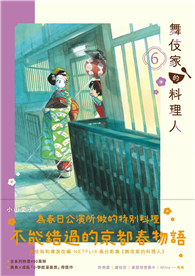【推薦序】
峰迴路轉讀蕭文◎吳鈞堯
二○一七年秋天,我在臺南國家文學館「現代文學」教室,開設文字實用班以及小說與散文創作等,為期五季。蕭文約莫二○一八年加入討論。學員女性為主,蕭文儒雅兼帥氣,一坐下來,很快就是焦點。他的話極少,也極少缺課,我在臺前,有時候與他眼神短暫交會,難免警惕,這傢伙是高手,會不會是踢館來著?
不會因為蕭文在或不在,而多講或少說,最是好奇,他什麼願意開金口,在女音中,為男聲添一份存在感,這情形歷經一季,我們的相處才不致履冰,一個來由是擁有共同朋友《中華日報》主編羊憶玫,以及對文學精進,持有一樣的熱情。
外溫內熱,我認識的蕭文。這性情早寫進文章,散文集《追尋府城》即為明證。書籍劃分「人物:為城市寫歷史」、「古老的小鎮:安平」、「臺南臺地:臺南東區」,「鷲嶺:蹲踞大鳥的城市」、「沙丘上的市區:府城南境」,目錄就很驚人。最易為的寫作是擴散型,隨著青春、親情、遊覽、美食等,一個觸發處長出一篇文章來。往好的說,是繽紛亮麗、題材多元,關懷面向廣,但我不喜歡文章處處著力,顯得缺乏重心,於是問題來了,怎麼寫才好?
我以為情緒要能沉澱,磨練為情感最好,一旦動情了、且是深情,才能就一個題材往下挖掘,猶如挖礦、挖井,絕不能挖個幾米,碰到硬壁就放棄,而需要鑿深,才能出土事物本質。一般寫臺南,多見整個臺南寫就一本,分區而為、且欲罷不能,非常少見,也唯有挖得深,才會在深層處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看見歷史的連結不是偶發,而是一連串的累積,這構成蕭文的寫作基礎,深入日本時代,當年的人事物為什麼今日還在?又被哪些力量干預,古蹟不復存,讓人在殘陽向晚,對著一座遺失的城牆、堡壘、寺廟,憑弔?
愁,尤其是肇因於失去的愁,常見且價廉,蕭文讓他的惆悵依附歷史,且反芻,事件的真相便容易一一剝解。他的行文客觀為尚,縱橫在報導與散文之間,「我」偶爾露臉,讓歷史經由他的雙眼、心眼,給一個存在更多的憐惜。〈沒有月臺的火車站〉結尾時寫著,「在這裡進出的人有限。它不需要人群,不需要嘈雜的聲音,餐飲店曇花一現……這裡又恢復往日的寧靜。寧靜是這裡唯一的聲音」。
這兒塑造了蕭文踏訪的姿態。源於內心的觸動,而能深入不復舊景的所在,歷史是長廊、更見蜿蜒,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回身走入,但蕭文做到了。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追尋府城的圖書 |
 |
追尋府城 作者:蕭文 出版社: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11-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85 |
二手中文書 |
$ 175 |
台灣歷史 |
$ 198 |
中文現代文學 |
$ 220 |
中文書 |
$ 220 |
現代散文 |
$ 225 |
台灣史概論 |
$ 225 |
文學作品 |
$ 252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追尋府城
作者從小在臺南長大,基於對故鄉深厚的情感,不斷地追尋這片土地上的故事,全文分為「人物:為城市寫歷史」、「古老的小鎮:安平,古名『大員』」、「臺南臺地:臺南東區」、「鷲嶺:蹲踞大鳥的城市」、「沙丘上的市區:府城南境」以人物的紀述和地景的變遷重塑臺南的今昔。
這兒塑造了蕭文踏訪的姿態。源於內心的觸動,而能深入不復舊景的所在,歷史是長廊、更見蜿蜒,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回身走入,但蕭文做到了。~吳鈞堯
作者簡介:
美國耶魯大學公共衛生碩士(主修醫務管理),淡江大學教育資料科學系畢業。曾任台南中華醫專專任講師、醫務管理科主任,嘉南藥專、致遠管理學院兼任講師,屏東基督教醫院執行秘書、醫療事務部主任…等。
著獎:
二○一五年旺報第六屆兩岸徵文獎
二○一二年台南文學獎
《水交社記憶》(二○一二年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化資產類調查研究與出版補助)
《府城竹籬笆歲月》。
推薦序
【推薦序】
峰迴路轉讀蕭文◎吳鈞堯
二○一七年秋天,我在臺南國家文學館「現代文學」教室,開設文字實用班以及小說與散文創作等,為期五季。蕭文約莫二○一八年加入討論。學員女性為主,蕭文儒雅兼帥氣,一坐下來,很快就是焦點。他的話極少,也極少缺課,我在臺前,有時候與他眼神短暫交會,難免警惕,這傢伙是高手,會不會是踢館來著?
不會因為蕭文在或不在,而多講或少說,最是好奇,他什麼願意開金口,在女音中,為男聲添一份存在感,這情形歷經一季,我們的相處才不致履冰,一個來由是擁有共同朋友《中華日報》主編羊憶玫,以及對...
峰迴路轉讀蕭文◎吳鈞堯
二○一七年秋天,我在臺南國家文學館「現代文學」教室,開設文字實用班以及小說與散文創作等,為期五季。蕭文約莫二○一八年加入討論。學員女性為主,蕭文儒雅兼帥氣,一坐下來,很快就是焦點。他的話極少,也極少缺課,我在臺前,有時候與他眼神短暫交會,難免警惕,這傢伙是高手,會不會是踢館來著?
不會因為蕭文在或不在,而多講或少說,最是好奇,他什麼願意開金口,在女音中,為男聲添一份存在感,這情形歷經一季,我們的相處才不致履冰,一個來由是擁有共同朋友《中華日報》主編羊憶玫,以及對...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局長序 尋訪臺南的文學蹤跡 葉澤山
編輯序 臺南人的文化輝光 陳萬益
推薦序 峰迴路轉讀蕭文 吳鈞堯
自序 蕭 文
人物:為城市寫歷史
古老的小鎮:安平,古名「大員」
臺南臺地:臺南東區
鷲嶺:蹲踞大鳥的城市
沙丘上的市區:府城南境
編輯序 臺南人的文化輝光 陳萬益
推薦序 峰迴路轉讀蕭文 吳鈞堯
自序 蕭 文
人物:為城市寫歷史
古老的小鎮:安平,古名「大員」
臺南臺地:臺南東區
鷲嶺:蹲踞大鳥的城市
沙丘上的市區:府城南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