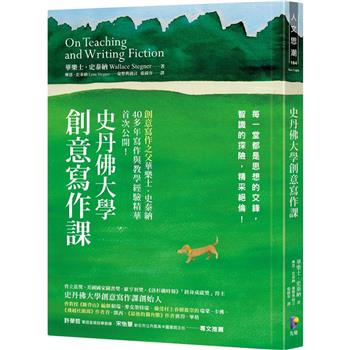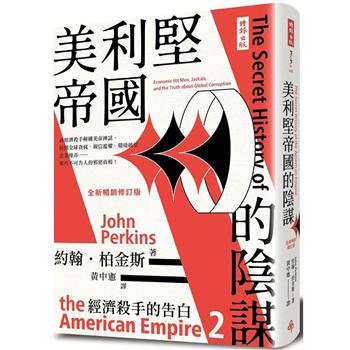導論(摘錄)
一、走向「文人園林」
中國古典園林歷史源遠流長,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以緩慢的步調積累經驗,自我修正,終而在明清時期完成精密的園林體系。
大抵而言,先秦兩漢以皇家宮廷園林為主流,起源於帝王狩獵之囿與通神之臺,既循天人合一思想體系,發展人化自然,同時想像神仙境界,再現山嶽與海島風景。皇家園林規模宏大、體勢雄偉,如上林苑包括有山水、動植物、宮苑、臺觀與各種生產基地,提供居住、生產、遊憩、狩獵等主要功能。至魏晉南北朝時期,貴族豪門在政治權力之外,同時擴展大規模的莊園經濟,經始山林,巡視地利,在遊覽中發現山水之美,注目鑑賞,進而建宅棲遲,頤養閑暇,於是山水莊園既是創造經濟價值的世族資產,同時也具有遊賞山川的功能,近則提供日常性遊賞活動,遠則作為向外窮名山、泛滄海的據點。這些貴族文士遊覽山川、賞玩風景,奠定此後人物與景象關係發展的基礎,迨及隋唐,遂有「文人園林」典型的出現。
唐王朝開創了意氣風發的盛世,帝國復歸統一,豪族勢力和莊園經濟受到抑制,科舉取士助成了社會階層的流動,文士成為引領社會的主力。文人仕宦經歷中參與地方公共山水的開發與整治,如柳宗元之發現永州山水隱蔽之美,白居易之開闢忠州東坡、杭州西湖。對於自然的理解和鑒賞、宦海浮沉的感懷、人生哲理的體悟,都融鑄進入造園活動之中。不同的山水與個人經驗進入私人園林,表現為不同的型態:王維的輞川鬆動了與經濟、政治權力緊密聯結的莊園形態,成為其學佛習禪的道場;白居易藉由理水置石,草木植栽等手法,先後在江南江北興建草堂、修造宅園,結合自己的人生經歷賦與空間主體性意涵。他們都標誌了文人園林興起的新里程,於後代園林發展影響深遠。宋明以降,有別於漢唐的閎放風度,文化走向內歛沉潛,心性之學昌明,修持工夫就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文人園林作為體現心性操持的場所,在微觀境界中追求體系的自我完善。加上市民經濟穩定成長,雅俗文化交流,追尋精緻美感品味成為普遍風氣,園林藝術技法日趨精密,發展至晚明清初臻於巔峯。
園林作為人們參與改造形成的第二自然,在唐宋以降文人手中逐步凝塑出一貫相承的理想特質,成為引領中國古典園林的主流,從而影響皇家貴戚以及釋道寺觀園林。這種理想特質表現在對相關物質的認識、選擇與操作上,表現在景象結構的創建手法與意境營造上,更表現在園林居遊的生活經營與價值實踐上,筆者嘗試由四個層面進行說明:
首先,園無定制,精在體宜,園主選擇性地運用人為建築與水石、植栽、動物等自然元素進行有機的組合,構園手法並無定制。園林所在地理環境、位置形勢不同,園林主人的審美品味、人生態度有別,影響建物體量形製的規劃,植栽水石的選擇處理,因而也就更發展造園手法的多樣性和自由度。茲以白居易為例,方其貶謫江州,在香鑪峰下營構草堂三間,藉由簡易的工法,消融人為與自然的隔閡,由謫遷的過客轉成「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自覺擁有了整座廬山。這是在山林江湖之地營建居室,將人引進自然之中。白居易晚年經營洛陽城內履道宅園,引入伊渠水、太湖石、白蓮、青板舫、華亭鶴等,建構了一個水竹相映、恍若江南的情境。這是在城市中圈圍出一片領域,經由疊山理水等手法,將自然引入人境。發展到明清時期,園藝技法更加豐富多變,分景也益加繁複,見諸記載者,如明初陶宗儀的南村別墅有十景,中葉吳寬的東庒有二十四景,稍晚王獻臣的拙政園有三十一景,後期安紹芳的西林園有三十二景,秦耀的寄暢園有五十景,祁彪佳寓山有四十九景等。分景數量的增多,必然同時聯結著個別景象個性特色的追求與組織導引的複雜化,是以陸續出現許多造園專家,以及分享造園心得的文字。然不論是園主自行規劃,或者委託專家造園,都須依立園基址條件相地合宜、構園得體,是以各各手法有別,得失互見,非複製拼貼可成,每一座有生命的園林都是嶄新的創作。
其次,雖由人作,宛自天開。園林內部元素的安設配置,景面的選取呼應,路徑的導引組織,構作成之於人。其中優秀的園林主人不只要技藝純熟,不落斧鑿痕跡,更追求精神境界上的上參造化。不同於穴居野處,園林是人工與自然的協調共構,唐人的發現美景,造亭築室,即每每強調剪焚蓁莽、刳闢朽壤的人為努力,而努力的意義在於幫助自然彰顯其原被隱蔽的美感。柳宗元自言始得西山「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宴遊經驗之前,先行「斫榛莽,焚茅茷」;薛存義整治零陵縣東山麓,「發牆藩,驅群畜,決疏沮洳」,始建零陵三亭;崔能之亭亦然:
於是刳闢朽壤,剪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疏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遊亭,以宅厥中。
人力與自然並非對立,人為的努力是為幫助造物者彰明其本然面貌,所以說「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這種天人關係的體認實為文人園林精神的基本總綱,流貫到晚明,遂可見到精神相通的體會。如祁彪佳的「開山誰是主,摩詰擬前身。為愛林泉好,翻令結構新」、「鴻濛闢川巖,缺陷猶未補。補之以人工,開山我作祖。林壑秉清淑,靜者乃能取」、「丘壑有靜緣,真宰每獲惜,解會非其人,不易言開闢。胎因要以癡,圓果要以癖,運之勇猛心,鴻濛便可劈」,體認鴻濛開闢仍存缺陷,川巖林壑秉清淑之氣,只是停留於自存狀態,現成地擺置於天壤間,無能自補缺陷,而有賴人的努力;人自覺承擔下來,不是以人力向自然挑戰,反而是以人力去成全自然、實現自然。「誰是主」、「我作祖」並非誇示物質性宰制權力的占有,反而更接近於一種責任的明確體認與承擔,這是經歷宋明理學文化脈絡下的發展。
再次,因地借景,內外相參。一般而言,私人園林因涉及所有權問題,多有其邊界限定,隨基勢高下、地形方圓,安排建築形製與花木水石的關係,實體的構作工程固然限於園內,但景象的收攝完成、意境的鎔鑄蘊涵則穿透園林的邊界,融合內外為一。如杜甫素樸的浣花草堂「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通過一門一窗,草堂和園外自然山水取得聯繫,收天地無限之景於一園之內,也將園內有限之景融匯到無限的宇宙天地之中。王維的竹里館,在竹林中提供他停駐的據點,人與自然的關係通暢和諧,彈琴長嘯之聲可以迴盪於竹林的間隙,乃至傳揚於夜空之中,而一輪明月轉出於竹篁上頭,彷彿有情來當空相照。這種建立內外聯繫的借景手法簡單而巧妙,為歷代園林所普遍運用。宋司馬光的獨樂園築有見山臺,以望洛陽城郊林薄茂盛的萬安、軒轅、太室山,那是平常家居無法望見的視野。張德堅有感於東坡〈赤壁賦〉所謂江上清風與山間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遂於禾江之洲作堂名曰「無盡藏」,以收取江山清風明月而儲於斯。明代張懋之筠芝亭以樓閣收攬山水雲霞,園中古木樓臺也與遠山落照相互掩映交匯:「樓曰霞外,南眺越山,明秀特絕,亭之右為嘯閣,以望落霞晚照,恍若置身天際,非復一丘一壑之勝已也。」此類人在園中恍若置身天際的感受,不只獲得身體感官的審美欣趣,在縱覽天色蒼茫,浮雲滅沒中,往往更交雜著心靈神思放逸八極、超然塵外的自由,以及環顧塵寰、醉醒清濁間的思索。即如李滉的陶山書堂座落在東西翠屏山與洛川之間,他將自然山水收攝進來作為書堂景象,每喜登上川岸山麓平臺眺望水天,「縱翼揚鱗孰使然,流行活潑妙天淵」,「若知體用元無間,物物天機妙飛揚」,看到天理活活潑潑地流行,也聯結朱熹半畝方塘的心性取譬,自我策勵主敬應物,將工夫與道體相融為一。這些園居經驗結合著審美視野的擴展、心靈境界的開拓、天人之際的體察、心性工夫的惕厲,都是文人在園林中的真實感受,相隔數百年遙相呼應。
復次,時空並行,生滅相即。園林雖然主要表現為空間的形態,其實不能外於時間而存在。園林的時間性一則表現為景象導引程序的先後久暫,通過或斷或續、或動或靜的遊覽途徑,展示了諸景象構圖的參差掩映,產生了時間序列;二則表現為園林景象在晨昏迭代、四季流轉間不同形態的交替關係;三則表現為園林由始造到興華再到頹敗的生命史。這三層時間的向度相互重疊綰合,而人活動於其中,以人生的時間尺度與之俯仰對應,交映互答,生發意義,造園、居遊與書寫莫不是落在時間的維度中進行,不待一一指明。此處僅以二例略見園林時間之作用,或在轉瞬幾微之間,或在年歲積累之中。王維輞川詩的「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最底層是行遊所見景象的先後序列接續,其次是山林水澗與空中雲嵐虛實間的相互滲透,然後是水窮與雲起一滅一生的抑揚銜接中同時喚起即生即滅、不生不滅的思悟,詩人的閒行與坐看,即在園居生活的日常時間裡,也即在學佛尋道的工夫流程裡。至於「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則靜觀辛夷花開落的過程,它經過漫長的孕育過程結苞開放,而後紛紛凋落,詩句中彷彿將此數月凝聚於眼前一瞬,呈現緣起緣滅的從容。不論是面對當前倏起旋變的景象,或者在悠長的歲月中由紛陳的色相中照察本然實相,這是學佛人所見的園林時間。而白居易之於履道園,〈池上篇并序〉歷數長慶四年(824)至大和三年(829)間的經營,由擁有宅園起,增建粟廩、書庫、琴亭,增置天竺石、華亭鶴、太湖石、白蓮、折腰菱、青板舫、歌樂隊、釀法、青石、琴與琴曲等,是這座園林逐漸脫離舊主、轉生新貌的過程,也是主人罷杭州刺史、蘇州刺史、刑部侍郎,得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的歷程。這六年間主人與園林的時間漸漸重疊,終於「洎吾不才身,今率為池中物矣」,此園進入新里程,成為主人實踐中隱之地。這是在較長時間段落中,園林逐漸成長凝塑出新生的性格,與主人的生命里程同步進行,終而相互交匯為一。
明清以降園林風氣興蔚,園林書寫表現於更繁複的園記、園林專志、社集題詠、書信、日記之中,觸及更多有關空間景象的時間流變、特定時間延滯下的空間景象、園林經驗或事件的記憶、古園的修復與今園的未來預想等課題,許多時間的面向被開拓出來,本書中將多所涉及。
前述四個層面的說明與舉證旨在揭示文人園林有別於前代帝王苑囿、貴族莊園之處,不再以展示權力財富或提供生產享樂功能為主,而有更多關於藝術審美、物我關係、天人之際、園林歷史等層面的關注。可以說園林在主人宅邸之外,親密地提供一處審視自我與世界關係的場域。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在勞績中安居:晚明園林文學與文化的圖書 |
 |
在勞績中安居:晚明園林文學與文化 作者:曹淑娟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0-04-14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545 |
中文書 |
$ 546 |
文化研究 |
$ 546 |
文學 |
$ 546 |
Social Sciences |
$ 558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在勞績中安居:晚明園林文學與文化
從嘉靖後期至明清易代百年間,正是明代政治日漸頹唐而社會文化仍蓬勃發展的時期,園林作為綜合性藝術文化的載體,在這段時期有著十分精緻成熟的發展,也因時代變局,更鮮明呈現繁華鼎盛與轉瞬丘墟的雙面性,今日尚能從留存的豐富文獻中訪見。本書作者廣泛蒐集文獻,精讀文本,並從不同角度抉發議題,分為四個單元:園居經驗與話語表述、生活實踐與體道境界、時間流變與意義詮釋、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分別選擇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觀察相關人物興築、居遊園林過程中生動的語文表述與實際行動,深入探索他們的園林技藝、審美理念,以及在人生價值的選擇、存在意義的領會上所作出的真誠努力。
作者簡介:
曹淑娟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曾任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哈佛大學東亞系訪問學人,捷克查理士大學短期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園林文學、明清文學、中國詩學,關懷人的存在境域與感受。著有《華夏之美──詩歌》、《漢賦之寫物言志傳統》、《晚明性靈小品研究》、《流變中的書寫──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孤光自照──晚明文士的言說與實踐》以及〈江南境物與壺中天地──白居易履道園的收藏美學〉、〈《千載佳句》文本空間的建構及其意義〉、〈杜甫浣花草堂倫理世界的重構〉、〈演繹創傷──〈同谷七歌〉及其擬作的經驗再演與轉化〉等論著多種。
章節試閱
導論(摘錄)
一、走向「文人園林」
中國古典園林歷史源遠流長,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以緩慢的步調積累經驗,自我修正,終而在明清時期完成精密的園林體系。
大抵而言,先秦兩漢以皇家宮廷園林為主流,起源於帝王狩獵之囿與通神之臺,既循天人合一思想體系,發展人化自然,同時想像神仙境界,再現山嶽與海島風景。皇家園林規模宏大、體勢雄偉,如上林苑包括有山水、動植物、宮苑、臺觀與各種生產基地,提供居住、生產、遊憩、狩獵等主要功能。至魏晉南北朝時期,貴族豪門在政治權力之外,同時擴展大規模的莊園經濟,經始山林,巡視地利,...
一、走向「文人園林」
中國古典園林歷史源遠流長,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以緩慢的步調積累經驗,自我修正,終而在明清時期完成精密的園林體系。
大抵而言,先秦兩漢以皇家宮廷園林為主流,起源於帝王狩獵之囿與通神之臺,既循天人合一思想體系,發展人化自然,同時想像神仙境界,再現山嶽與海島風景。皇家園林規模宏大、體勢雄偉,如上林苑包括有山水、動植物、宮苑、臺觀與各種生產基地,提供居住、生產、遊憩、狩獵等主要功能。至魏晉南北朝時期,貴族豪門在政治權力之外,同時擴展大規模的莊園經濟,經始山林,巡視地利,...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後記
筆者多年來以園林為窗口,觀察中國文學如何處理人與所在世界的關係,晚明是我特別關注的一段時期。早期聚焦於遺存豐富文本的祁彪佳及其寓山園林展開論述,已於2006年出版《流變中的書寫──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十餘年來一邊追溯唐宋文人的前行典範,對於晚明園林文學與文化的探索並未停歇,本書正文收錄的十篇論文,在長期的規劃中終於一一完成。
書中論題或者進行文士群體共相的分析,如討論明人園記中的有無論述、陳繼儒等《十六觀》系列的寫作出版;或者選擇個別案例以彰明典型,如袁宏道與柳浪、李滉與陶山書堂、汪汝謙與...
筆者多年來以園林為窗口,觀察中國文學如何處理人與所在世界的關係,晚明是我特別關注的一段時期。早期聚焦於遺存豐富文本的祁彪佳及其寓山園林展開論述,已於2006年出版《流變中的書寫──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十餘年來一邊追溯唐宋文人的前行典範,對於晚明園林文學與文化的探索並未停歇,本書正文收錄的十篇論文,在長期的規劃中終於一一完成。
書中論題或者進行文士群體共相的分析,如討論明人園記中的有無論述、陳繼儒等《十六觀》系列的寫作出版;或者選擇個別案例以彰明典型,如袁宏道與柳浪、李滉與陶山書堂、汪汝謙與...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導論
一、走向「文人園林」
二、明代的社會文化轉型
三、社會空間的延伸
四、文本空間的建構
五、隱喻空間的形成
六、本書論述綱領
第一單元 園居經驗與話語表述
小有、吾有與烏有──明人園記中的有無論述
一、論題說明
二、小有──從生活實感到存有論的觀想
三、吾有──園林藝術創造主體的提出
四、烏有──意中之園的紙上虛構
五、餘論──遊園者的觀點
晚明藝文《十六觀》系列的話語唱和與經驗觀想
一、前言
二、話語唱和(一)──《讀書十六觀》的出現與續演
三、話語唱和(二)──藝文《十六觀》的推擴與...
一、走向「文人園林」
二、明代的社會文化轉型
三、社會空間的延伸
四、文本空間的建構
五、隱喻空間的形成
六、本書論述綱領
第一單元 園居經驗與話語表述
小有、吾有與烏有──明人園記中的有無論述
一、論題說明
二、小有──從生活實感到存有論的觀想
三、吾有──園林藝術創造主體的提出
四、烏有──意中之園的紙上虛構
五、餘論──遊園者的觀點
晚明藝文《十六觀》系列的話語唱和與經驗觀想
一、前言
二、話語唱和(一)──《讀書十六觀》的出現與續演
三、話語唱和(二)──藝文《十六觀》的推擴與...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