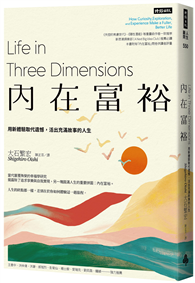圖書名稱:你可以獨立,但不孤立
生病、搬家、換工作、財務問題,在人生的各個階段,
你可能會發現自己突然就陷入孤立無援的處境!
當你需要協助時,臉書明明有四百個朋友,卻不知道要打電話給誰?
翻遍通訊錄卻找不到人可以傾訴?
本書是一個資深心理諮商師走出孤立處境的練習,
當你找不到支持、覺得被孤立時,一定能從中得到暖心指引。
儘管網路社群發達且幾乎有求必應,社會孤立卻是日益猖獗的傳染病。當我們因為種種原因陷入孤立時,不只會感到孤單寂寞,更會對於自己的處境感到羞愧,因為我們的社會把孤立無援的人給污名化了。
本書作者芙爾‧沃克是一位六十歲的單身女性,在經歷一場大手術後卻無人照應,轉換職場與環境造成生活處處碰壁,她本身是個資深心理復健諮商師,卻同樣羞於向人求助。當她終於走出孤立後,她決定對面臨同樣問題的人伸出援手,協助他們重建社交支持系統,擴大朋友圈,建立社會安全網,培養歸屬感。在更深層的心理上,她也告訴人們如何和孤獨為友,而不是以它為恥,並且對於其他陷於孤立的人們敞開心房。在你找不到人可以倚靠的時候,這是一本暖心、坦誠而撫慰人心的作品。
本書結合作者與十五位個案的真實故事,輔以社會研究和心理諮商的專業,獻給許許多多因疾病、喪偶、失業和照顧生病的家人而被孤立的人們。
作者簡介
芙爾.沃克Val Walker
維吉尼亞聯邦大學復健諮商碩士,專研悲傷、失去與失能的心理諮商。具有專業復健諮商師資格,曾服務於退伍軍人協會,也曾擔任喪親團體的支持團體,並曾於維吉尼亞州醫學院從事相關研究。之後從事訓練工作,於緬因州、維吉尼亞州和麻州輔導相關諮商人員。第一本著作《安慰的藝術》(The Art of Comforting),很快就被許多大學與研討會指定為學生和醫院員工的訓練手冊。
譯者簡介
嚴麗娟
台大外文系畢業,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語言學碩士及西敏斯特大學(Westminster)雙語翻譯碩士。譯作包括《自閉兒瑜伽療法》、《生物科技大商機》、《女人要的不只是愛》、《暖化?別鬧了!》、《吃對營養,享瘦健康:德國方法醫師的代謝平衡密碼》、《猩猩心事:寧姆猩斯基的故事》、《吸引力漩渦》、《財富的吸引力法則》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