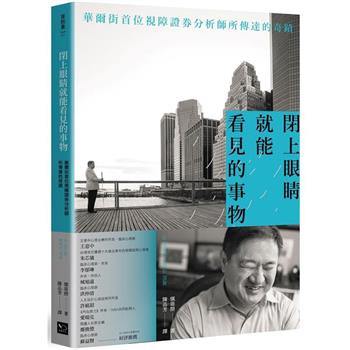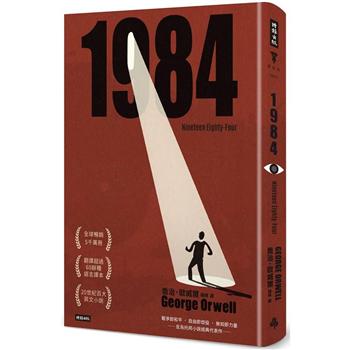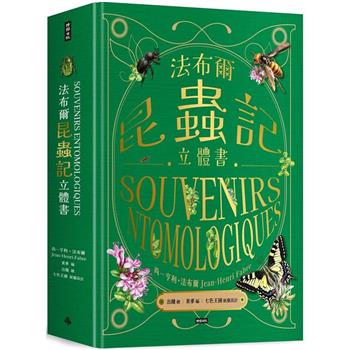作者王威智愛往山裡跑,既是爬山客,又是花蓮縣消防局山域義消,兩度前往八通關越嶺道協助搜尋救援。
他用腳走出《越嶺紀》,於「新高登山東口」〈西出中仙道〉,途經〈KSS-748〉,在瓦拉米拒絕〈一起做蕨吧〉的誘惑,不認為〈噴水池多美麗〉,想像一百年前一群〈遠離大分〉的布農族人,小心翼翼〈安渡土葛〉,在〈托馬斯的蘋果樹〉下旁觀合照的日警與警眷,爬上〈小的大水窟〉翻過中央山脈,最後一點也不躑躅地回到山下的日子。
玉里大通路邊曾豎立「八通關越道路」起點標,
一旁還有一支方尖碑,
寫著「新高登山東口」。
抵達八通關大草原時,
一度生出逆向荖濃溪源流爬上玉山的念頭。
背包上肩猶豫甩開,
我們按計畫順著陳有蘭溪走完全線——
正是為了仔細看才上路越嶺。
喜愛爬山的人都明白山頭只是目的地,目的地往往不是爬山最有趣最有意思的地方。八通關越嶺道,日治三大越嶺道之一,與合歡、能高一樣,在化身熱門的健行路線前,都是用來壓制原住民族的警備道路。走進八通關越嶺道,全程不攻山頭,反而令人輕易受到時間的召喚,聽見從前在這條順著等高線爬升又低降的老路來來去去的人們的故事。
山不一定非百岳不爬,文章不一定用手寫。
*假設能在日本撤出臺灣前後爬上佳心的石階,人們將會看見完好但空蕩蕩的駐在所,還有療養所,推開門或許還能聞到一絲微弱的藥水味,診所才有的那種氣味,比殘存的記憶還稀淡。——〈KSS-748〉
*在跟漣漪一樣隱約的泠泠水聲中,一個警察正從屋裡搬出木凳,一條大狗毛色溫潤,模樣相當健康,從駁坎間的石階走上來,踱過水池,趴落在凳子旁。……景物開始在快門前方凝固:陡急的山坡、山路旁兀立直挺的松樹、廳舍、樹木、池邊的矮植株,東來的日光與所有的陰影……——〈噴水池多美麗〉
*圓鐘高掛,午後一時十分,四月二十一日,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拉荷阿雷不熟悉平地世界的月日年,但熟知此時正是水鹿生產期。他想吿訴知事先生收到鹿角之時,一頭鹿嬰或許正落地。——〈遠離大分〉
*有個男人蓄八字鬍,抿嘴但隱隱顯出笑意;有個年輕人折彎左臂搭在一旁同事肩上;女人盛裝但不到華麗的地步,看起來反而和山裡的日子一樣平淡;一個男孩口含食指,一個因突來的鳥鳴而分心歪頭,還有一個在快門按下的那一瞬間低頭不知在看什麼。——〈托馬斯的蘋果樹〉
本書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創作
作者簡介:
王威智
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碩士。喜歡棒球和籃球,進入中年後還可以和小朋友玩玩。喜讀地圖,喜歡走進臺灣山。曾獲時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1995年主編《臺灣民主國郵史及郵票》,20多年後重新編輯出版《臺灣老虎郵》(蔚藍,2018);著有《我的不肖老父》(東村,2012)、《製圖師的預言:十六世紀以來關於花蓮的想像》(蔚藍,2014)、《凡人的山嶺》(蔚藍,2019)及繪本故事《兩個鼻孔一起minasi》、《爺們不是好兄弟》、《惡地公的花生糖》(以上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8)等。
章節試閱
一起做蕨吧
繞過黃麻山的西北向小支稜,越嶺道轉向南方,沿黃麻溪東岸山腹腰繞並開始爬升,坡度和緩,從海拔八百公尺開始,朝黃麻溪源頭蜿蜒而上,感覺就像一邊走一邊找哪裡適合過溪。當山路遇到從一顆編號「補武55」的三角點往西北西方低降的稜線,已不知不覺走完一段若有似無的下坡路了。
「補武55」是日治殖產局在「玉里測量區」進行三角測量所埋設的森林三角點之一,基石截面十五公分見方,南面刻「森林三角點」,北面有一個大大的「山」字。從一九三○年四月下旬開始直到年底,前後兩百五十幾天,測量班班長武元忠男率領五人隊穿梭於海岸山脈和中央山脈丹大山以南的東部山區,單是在八通關越嶺道沿線至少就埋了七個森林三角點。關於測量路線,目前並未發現明確的紀錄,根據三角點的編號順序,推測可能由東往西,先海岸山脈後中央山脈。至於前往「補武55」的路徑,或許與今日攀登大里仙山的慣行路線一致,也就是從佳心駐在所後方的山坡往上攀爬,上稜後轉南經黃麻山抵達目的地,一顆標高一六八七公尺的山頭。他們把這個山頭定為相當於四等三角點的「補點」,埋下基石。依慣例,武元班長在編號前冠上帶隊人也就是他自己的姓氏首字。
如果武元班長一行真的採取此一路線,那麼他們可能在佳心駐在所度過舒適的一夜,隔天清早才上山。海拔漸高,耕地漸稀,他們走進潮濕的原始森林,地上鋪滿松蘿,彷彿走在鬆鬆厚厚的地毯上,偶爾有人摔倒或踩空,但無大礙,這裡是一片魔境般的森林,沒有人確知雙腳踏踩的青翠之下是堅實的地面還是夢。森林茂密,枝幹交錯橫生,每一棵樹都像發了綠毛的珍獸,映入雙眼的除了綠還是綠,無松蘿之處則為蕨類的領地。抵達一六八七山頭之前,他們將遇見一片龐大的杜鵑林,松蘿從地面往上爬滿樹林,一直往稜線高處延伸,甚至與地衣、苔蘚同時密密包覆同一棵樹。他們偶爾透過林縫望見西方的新康山,像一堵巨大無匹的高牆,斷然遮蔽視野,轉頭往東北方遠眺,則是拉庫拉庫系溪對岸逐漸拔高的玉里山稜線。
九十年前,武元班長指揮大家在不怎麼寬闊的山頂挖洞,按照施作規範埋設基石,如今這座更常被稱為大里仙山前鋒的山頭不知因土石堆積或基石下陷,使得「森林三角點」的「點」字沒入土中,整顆基石在地表上只露出三、四寸。對森林三角點有所知者有限,森林三角點分主、次、補、交四個等級同樣鮮為人知,至於後綴的「武」、「川」、「沖」、「近」、「藤」……如果不是有意追索,恐怕註定只能是泛黃的紙頁裡千千萬萬個鉛印字之一,就像遭到埋沒的基石,沒有原因,但必然發生。
現在是衛星時代,大地測量使用更精準的工具,三角點不再是非有不可的基準,如同各種用來度量世界的「尺度」標準從物質世界的實體「原器」一一變成物理常數,例如著名的「一公尺」鉑銥合金棒不再是「公尺」,「真空中,光在二億九千九百七十九萬兩千四百五十八分之一秒行進的距離」,這才是「公尺」。從前每一瓦白熾燈的發光強度是一燭光,現在「一個頻率為五四○.○一五乘以十的十二次方赫茲的單色輻射光源,在某方向的輻射強度為每立弳六百八十三分之一瓦,則該輻射源在該方向的發光強度」才是一「燭光」。
重新建立衡量的標準、重新定義或重新命名,都是推翻既有認知顛覆熟悉的世界的手段,看似無奇,卻鬆動事物的本質,令其產生根本上的變動。這大約也是瓦拉米過去一百年的經歷,從malavi、蕨(ワラビ)到瓦拉米,如今這個據點最為人知的就是一日健行來回的折返點,或繼續深入拉庫拉庫溪流域的中繼站,從登山口到瓦拉米這一段長約十四公里的越嶺道經常被稱為瓦拉米步道,聽起來彷彿瓦拉米就是終點。
離開佳心後,繞過西北方的小尾稜,路徑一轉向南方,一顆大岩石迎面而來,從靠山那一側向山徑橫衝而出,狀似鯊魚,缺乏軀幹,短少尾部,只有一顆大頭,不如真鯊修長,膨脹的比例令它看起來豐滿而圓潤,但一樣有明顯而突出的吻部,斜斜往下裂開透空的岩縫是嘴,微微張開,露出隱隱然的詭異笑意,酷似偷偷撇頭的奸邪一笑。最滑稽的是魚頭頂上一片姑婆芋「純林」,大大小小幾十株,株株挺立,乍看一片枯葉也沒有,綠意盎然,活力充沛。一隻白眼在近吻端處圓睜直視,那是好事者的傑作,眼上甚至掛著一彎睫毛。
大魚頭人稱大白鯊,不知何故擋在路中央,行人不是從路緣側身繞行,就是彎腰低身而過。這不太像越嶺道該有的樣子,這條路的原始用途是行軍、輸送火炮、運補必需品,以確保拉庫拉庫溪流域的「安穩」,即使「大白鯊」再可愛有趣,終究是阻礙通行的岩石,不會任其擋道。這一段路走過好幾次,就是沒能看出改道的痕跡。
大白鯊左側有隱隱約約的踩踏痕跡,朝東南方往上爬升,還不到路跡那麼清晰可辨的程度。後來查閱電子地圖,發現大白鯊附近標註了一條路,盡頭註明布農族舊居地,如果將一九一六年的《蕃地地形圖》套疊現代地圖,可以發現越嶺道上方黃麻山稜脊兩側的山坡曾經是布農族人的聚居地「カシン社」,也就是佳心社。考古學家在此尋獲遺跡,數量龐大,但似乎有另一群人比布農族人更早抵達此地,並居住了一段時間。不同時期的考古學家在同一地區——即拉庫拉庫溪與黃麻溪合流點東南方黃麻山稜線西北側的緩坡——都曾經發現史前器物的殘片,有石器也有陶器,由於鄰近黃麻山和黃麻溪,這片史前先人生活過的山區被命名為「黃麻遺址」。
考古學家在黃麻遺址挖出陶片,其中多數為「夾石英砂陶」,這種材質的陶器不屬於拉庫拉庫溪,而是秀姑巒溪中游的物產,他們認為如果這些陶器是「黃麻製造」,那麼原料應該取自秀姑巒溪中游,不然就是以成品的形式輸入拉庫拉庫溪流域,而使用這些陶器的人們可能跟陶器一樣,都來自縱谷的秀姑巒溪中游。這一群古人的身分至今未獲確認,他們為何以及何時前來也不明。由於那些陶器與阿美族的素面陶器型式相近,部分學者因此推測這群在黃麻遺址活動的先人或許是阿美族的祖先,也就是說阿美族人早在布農族人之前可能就在這片山林活動。
黃麻遺址與佳心舊社的分布範圍大致重疊,但海拔稍低,一往高處進入佳心舊社的範圍,史前遺物就愈少,這似乎暗示晚來的布農族人選擇黃麻遺址的高海拔地帶建立聚落,在史前先人生活過的地方展開新生活,換句話說先人在史前某一段時期可能遍布整個黃麻山的緩坡地帶。如果這項假說成立,只要得知黃麻遺址的陶器(夾石英砂陶)文化何時結束,就可以推斷世居布農族人何時翻山越嶺,來到中央山脈以東的新天地,並順著流水的方向遷移,選擇合適的據點,在拉庫拉庫溪流域建立一處又一處家園。黃麻的遺物像時間的密碼,只是自發掘以來尚未破解。
大白鯊之名不知起於何時,有沒有布農式名字同樣不得而知。假如這顆魚頭長久以來一直盤踞原地,則更早的史前先人又如何叫喚?由於缺乏記載,未來相關文獻出土的機率也十分渺茫,所有關於這顆巨岩之名的疑問可預期地將繼續成謎。唯一可以斷定的是,大海離拉庫拉庫溪太遠,鯊魚也不是日常風景,「大白鯊」這個海味十足的名字多半不是黃麻先人也不是布農先民的手筆。如果慮及五十年來資訊距離急速縮短的事實,則著名的驚悚電影《大白鯊》將是大白鯊之所以得名最富說服力的源起之一,果真如此,最早也不過是四十年前的往事。
黃麻山以北這一片向拉庫拉庫系河谷低降的山林,除了可見的滿地落葉層層相疊,還有一代踩過一代的文明的痕跡,能夠察明並分析辨認自然好,對於不求甚解的一般人如我者,知道曾經有過不同的足跡也就夠了。
路過黃麻。
臨黃麻溪谷一側的陡壁不知幾十年前就已嚴重坍方,山路改道從駐在所面前的階梯直接爬上並穿越平台,如果匆匆路過,可能不會發現隱沒在草葉下的駁崁,因此忽略舊道在平台下方盤繞而過。為了有利的守勢,在越嶺道上方高處建立駐在所並以階梯連接是日警建立駐在所的一般原則,布農族的對外聯絡道通常也開在部落下方,兩者對於安全與監控的設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一如其他駐在所,在今日黃麻很難看見舊時的痕跡,平台上是一片綠油油的草地,彷彿是經過某種抹除人為痕跡的神器擦拭後的成果,除了平坦得不太自然的地形,和一口落在平台邊緣山坡下的混凝土槽,此外毫無舊跡,翠綠的蕨葉從槽裡伸出,在陽光照耀下愈加青翠,蓬勃的生氣讓人感到愉悅,卻無助於理解水泥槽的用途,最可能用來蓄水,但水源來自何處?就算對平台進行測量,取得所有關於平台和水泥槽的數據,例如長寬、厚薄、座標、方位、海拔高度……,仍難以得知原貌,至於老照片,數量極少,只能提供模糊的輪廓。
就算「喀西帕南事件紀念碑」這樣完好存在的遺物,也不能確保歷史事件被「正確地」敘述。這座離黃麻駐在所二、三十分鐘的紀念碑,今多被稱為「喀西帕南事件紀念碑」,光憑這幾個字應該沒有人不感到疑惑,僅靠碑文很難明確指出其「立場」。一九一五年五月十二日布農族人對喀西帕南駐在所發動奇襲,日警傷亡慘重,駐在所毀於蓄意縱火,大約半年後撤廢,實際運作不及三年便匆匆跳下歷史舞台。我們當然知道紀念碑由日人起造,紀念的對象是遇襲身亡的日警,因為立碑不是布農族人慣行的舉動,把「カシバナ事件殉職者之碑」讀成記成「喀西帕南事件紀念碑」,大約是為了避免從日本人的角度發聲所感到的尷尬,又或者不願令布農族人不快,無論何者,好像都不是直視往事該有的眼光。
一九四四年,臺灣總督府撤除八通關越嶺道東段沿線全數駐在所,此時日本戰況漸漸告急,物資與財政一日乏於一日。促使日警撤離的原因可能還包括拉庫拉庫溪流域早在一九三五年前後就完成集團移住,多數族人已下山過起平地生活。對日本當局而言,比起三十年前備受不屈的布農族人威脅的年代,山區已平靜許多,平靜到可能不再需要監控。無論如何,日本人在山上留下不少廳舍,塌倒前是人們進出山間過夜討暖的好地方,傾頹的檜柏樑柱牆板無疑是方便又有效率的柴火——這可能是除了華巴諾和太魯那斯以外各駐在所連殘餘建材也不可見的主要原因,也可能二次利用變成獵寮工寮的部分建材,如賽珂。
六○年代臺灣啟動「經濟奇蹟」,那時布農族人「離家」還不是太久遠的往事,甚至相隔不到一個世代,當年下山的族人中如果有十幾歲的年輕人,那麼他們踏進「奇蹟」的年代之時正值四、五十歲壯年。即使下山後三十年都不打獵,來自山林的基因也不會消失,他們從小跟隨父祖,十幾歲的少年已能獨當一面,說他們是傳統餵養的最後一代也不為過,回到山上打獵理所當然,事實上他們一直出入山區,即使在堅持並貫徹保育的國家公園境內,也遏止不了打豬獵羊的天性和渴望。
日本統治臺灣,處處留下殖民的痕跡,戰後與民生無關但與國族情感有所牴觸的建物——例如神社和紀念碑——曾經遭到計畫性抹除。拉庫拉庫溪流域深山裡幾十處駐在所和附屬設施並未淪陷於仇恨巨浪的襲擊,八通關越嶺道東段沿線有十餘座紀念碑,每一座都孤單地立在路邊,除了風吹日曬,幾十年來安好無損,看不出人為破壞的跡象。布農族人一直出入山區,不可能沒有注意到那些豎立在路邊的紀念碑,但他們似乎不打算花力氣推倒那些刻著日警或受其雇傭的非布農族原住民族人名字的紀念碑。平地的「國仇」似乎屬於另一個國度,不適用於拉庫拉庫溪的人們,他們有自己的仇怨,一種平地人不能輕易理解的情感。從某個角度來看,此地的布農族人更勇於直視歷史的遺物,那些紀念碑的主人每一個都是布農族人刀槍下的亡魂,也是布農族人不怯於反抗的見證人。
一起做蕨吧
繞過黃麻山的西北向小支稜,越嶺道轉向南方,沿黃麻溪東岸山腹腰繞並開始爬升,坡度和緩,從海拔八百公尺開始,朝黃麻溪源頭蜿蜒而上,感覺就像一邊走一邊找哪裡適合過溪。當山路遇到從一顆編號「補武55」的三角點往西北西方低降的稜線,已不知不覺走完一段若有似無的下坡路了。
「補武55」是日治殖產局在「玉里測量區」進行三角測量所埋設的森林三角點之一,基石截面十五公分見方,南面刻「森林三角點」,北面有一個大大的「山」字。從一九三○年四月下旬開始直到年底,前後兩百五十幾天,測量班班長武元忠男率領五人隊穿梭...
作者序
【序】
代序.西出中仙道
深秋清晨五點,天光仍黯淡,風很輕,掀不動地上的枯葉。我們一行各自負重,帶上必要裝備,在黯淡天光微弱山風中,走進八通關越嶺道。
不爬山時,地圖經常是攤開的,有時持筆比劃,有時伸指沿地圖上的路徑神遊,例如中橫迴頭彎上中央尖、南湖西稜轉南稜經中央尖東峰上中央尖再橫渡危崖過甘藷、無明、鈴鳴轉南續經斷崖上畢祿下大禹嶺,也曾站上義西請馬至峰頂的三叉路,遙望劇烈西折後再度折向南去的中央山脈,只要兩、三天就可以接上曾經走過的馬利加南、馬博拉斯以至秀姑巒、大水窟。類似的神遊遐想不知演練過多少回,路線老早畫進腦袋,感覺熟悉,其實陌生。這些都不是一般路線,但也不見得多麼稀奇,早有前人留下紛雜的足跡和疏詳不一的紀錄,那些我以為人跡罕至的深山,其實不像紙上的比劃。
八通關越嶺道是其中之一。
一九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可能是毛利之俊在《東臺灣新報》的最後一個上班日,因為兩天後《臺灣日日新報》刊出一則人事短訊,簡略直白說了毛利離開報社。這一則短訊僅兩行,不及二十個字,稱不上新聞,卻不難看出這個媒體人在東臺灣擁有某種聲望。
一年半以後,毛利帶著攝影師從蘇澳出發,取道臨海道路——可能搭乘東海自動車株式會社巴士——抵達花蓮市區。這一段路和途中緊緊交鄰的山和海,是我熟悉的北花蓮,距今五十年前,濱海小城花蓮的和式氣息猶仍留存,感覺得到,甚至聞得到,這是純粹的個人感受,不是嚮往,我的歲數不夠長故無涉眷戀,當時我認識的理解的北花蓮就像同學之中有人體內流著四分之一日本血液這樣的事實。
毛利由北而南,自平野深入中央山區,在花蓮的最後一段旅程,他看見秀姑巒溪寬闊的出海口和嬌小的奚卜蘭島,我則因罕有的家庭出遊而對同樣的景物留下模糊的印象,我看見一模一樣為流水恆常洗刷的白玉巨石,還看見毛利未曾見的橫跨兩岸的虹橋。
緊湊的行程化成《東臺灣展望》,以一百零六面相當於八開的紙頁來「展望」花蓮。毛利對橫斷中央山脈的越嶺道投以極大的注目,他一步一步走進中央山地,最後三條越嶺道以近四成篇幅佔據毛利眼裡的花蓮,其中八通關越道一線就費去二十四頁,彷彿那是一條複雜得不可盡訴的路。
有很長一段時間,毛利走過的山徑抵達的深山對我就是陌生的傳說。
除了山水樹石,毛利為沿線每一處當年服役中的駐在所及其附屬設施至少安排一張照片,並且總是以房舍為背景,招集駐守的警察警眷,在深遠的山間留下一幅又一幅「紀念照」。經過時間醃漬煎熬,紙頁泛黃而易碎,泛黃易碎的紙張和其上的照片一向輕易吸引目光。一開始我深受毛利的照片所惑,只看見他看見或他選擇讓世人看見的,無力追究他到底怎麼看,也無能細察他在觀景窗之後可能如何受到時代的侷限,只能揣摩他的腳步越過塔次基里溪出海前最後一座鐵線橋,轉入太魯閣峽谷,在奔騰溪水的激越聲中踏上「合歡越」,回頭往南穿越吉野村,西進木瓜溪谷之上的「能高越」,最後取道「中仙道」,南下花東縱谷繁華卻又嫻靜的小鎮玉里,再岔出中仙道轉進「最後未歸順蕃」的傳統領域。
毛利於暑夏時節穿行於拉庫拉庫溪南岸的「八通關越」,從北回歸線以南的熱帶闊葉林開始,幾天之間就走上高海拔的檜柏松杉,踏上越嶺點大水窟池,在狂放的風中爬上階梯,在(臺中)州(花蓮港)廳界之上來回走動,眺望中央山脈最高峰秀姑巒山與大水窟池西北方以池為名的大水窟山之間的稜線。《東臺灣展望》雖未提及,但毛利之俊一定注意到吳光亮的「中路」,甚至看見比今日所見更清晰可辨的清軍營盤址。他說大水窟附近僅有細草、山躑躅(杜鵑)和散發「神秘之美」的榛柏(圓柏),視野既然無礙,就不可能看不見路跡明顯的「中路」。或許當年他望著「中路」,正如今日我見八通關越嶺道。
關於毛利去而復返的八通關越嶺道,很長一段時間我所知的其實是久遠的描述與歷來行程紀錄的混合產物,一種建立在文獻、他人足跡和不同版本地圖之上的想像。二、三十年以來,我想像卻無法細述那些離日常很遠很遠的山、路、人與事,沒有走過就是沒有走過,那些往事跟山下多數人的生活幾乎沾不上關係,跟風一樣吹逝以後無輕無重。如此,我又何以對或毀壞或改道的山徑、幾乎看不出痕跡的駐在所教育所有所持執?
當我有能力將陰森圖書室裡紙頁翻動的輕響變成深秋山風拂過草樹的清音,將當年手中紙張的重量化作頓重的步伐,我想做以及所能做的就是去看看泛黃紙頁裡毛利之俊與攝影師鏡頭下的天光是否仍然朗亮,是否一樣耀眼地射穿樹冠並在山徑上閃爍。拉庫拉庫溪或許不如八、九十年前豐滿,不過泠泠水聲仍舊揚自深深的谷底,鐵線橋無一完整存留,但鹿鳴、山風橋門仍在,意西拉殘橋尚未墜毀,也還能在十里駐在所臨谿一側仰望毛利或許曾經仰望的新康山,鑽行他一定也曾鑽行的沙敦隧道,如此一來,我就離毛利的展望更近一點,有機會窺探像他這樣一個來自殖民國度的知識份子,究竟期待在幽遠的山地看見什麼。
毛利之俊留下照片和夾雜漢字的文章,我曾深深為之撼動。除了地名,儘管日文漢字往往不保有漢字的意義,我仍試圖推敲其所描述,不甚解其義並不妨礙「八通關越」如貫穿臺灣一般貫穿我的心思,這條路催促我反覆在地圖上遊走,反覆瀏覽他人的紀錄,同一篇或者新尋得的。這些演練與神遊一再重覆,實際上是預習卻似乎極熟悉,以至於有時誤以為是複習或回想一條已經走過的路,那些已知的崩塌、下切、高繞,盡可能熟記,步程、水源、夜宿點則無不瞭然。
我不期待看見毛利之俊看見的,官廳房舍早已銷腐,山徑斷毀,樹木榮枯,我充分理解不可能看見毛利之俊曾經眺望的風景,也不可能重覆與他一樣的路線。對於時間,八、九十年是一截無可無不可的線頭,之於人世——尤其二十世紀以後——則漫長而痛苦,足以扭轉幾代人的運命與處境。後來的命運與處境,毛利之俊來不及展望。
第一晚,我們前往玉里——如同當年打算走進八通關越嶺道的行旅——在一位熱情的山友家裡叨擾過夜。他的盛情宛如此地富有盛名的縱谷米倉,飽滿而熾烈,他確實也是當地知名且傑出的農夫,耕地數十甲,白米、紫米、紅米,想像得到的各「色」稻米都種得出來,可以應客戶的需求選植特定品種。這位具備現代視野的農夫在拉庫拉庫溪水澆灌的寬闊原野建立家園和田園,比起多年前來自喀西帕南部落的一個布農家族顯然幸運多了。這個布農家族被迫下山,打算落腳玉里,一踏上平地卻發現沒有動物的蹤跡,對於靠山吃山偶爾打獵的天性無疑是莫大的打擊,三、四天後,他們妥協地走向近山地帶。這是九十年前的往事,並非人人都樂意或習慣平坦的生活。
隔日透早,一個天光即將亮起的深秋清晨,我們自花東公路——毛利筆下的「中仙道」——岔出,走進縱谷西側山區,展開一趟百公里的橫斷行。送別的友人揮手致意,他們說,幾天後大山另一邊見。
【序】
代序.西出中仙道
深秋清晨五點,天光仍黯淡,風很輕,掀不動地上的枯葉。我們一行各自負重,帶上必要裝備,在黯淡天光微弱山風中,走進八通關越嶺道。
不爬山時,地圖經常是攤開的,有時持筆比劃,有時伸指沿地圖上的路徑神遊,例如中橫迴頭彎上中央尖、南湖西稜轉南稜經中央尖東峰上中央尖再橫渡危崖過甘藷、無明、鈴鳴轉南續經斷崖上畢祿下大禹嶺,也曾站上義西請馬至峰頂的三叉路,遙望劇烈西折後再度折向南去的中央山脈,只要兩、三天就可以接上曾經走過的馬利加南、馬博拉斯以至秀姑巒、大水窟。類似的神遊遐想不知演練過多...
目錄
代序.西出中仙道
KSS-748
一起做蕨吧
噴水池多美麗
遠離大分
安渡土葛
托馬斯的蘋果樹
小的大水窟
南方躑躅
代序.西出中仙道
KSS-748
一起做蕨吧
噴水池多美麗
遠離大分
安渡土葛
托馬斯的蘋果樹
小的大水窟
南方躑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