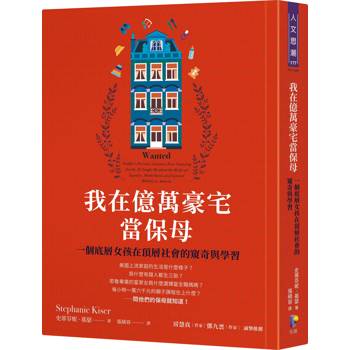這是一本關於法國的古今全史,也是一紙寫給法蘭西的情書
英國大眾歷史作家界的祖師爺諾里奇爵士,以幽默風趣、引人入勝的筆調,
引領讀者走進「高盧雄雞」兩千年的迷人歷史
Amazon 4.2分、Goodreads 4.0分 讀者好評
《牛雜》《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旁觀者》《星期天獨立報》《鄉村生活》《今日歷史》
《每日電訊報》《泰晤士報》《歷史揭密雜誌》一致盛讚【內容簡介】
這本《法蘭西全史》的對象並非專業歷史學家,他們會發現書中每一件都是他們已知的事。本書是為一般讀者所寫,也就是法國人非常動人的稱之為「有著一般感官知覺」(l’homme moyen sensual)的普通人,而且寫作動機是出於:相信說英語的一般男女對法國史知識相當有限。……我知道我之前說過這件事,但我幾乎可以肯定這將是我的最後一本書。我喜愛寫作的每一刻,並將其視為,我對這輝煌國家多年來給予我的幸福,所獻上的感謝之意。──約翰.朱利葉斯.諾里奇
提到法國的歷史,映入讀者眼簾的可能是聖女貞德、路易十四世、戴高樂等著名人物,也可能是英法百年戰爭、法國大革命、拿破崙戰爭等重要事件,但作者認為大多數人對法國的認識也就僅止於此,我們需要一則動聽的故事把諸多法蘭西的歷史人、事、時、地、物串聯起來,填補人們心中法國史的空白,約翰.朱利葉斯.諾里奇爵士的《法蘭西全史》就因此而生。
本書將從決心阻止羅馬將軍凱撒入侵的那位高盧人酋長說起,到查理大帝是如何略施小計取走教宗手上的帝冠。從法蘭西人大批加入東方的十字軍戰爭,到聖殿騎士團是如何在一夕間走入歷史。從太陽王路易十四世震鑠古今的功業,到法國人民攻陷巴士底監獄的風暴。從法國軍隊搭乘大隊計程車奔赴一次大戰戰場的戲劇場面,到二戰諾曼地登陸扭轉世界命運的一擊,《法蘭西全史》將帶領你我穿越兩千年趣味性十足、令人大開眼界、包羅萬象的法國歷史。
約翰.朱利葉斯.諾里奇爵士是英國老牌的歷史學者,所寫的西西里、威尼斯共和國、拜占庭帝國、教宗和地中海相關歷史多年來深受讀者喜愛。《法蘭西全史》是諾里奇爵士作家生涯的閉門顛峰之作,也是寫給他最愛的法國的一紙情書,獻給每一位迷戀法國、鍾情法國的男女。
【國際書評】
滿腔熱情之作……可嘆諾里奇在不久前去世,他最為平易近人的學究氣息貫穿全書,這位如長輩般的導師邀請各位一邊喝著葡萄酒,一邊聽他娓娓道來兩千年法國史。從高盧人講到查理曼,從凱撒講到戴高樂。他以熟練但溫和的筆調描述性、死亡和網球。閱讀本書可以搭配一次暑假的法國之旅,或讓你突然想造訪法國。──《牛雜》
諾里奇這本法國政治史從維欽托利談起,到一九四五年的戴高樂結束,它邀請我們一起對歷史上的偉人肅然起敬,甚至使我們對這些人的勝利感同身受……極具啟發性。──《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這是一本有溫度又宜人的法國簡史,它以歡快的筆調鎖定一般讀者,這是諾里奇所寫的情書,獻給他熟悉的法國。──《旁觀者》
一本以英文寫成的簡明法國史絕對有其必要,而且在許多方面來說,諾里奇都是寫作本書的最佳人選……他對法國的熱愛可以追溯到童年時期,這份愛意顯然也處處出現在這本易讀又具娛樂性的歷史書中。──《星期天泰晤士報》
諾里奇處理歷史事件的方式,就像是和讀者在火爐邊親切地閒聊。──《星期天獨立報》
作者以十足的魅力和對法國顯而易見的熱情訴說這則故事……我的孩子時常問我,英國中等教育普通證書(GCSE)的教學大綱為什麼不是介紹英國歷史,而是神祕兮兮地探究威瑪共和國、納粹德國與俄國。他們想要的是以全面、易讀和令人享受的故事檢視我們島嶼──這正是諾里奇書寫法國的方式……這本值得推薦的簡明歷史書籍,最吸引人的就是它娛樂性高,同時見聞廣博,筆調流暢,機智又帶著一抹幽默感:閱讀這本法國史是一大樂事,它令人愛不釋手。──《鄉村生活》
作者簡短的結語「法國的精髓」,幾乎可說是本書最精采的部分。他列出這個令人陶醉但偶爾也令人惱怒的國家裡他最喜愛的事物,包括建築、繪畫與音樂,他對這些文化懷抱最大的熱情,並且自始至終都以忠實可信、迷人與機智的方式加以描述。──戴斯蒙.蘇爾德(Desmond Seward),《今日歷史》
不久前過世的諾里奇在他最後一本書中,以令人欽佩的輕快氣氛與都市風格著手處理兩千年法國史這令人望之卻步的龐大主題。它的語氣裡帶著那麼點(或許是刻意的)幽默作家塞拉爾(W. C. Sellar)《一○六六年之種種》(1066 and All That)的味道──「卡佩王朝的國王們逐步打造法國,把如同卡士達醬糊成一團的卡洛林王朝轉變為一個統一的國家」──此外他逗趣的注解值得讀者單獨重溫其內容。──《每日電訊報》夏日選書
諾里奇以大量精采故事,不費吹灰之力講述法國歷史:風流倜儻的國王、可怕的瘟疫和傳說中的晚餐。──《泰晤士報》
諾里奇以他一貫溫暖而愉快的引導,帶領讀者踏上一場從歷史之初到二十一世紀的法國史之旅……他以高度的娛樂性介紹這迷人的國家。──《歷史揭密雜誌》
作者簡介:
約翰.朱利葉斯.諾里奇 John Julius Norwich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旅行文學作家、電視節目名人。父親是邱吉爾時代的內閣情報部長、二戰後英國首任駐法大使、諾里奇子爵達夫.庫伯(Duff Cooper)。服完兵役後,他在牛津大學新學院(New College)取得法語學位。一九五二年他進入外交部,曾任職塞爾維亞貝爾格勒和黎巴嫩貝魯特的英國大使館,也曾經隨英國代表團前往瑞士日內瓦參加裁軍談判會議。一九五四年繼承父親的諾里奇爵位。
諾里奇爵士在一九六四年離開外交圈,開始他的作家生涯,擔任英國皇家文學學會、皇家地理學會,以及倫敦古董學會會員,並由於其在人文領域的貢獻,於一九九三年獲頒英國皇家維多利亞勳章。
諾里奇爵士著作等身,出版過數十本歷史作品,題材包括西西里史、威尼斯共和國史、拜占庭帝國史、教宗史和地中海史,以及書寫四位近代著名君王,英國亨利八世、法國法蘭西斯一世、西班牙查理五世,鄂圖曼蘇萊曼大帝的《四君主》。《法蘭西全史》是筆耕一生的諾里奇爵士的最後一本著作,於二○一八年三月出版,作者也在同年六月過世,享年八十八歲。
譯者簡介:
何修瑜
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紐約理工學院傳播藝術碩士。自從十歲看了《簡愛》之後就立志成為譯者,長大後如願以償。譯有《在風暴來臨之前:羅馬共和國殞落的開始》、《伊斯蘭新史》、《鄂圖曼帝國的殞落》等十餘本著作。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極度黑暗(前五八至八四三年)
法國正如英國,是一座民族熔爐,利古里亞人(Ligurians)、伊比利人、腓尼基人和凱爾特人只是其中少數,更何況古代高盧還有五百餘種不同部族。然而正如我之前可能已經提到過的──史前史最好還是留給史前史學家。或許值得記載的是,有一群來自小亞細亞愛琴海岸、熱愛冒險的希臘人在大約西元前六百年建立了馬賽城,但可惜他們沒有留下現存的歷史遺跡,也沒有留下太多文化。我們的故事其實是始自西元前二世紀末,這時羅馬人征服現今法國東南角,並設為羅馬共和國的第一個行省(此地至今還保留「普羅旺斯」這個名稱,也就是Provence),將新城市塞克斯泉城(Aquae Sextiae),也就是後來的艾克斯普羅旺斯(Aix-en-Provence)設為首都。接下來還有許多繁榮的城市,尼姆(Nîmes)、亞爾(Arles)和奧蘭治(Orange)不過是其中一些,就如古羅馬作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所說:「與其說是行省,此處比義大利本土更像義大利。」當時普羅旺斯必定是個非常宜人的城市。
請外國人說出法國第一位英雄時,只有極少數人會追溯到比查理大帝更早之前的時代。但對法國人來說,他們最早的重要領導人物是維欽托利(Vercingetorix),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偉大的戰士國王」或「偉大戰士們的國王」。而所有關於他的文字敘述都來自羅馬人,這一點更讓人訝異,因為能從貶抑他的聲譽中獲利最多的就是羅馬人。南法是羅馬帝國最先設立也是最富饒的行省──正因如此富饒,羅馬人迫不及待想繼續擴張。引用凱撒最著名的開場白,眼見鄰近的高盧「分成三部分」,狡猾的羅馬人決定操弄這三個彼此敵對的部族間長久以來的緊張關係。凱撒一直聲稱,他在西元前五八年入侵高盧,主要的理由是防衛和先發制人。北邊的高盧部族曾經無數次劫掠這個羅馬行省,有幾次是嚴重的攻擊,因此他決心免除將來更多的麻煩。這或許部分為真,戰爭當然也讓羅馬人建立萊茵河上的天然邊界。但眾所周知的是,凱撒野心勃勃。羅馬共和國不久就變成獨裁國家,更多權力集中在更少數的人手中。如果最終能如願以償將大權一手在握,他需要一支軍隊,而一場高盧的大戰就能使他達到目的。
雖然有些部族已經擁有一般程度的文明,對抗凱撒的這些高盧人基本上還算是野蠻人。他們沒有稱得上是城鎮的聚居地,村莊往往只是幾間泥巴和樹枝搭成、以茅草作為屋頂的小屋,周遭是簡陋的圍籬。他們幾乎沒什麼農業知識,也對此毫不在意。高盧人是放牧人,不是農夫,他們豢養羊和豬,獵捕數量總是不虞匱乏的鹿,這些人一直以來都是肉食者,也都喜歡打鬥。高盧人的馬術或許還勝過羅馬人,但他們缺乏羅馬人的精良武器,但有著勇氣與決心,再加上人數上的優勢,使得他們成為可怕的敵人。在幾次血腥交戰中他們獲得勝利,然而最終還是被羅馬人打敗,理由很簡單,或許是因為部族社會形態,使得高盧人無法達到任何程度上的政治統一。
大致上因為如此,戰爭前期他們沒有出現卓越的領袖。但在西元前五二年初,當凱撒在山南高盧(Cisalpine Gaul)集結軍隊時,三十歲的維欽托利成為居住在現今奧弗涅(Auvergne)阿維爾尼人(Arverni)的首領。他馬上就和鄰近部族結盟,很快便取得一支龐大的軍隊。第一個步驟就是說服高盧人,他們的敵人是羅馬人,而不是自己的鄰居。維欽托利顯然是一位很有感染力的戰略家,他在法國中央高原(Massif Central)的日爾戈維亞(Gergovia)首次迎戰入侵者,這是一場決定性的勝利。根據凱撒自己的敘述,羅馬人喪失了約七百五十個軍團,其中包括四十六名百夫長,讓這位卓越的年輕將領面臨迄今遭遇過最嚴重的威脅。決心不計一切代價趕走羅馬人的維欽托利採取焦土政策,他將能夠提供食物或庇護所的所有村莊摧毀,但結果是:居民在這場游擊戰中付出的代價和入侵者一樣大。當這些部族要放火燒了富有的阿瓦利肯(Avaricum)聚落時卻遲疑不前,他們辯稱此地的天然屏障就能提供保護(該聚落建在一座山丘上,而且周圍有沼澤環繞)。維欽托利勉強同意,但當羅馬圍城成功時,卻證明他才是對的。同年九月,凱撒在阿萊西亞(Alesia)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從戰場上逃離的高盧人被羅馬騎兵攔截,殺到幾乎一個也不留。首領維欽托利是幾位倖存者之一,他第二天就正式投降。西元一○○年左右,羅馬時代偉大的希臘歷史學家普魯塔克(Plutarch)在史書中告訴我們,「所有戰事的主要發動者」維欽托利是如何穿上最華麗的盔甲,也將他的坐騎精心裝扮,騎馬出營。他騎馬繞著王座上的凱撒一圈作為受降儀式,之後下了馬,將盔甲脫下丟到一旁,不發一語坐在凱撒腳邊,直到被帶到牢裡囚禁為止。
維欽托利必定很想自我了斷,一世紀之後的英格蘭女王布狄卡(Boadicea)被羅馬人打敗後據說便是如此。不過他沒有,他被囚禁了五年,最後在凱撒的凱旋式中於羅馬街頭遊街示眾,依照慣例被處以絞刑。十九世紀時,主要拜拿破崙三世之賜,他被譽為第一位偉大的法國民族英雄。在法國中部的克萊芒費朗(Clermont-Ferrand)有一座這位年輕將軍的雄偉騎馬雕像,他的馬兒正在狂奔。在他最後一次輝煌戰役可能發生的地點立著另一座雕像,雕像圓柱形的底座上刻有本章開頭引用的銘文,雕像臉上還被賦予海象般茂密的短鬚,直到二十世紀初法國政治家喬治.克里蒙梭的年代為止,都難以有人與之匹敵。
戰爭又拖延了一兩年,但在阿萊西亞之戰後,高盧人實際上已屬於羅馬了。高盧人實在沒什麼理由喜愛他們的征服者,凱撒對他們的嚴厲往往到了殘酷的地步,而且絲毫不尊重他們。他毫不留情地掠奪財物,沒收他們的金銀,將許多人賣身為奴。但隨著時間過去,高盧人開始明白,他們的損失還是有得到補償。沒有比共同的敵人更能使眾人團結一致,在羅馬政府的統治下,高盧各部族前所未有地團結,部族體系已經消失。羅馬人建立了三個羅馬政府,分別是凱爾特高盧(總督的行政中心位於里昂)、大約位於現在比利時的比利時高盧,以及在法國西南部的阿基坦高盧。他們立刻開始安頓下來,在五十年間,高盧的地貌已經改頭換面,正如一世紀前的法國南部行省。這裡不但出現新的道路、城市、鄉村別墅、劇院、公共澡堂,還初次有了以犁耕作的田地。現在,只要稍加努力,受過教育的高盧人也可能獲得羅馬公民身分,享有隨之而來的特權。身為羅馬公民,他們甚至能被授權指揮軍隊或擔任行省的行政官員。
★★★
高盧在接下來的五百多年依舊由羅馬人統治,這段時間大約和現代英國與亨利八世統治時期的間隔相當。到了二世紀初,人們開始談論一種新的宗教,它源自遙遠的亞洲行省,但卻在歐洲各地與歐洲以外地區產生深刻的改變。正如羅馬文明,基督教文明也緩緩從地中海向北擴張。西元一○○年,第一批傳教士已經抵達馬賽,又過了將近一世紀,基督教福音的傳播已遠至里昂。如今已成為一個帝國的羅馬,在宗教方面寬容得令人訝異,只要口頭上支持皇帝的信仰,人民大致上就能自由信奉自己喜愛的宗教。然而基督徒連這樣都不願意,於是迫害在所難免。從西元六四年的羅馬大火之後,在羅馬皇帝尼祿主導下,對基督徒的迫害斷斷續續持續了兩百五十年,並且在第三與第四世紀間的羅馬皇帝戴克里先統治時,到達黑暗的頂點。殉教者不計其數,第三世紀巴黎主教聖德尼(St. Denis)在頭被砍下時正在佈道勸人悔悟,據說他平靜地拾起頭顱,走了幾英里來到之後以他為名的修道院位址。
不過接著黎明到來,三一三年二月,兩位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和李錫尼(Licinius)頒布米蘭敕令,永久確立了整個羅馬帝國對待基督徒的寬容政策。二十五年後,君士坦丁自己也受洗了(雖然不可否認是在他臨終前)。在接下來的幾世紀,法蘭西雖然飽受宗教戰爭摧殘,基督教地位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卻沒有再次動搖。
第五世紀初,羅馬帝國氣數已盡,幾乎擋不住哥德人、匈人和汪達爾人等蠻族侵略,這些人不斷從東北方揮軍南下,尋找更溫暖的氣候與更肥沃的土地。他們不只是入侵的軍隊,而是包括男女老幼的大批移民。東哥德人、西哥德人和汪達爾人至少是半文明的,他們都是日耳曼民族,也都是基督徒。不幸的是這些人也是信奉異端的亞流教派(Arianism),堅決相信耶穌基督並非如正統基督教信仰的主張,與天父同為永恆的存在,且存在於同一本體,而是由祂在某個特定時間為了某個特定目的所創造出來,是為了拯救世界而挑選出的媒介。這種信仰使得他們與教會產生極大的爭執,但他們並不想摧毀一心景仰的羅馬帝國。他們想要的只是一個生存空間,找到一個安居的地方,於是他們就在這裡安定了下來。
然而匈人也就是蒙古人,卻是徹頭徹尾的野蠻人。他們大多露宿野外,鄙視一切農業活動,甚至不屑於熟食,傳說他們會在騎馬時把生肉夾在大腿和馬腹間按摩,使肉質變軟。至於衣飾,他們喜歡穿長袍,但除了以亞麻為材質,令人訝異的是他們也殘忍地把田鼠皮縫成皮衣,他們會一直穿著皮衣不脫下,直到田鼠自己脫落(四一六年羅馬通過一條法律,禁止任何穿著動物毛皮或蓄長髮的人進入羅馬城內)。匈人首領阿提拉(Attila)矮小黝黑,他長著獅鼻、頭大眼睛小、鬍鬚稀疏散亂。然而幾年內他已經讓整個歐洲對他聞風喪膽,不管在之前或之後的歷史上,他引起的恐懼無人能及,或許只有拿破崙能與之匹敵。
匈人在四五一年初渡過萊茵河,橫掃法蘭西,遠至奧爾良,直到六月二十日,才在馬恩河畔沙隆城(Châlons-sur-Marne)外的卡塔隆平原(Catalaunian Plains),被羅馬與西哥德聯軍擊退。如果阿提拉真的繼續進攻,法國歷史可能會截然不同。但就算沒有阿提拉,局勢已經相當不妙。整個帝國搖搖欲墜,連橫越阿爾卑斯山的通信都已斷絕,來自羅馬的命令無法順利傳達。四七六年,可憐的西羅馬帝國最後一任皇帝,只是個孩童的羅慕路斯.奧古斯都路斯(Romulus Augustulus,這兩個名字的字尾都有「小」的意思)被罷黜,這個結局並不令人訝異。
雖然在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繼續宣稱擁有羅馬帝國主權,但羅馬帝國已名存實亡,高盧在所謂的國王、公爵和伯爵統治下,分裂為許多小規模的蠻族國家。不過正如我們所知,自然界中沒有真空狀態,某個國家遲早會比其他國家強大,並取得最終的控制權,而這一次是薩利昂法蘭克人(Salian Franks)。他們相當晚才抵達高盧,首次出現於二世紀,而後在接下來的三百年逐漸與高盧―羅馬人融合,並且在這過程中把他們的名稱賦予現代法國。四世紀下半葉,墨洛溫(Merovech)之子希爾德里克(Childeric)建立了他們的王朝,也就是後來所稱的墨洛溫王朝,而希爾德里克的兒子克洛維於四八一年成為法蘭克人的國王。幾乎將整個高盧統一在墨洛溫王朝治下的克洛維,極有宣稱自己為第一任法蘭西國王的權利。他的名字「克洛維」(Clovis),相當於後來法文中的「路易」(Louis),在法國君權結束之前,這曾是十八位法蘭西國王的名字。
如果我們以看待英雄的眼光看克洛維,就像我們看待維欽托利,那將是美事一樁。可惜我們不能如此,因為他是個怪物。他偶爾會以師出有名的戰役消滅敵人,就像四八六年的蘇瓦松(Soisson)戰役中,他一舉結束西羅馬帝國在義大利領土以外的政權。然而他更常採用冷血謀殺的方式,洋洋得意地暗殺所有可能威脅他的人,無論對方是不是法蘭克人,這個做法很管用。他在五一三年左右死去(確切日期無從得知),他的統治權擴展至現代法國的大部分地區以及比利時,並往東方延伸,遠達德國北部。主要受到他的勃艮地妻子克洛蒂爾達(Clotilde)唆使,他不情願地放棄原本信仰的亞流教派,於四九六年聖誕節接受了天主教信仰。從這天開始,法蘭西亞流教派的命運就已確定。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有愈來愈多人民追隨他的腳步,因此法蘭西和日耳曼逐漸走向宗教統一之路,在接下來的一千年中持續天主教信仰。也要拜這次的施洗之賜,三百年之後,查理大帝和教宗利奧三世(Leo III)才能結為聯盟,促成神聖羅馬帝國的誕生。
第一章 極度黑暗(前五八至八四三年)
法國正如英國,是一座民族熔爐,利古里亞人(Ligurians)、伊比利人、腓尼基人和凱爾特人只是其中少數,更何況古代高盧還有五百餘種不同部族。然而正如我之前可能已經提到過的──史前史最好還是留給史前史學家。或許值得記載的是,有一群來自小亞細亞愛琴海岸、熱愛冒險的希臘人在大約西元前六百年建立了馬賽城,但可惜他們沒有留下現存的歷史遺跡,也沒有留下太多文化。我們的故事其實是始自西元前二世紀末,這時羅馬人征服現今法國東南角,並設為羅馬共和國的第一個行省(此地至今還保留「普羅旺...
作者序
「終其一生,我對法國都抱持著某種概念。」戴高樂將軍回憶錄的開場白,已經成為世界著名的佳句。而我,也總是以諸多方式,懷抱著如是的概念。我猜想,這是源自一九三六年九月,將滿七歲的我初次造訪法國的經驗。當時,我的母親帶我去艾克斯萊班(Aix-les-Bains),主要目的是斷絕我對那位英國奶媽的依賴。一切彷彿就在昨日,我依舊能感受到越過英倫海峽的興奮之情;穿著藍綠色夾克的成群腳夫,身上散發出令人窒息的大蒜味;來自四面八方嘈雜的法語(拜五歲開始每星期兩次的法語課之賜,這些法語我已經聽懂不少);廣大無邊的諾曼地,放眼望去奇蹟似地沒有任何樹籬;薄暮時分的巴黎北站裡,頭戴法國軍帽和手拿一根短小雪白色警棍的警察,以及我看到艾菲爾鐵塔的第一眼。我們抵達艾克斯萊班一棟有著美麗小花園的樸素公寓,一個叫席夢的年輕女孩照顧我,而我母親則是為了矯正我,從早到晚跟我說法文。
戰前我還去過兩次法國,第一次是和我父母在巴黎待了一週,做了一般人在巴黎會做的事。我們乘坐塞納河遊船,遊覽我覺得無聊得要死的羅浮宮,也去了令我著迷不已的下水道。我們還登上凱旋門屋頂,這裡比艾菲爾鐵塔更能飽覽巴黎市全貌,就好像從飛機上往下看一樣。當然我們也上了艾菲爾鐵塔,不只爬上去,還在塔頂上極其時髦的餐廳裡吃午餐。我父親宣稱那是他最喜歡的一間巴黎餐廳,因為這是唯一一間完全坐在室內用餐的餐廳。我還記得,我看到這城市滿街都是餐廳有多麼驚訝,而且人們都在戶外用餐。這種把餐桌放在人行道上的情形,在戰前的倫敦幾乎是聞所未聞。我其他的記憶還包括:幾乎每個青少年都頭戴貝雷帽、身穿燈籠褲,數以百計這樣打扮的青少年,為了蒐集郵票而定期聚集在香榭麗舍大道圓環的大市場裡。
八年後,我父親成為大使,我們的生活因此變得十分不同。我還在上學,但現在假日我們總是在法國度過(包括仍在二戰期間的一九四四年聖誕節),而且是在一座大宅邸裡。我相信,這坐落於聖奧諾雷黑市郊路(Rue du Faubourg Saint-Honoré)的沙羅斯酒店(Hôtel de Charost,這是它的正確名稱),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大使館。這棟建築物曾經為拿破崙的妹妹寶琳.波格塞(Pauline Borghese)所有,而後被滑鐵盧戰役後曾短時間擔任英國大使的威靈頓公爵買下,在接下來的兩百年中一直是英國大使館所在地。
那年冬天天寒地凍,大使館是少數暖和的地方之一,而且會無限量供應威士忌與琴酒,這些東西在戰爭開始後就不見蹤影。每天晚上,裡面全是從尚.考克多(Jean Cocteau)以來的巴黎上流社會人士,大使館很快變成被稱做「綠沙龍」(Salon Vert)的某種機構。其中的社交女王是女詩人,也是我父親的情婦路易絲.德.維爾莫林(Louise de Vilmorin),她有時候會在大使館裡待上好幾週(我母親幾乎和我父親一樣愛她,毫無妒意,這並不奇怪,她是我認識的最迷人女性之一。我們成了好友,她教我好多首美妙的法語老歌,我在晚餐後會彈吉他唱著這些歌)。出入大使館的政治家寥寥無幾,卻有許多作家、畫家和演員。我記得暱稱為「寶寶」的舞台設計師克里斯提昂.貝哈德(Christian Bérard),也是常來報到的人物之一。有天傍晚,他帶著他的小哈巴狗,那隻狗一來就在地毯上留下一小塊乾燥的大便,他二話不說就撿起狗大便放進口袋。事後我母親說,這是她見過最有禮貌的行為。不過來客並非只限於法國人,還有英國人和美國人,以及任何我父母認識、又剛好出現的人。
回憶過往,我只有一樁憾事,那就是當時的我太年輕,小了兩到三歲。我認為自己已經很早熟了,但這些名人我只認得他們的名字。我會喊住考克多,幫他調一杯不甜的馬丁尼,但他的作品我一個字都沒讀過。要是一九四四年我已經十八歲而不是十五歲,我就能知道也能學到更多事。不過這也沒什麼好抱怨的,能在大使館裡就已經夠幸運了。
父親刻意將他的正式巡視行程安排在我的假日,因此我們能造訪這個國家的各個角落。一九四五年復活節,就在戰爭即將結束之際,我們驅車往南,沿路偶爾會經過一輛焦黑生鏽的坦克車。我永遠無法忘記第一次見到地中海時,那不同於英倫海峽的湛藍。一九四六年,我和學校的一個朋友從亞維儂,騎腳踏車橫越普羅旺斯到尼斯,但由於熱浪、戰後坑坑疤疤的道路以及老是被刺破的輪胎(幸好我們有合成橡膠腳踏車內胎),我們的旅程只完成了一部分。
一九四七年,在等著加入海軍時,我在史特拉斯堡某個很好相處的亞爾薩斯家庭裡住了半年,在大學以德語和俄語上課(從十二歲我就開始藉由「靈格風」課程學習這兩種語言)。我非常享受在史特拉斯堡的時光,只除了一件令人尷尬到極點的事:我的房東老是在她先生預定回家的五分鐘前,試圖奪去我的童貞(現在回想起來,她大概每晚在床上跟她先生全盤托出,好讓兩人哈哈大笑一番)。那年年底我們離開大使館,定居在香提伊(Chantilly)郊外湖邊一棟美麗的房子裡。這時法國已經成為我永久也是唯一的家,我愈來愈愛她。
正是在大使館裡,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戴高樂將軍。一九四七年六月六日,也就是諾曼地登陸的三週年紀念,法國在當時盟軍登陸的其中一座海灘舉行紀念儀式,之後在旁邊的旅館裡還有盛大的自助餐午宴。出於某種原因,我無法和我父母一起在前晚抵達,因此當天早上我自己開車前往。當時我十七歲,那是我第一次獨自開長途車。我希望能趕上午宴,但我卻在諾曼地沒有路標的狹窄道路上徹底迷路,午餐即將結束時才到達。我父親將我介紹給將軍,令我驚訝的是,身高將近兩百公分的他竟然站起來和我打招呼。我受寵若驚,但在食物似乎全被收走的同時也感到飢腸轆轆。桌上只剩下一個盤子,那就是戴高樂將軍的盤子,上面放著一大塊顯然還沒動過的蘋果派;我目不轉睛盯著它。「你覺得將軍會吃那個派嗎?」我問我母親。「我怎麼知道?」她回答,「你最好自己問他。」我在飢餓與害羞之間做了一番短暫的拉扯,最後飢餓獲勝,我走到將軍的桌子前面。「不好意思,將軍,」我說,「你要吃那塊蘋果派嗎?」他立刻把盤子推過來,同時帶著一抹微笑向我道歉,說他把菸灰都彈在派上了。發現自己可能太得寸進尺,於是我說,能吃將軍的菸灰也是我的榮幸──這句話顯然很成功。這就是我和這位偉人之間唯一的對話。和他與我父親或邱吉爾之間的談話不同,這段交談簡直再親切不過了。
這本《法蘭西全史》的對象並非專業歷史學家,他們會發現書中每一件都是他們已知的事。本書是為一般讀者所寫,也就是法國人非常動人的稱之為「有著一般感官知覺」(l’homme moyen sensual)的普通人,而且寫作動機是出於:相信說英語的一般男女對法國史知識相當有限。我們或許知道那麼點拿破崙、聖女貞德或路易十四世,但對大多數英國人來說,也就僅止於此。在我自己讀過的三所學校裡,老師只教我們英國人打的勝仗,像是克雷西、普瓦捷、阿金庫爾和滑鐵盧等戰役。
因此在本書中,我試圖填滿其間的空白。我想談談落入可憎的腓力四世手中之後,聖殿騎士團的命運是如何悲慘;腓力四世的女兒在奈斯勒塔裡的遭遇;出色的龐巴度夫人和惡劣的曼特儂夫人;以及現在幾乎被人遺忘,但或許是法國有史以來最好的國王路易―腓力一世,而以上這些只不過是序幕。第一章會迅速介紹基礎背景,帶領讀者從高盧人、凱撒大帝,一路來到查理大帝,範圍涵蓋八世紀之久。不過當我們繼續往下讀,速度當然也漸趨緩慢。第二十一章只處理二次大戰其間前後五年發生的事,本書就在此告一段落。所有歷史書必須要有一個清楚界定的終點,如果沒有,就會變成沒完沒了地談論時事。我或許也可以提到越南和阿爾及利亞,但實在沒什麼誘因讓我把歐盟也納入本書。一九四五年是舊時代的結束,也是新時代的開始。要談論法國第四與第五共和,必須另覓一位編年史家(他們的確也找到好幾位)。
作者在前言或序裡通常可以提到私事,但一般而言這不應該出現在正文裡。我必須承認在最後兩章裡我偶爾打破了這個規則。一九三七年,我的父親達夫.庫伯(Duff Cooper)被指派為第一海軍大臣,該頭銜是英國賦予海軍部長的殊榮,之後為抗議首相張伯倫與希特勒在慕尼黑簽訂協議,他辭去第一海軍大臣的職務。一九四○年,他加入邱吉爾的內閣,擔任資訊部部長,他先在遠東待了一陣子,之後回到倫敦從事情報工作。一九四四年一月,他在二戰期間戴高樂將軍於阿爾及爾成立的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裡,擔任英國代表。八月盟軍解放巴黎,他旋即擔任戰後英國第一任法國大使。由於擔任以上這些職位,他無論如何都會出現在我們的故事中,我很難遺漏他的事蹟。
我也在其他方面違反了歷史書籍的原則,尤其是一致性,我向來不喜愛這項美德。在接下來的內容中,讀者會讀到公爵(dukes / ducs)、伯爵(counts / comtes)、約翰(Johns / Jeans)與亨利(Henrys / Henris)等同一個字的不同說法。我對字的選擇偶爾只是搞混了,但更常是因為那個字的聲音很和諧──我很明白,對我而言順耳的字,對其他人來說可能難聽得離譜。若果真如此,我只能說聲抱歉了。
我知道我之前說過這件事,但我幾乎可以肯定這將是我的最後一本書。我喜愛寫作的每一刻,並將其視為,我對這輝煌國家多年來給予我的幸福,所獻上的感謝之意。
──約翰.朱利葉斯.諾里奇,倫敦,二○一八年三月
「終其一生,我對法國都抱持著某種概念。」戴高樂將軍回憶錄的開場白,已經成為世界著名的佳句。而我,也總是以諸多方式,懷抱著如是的概念。我猜想,這是源自一九三六年九月,將滿七歲的我初次造訪法國的經驗。當時,我的母親帶我去艾克斯萊班(Aix-les-Bains),主要目的是斷絕我對那位英國奶媽的依賴。一切彷彿就在昨日,我依舊能感受到越過英倫海峽的興奮之情;穿著藍綠色夾克的成群腳夫,身上散發出令人窒息的大蒜味;來自四面八方嘈雜的法語(拜五歲開始每星期兩次的法語課之賜,這些法語我已經聽懂不少);廣大無邊的諾曼地,放眼望...
目錄
序言
地圖
法蘭西歷代君王列表
第一章 極度黑暗
第二章 自取滅亡
第三章 王者之劍的贈禮
第四章 致命的塔
第五章 被俘虜的國王
第六章 意料中的結局
第七章 無所不能的蜘蛛
第八章 陽光普照的溫暖大地
第九章 以他一貫的浮誇
第十章 「值得一場彌撒」
第十一章 「朕即國家」
第十二章 大難臨頭
第十三章 「我真是你們的王」
第十四章 「不可軟弱!」
第十五章 是祝福或是詛咒?
第十六章 完美的妥協
第十七章 「國家榮耀的象徵」
第十八章 沒有謎題的獅身人面像
第十九章 最後的示威
第二十章 「我控訴!」
第二十一章 洛林的十字架
結語
謝詞
延伸閱讀
序言
地圖
法蘭西歷代君王列表
第一章 極度黑暗
第二章 自取滅亡
第三章 王者之劍的贈禮
第四章 致命的塔
第五章 被俘虜的國王
第六章 意料中的結局
第七章 無所不能的蜘蛛
第八章 陽光普照的溫暖大地
第九章 以他一貫的浮誇
第十章 「值得一場彌撒」
第十一章 「朕即國家」
第十二章 大難臨頭
第十三章 「我真是你們的王」
第十四章 「不可軟弱!」
第十五章 是祝福或是詛咒?
第十六章 完美的妥協
第十七章 「國家榮耀的象徵」
第十八章 沒有謎題的獅身人面像
第十九章 最後的示威
第二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