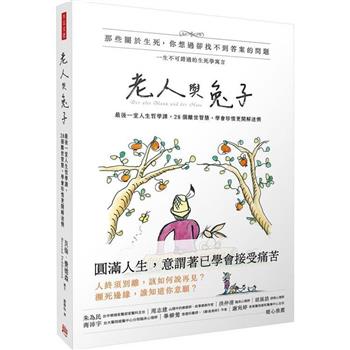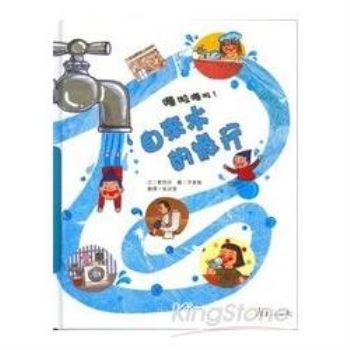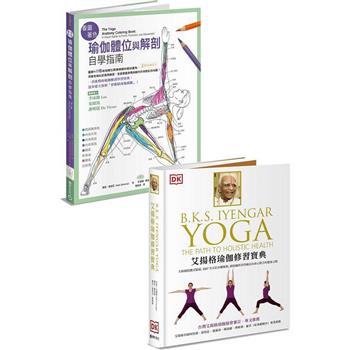第一章 母獅
聖潔寓存於美麗的記憶:葉子有如失重的青銅,歲月雕蝕,落入巴黎羅丹[ 羅丹(Augeuste Rodin):一八四○~一九一七,法國著名雕塑家。]雕刻花園的林木之間。對於羅丹,人體是自然終極的表現,裸體絕非墮落,因為它承受了天地萬物的榮耀和痛楚。我記得在這位藝術家的宅邸裡有一些奈內.馬利雅.里爾克[ 奈內.馬利雅.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一八七五~一九二六,奧地利著名德語詩人,曾當過羅丹的秘書。]所稱,雖然缺了手臂卻是完整的裸體軀幹雕像,以及一座腹部下垂,胸部鬆弛的女性美麗雕像。羅丹很清楚,四肢和青春之於美麗是不必要的。
羅丹的〈老婦人〉是名副其實的旅行女神。她的身體是受盡一生折磨的殘留,而她往下凝視的神情則暗示著記憶。除了回響,她的知識和經驗已不再有實質的目的。是的,這座雕像呈現出一名交際花,遠勝過她的罪愆:旅程是我們真正遇到自我。哲學家柏格森[ 柏格森(Henri Bergson):一八五九~一九四一,法國哲學家。]說,我們記得我們必須記得的,以便忍受。這是何以許多司空見慣的事已被遺忘,但旅行中的事卻從來不會遺忘。
*
「市井之徒無法洞悉賽蓮[ 賽蓮(Sirens):半人半鳥的女海妖,以歌聲吸引水手並使船隻遇難。]。」卡山札基斯[ 卡山札基斯(Nikos Kazantzakis):一八八三~一九五七,希臘作家,最著名的作品是小說《希臘左巴》(Vios kai politia tou Alexi Zormpa)。]如此認為,「他們聽不到空中的歌聲。瞎了,聾了,彎曲著身體,用力地由泥地上拉起槳。船長們更選擇性地聆聽著他們自己心中的賽蓮……莊嚴地為她揮霍生命。」
卡山札基斯的賽蓮是一個「殘酷的聲音——母獅」。她是他所有旅程中的伴侶。她「以爪子深掘入我腦中,我們映照出我們看到的,以及將要看到的。」勞勃.格雷夫斯[ 勞勃.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一八九五~一九八五,英國詩人。
]稱這頭獅是「白色女神」,可以用「母狼、母獅、美人魚或令人憎惡的老太婆」的樣子出現。格雷夫斯說,對她「精確的描寫,是對所有作家洞察力的試鍊。」
這個女神的肉體之美在她的雙眼。她的誘惑力是她的精神生命。因為那是在比較和隱喻每一個將意念神聖化的新物體和景色之後,所產生的渴望。
*
葉子落在雕像上,是我過去十四年來對於秋天僅餘的記憶。我坐上火車南下到馬賽[ 馬賽(Marseille):亦做Marseilles,法國南部海港城市,為普羅旺斯省首府,是法國第二大城,也是地中海第一大港。
]的那個夜晚,毫不猶豫地將羅丹的花園交給過去。一如所有的日記作者,我在啟程時寫下心中所感,即使那個地方的氛圍仍然霸占我的思緒。
此時,我在追憶之中旅行:僅僅挖掘出最有用的片段。
那時,我剛大學畢業,在佛蒙特州一家小報社工作。一九七五年夏天,我在每晚的新聞上看到了黎巴嫩的內戰消息。懷著成為海外通訊記者的希望,我在新聞通訊社、電視網和其他數家大型的大都會報社尋找工作。淺短的記者資歷,加上名不見經傳大學的文憑,我的履歷表隨即遭到遺忘。沒有人聘用我。
我惶惶難安。我那以駕駛卡車為業的父親,在他二十多歲時,已經乘火車走遍美國,在美國本土四十八州中,遊走了四十三州,以探聽賽馬情報賭馬維生。大贏時就住進一流的飯店,手上拿著大雪茄;但二十四小時後,他的生活卻可能像一九三○年代許多遊民一樣。他告訴我許多他在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的越軌行徑,以及當時一派平靜的田園生活和純真國民的影像;在那樣的環境裡,他當時的哄騙,也相對地沒有嚴重的殺傷力,人們甚至在你潦倒不堪時請你吃飯。
我父親記得的最後一次旅行是在一九四二年。當時,他剛在路易斯安納的波克堡(Fort Polk)完成基本訓練,正搭乘北上的軍隊列車,準備派遣到歐洲。在伊利諾的開羅(Cairo)附近一處鐵路聯軌站,西沉的太陽在大草原上灑下燦爛的色彩。其他的列車由不同的軌道匯聚到同一線上,載著士兵們前往東岸船隻泊候的定點。在廣闊的弧光那頭,他只見長長的列車以曲線迤邐拖行,背後則是被太陽染紅,平坦而無垠的風景。每個車窗上都有向外觀望的士兵。
我有一位旅伴同行。雖然我們分享了旅途得以更具魅力的熟稔親近,在另一架飛機上,我們仍是兩個各自一頁頁寫著自己的筆記本的孤獨生命。接下去的片刻,記錄著沉寂的航行,「我」這個代名詞,比「我們」來得適切。
有如走過博物館甬道般,我漫遊過不同的景色,探求一個我在大學時期從未找到的工作。我現在比過去第一次見到它們還了解這些地方,我的記憶無法不同時增強和失真。
*
里爾克曾寫及,羅浮宮內的希臘和羅馬藝廊「顯現給羅丹一個南方穹蒼下的古老世界,一座海洋和遠古文明巨大石頭紀念碑的光燦視界」。羅丹並非完全模仿希臘和羅馬風格。他是兩個基督文化千禧年的繼承者。他的雕像呈現的氣勢來自由原罪中衍生的混亂和不安。因此,它們缺乏古典雕刻中常見的理想化沉靜。我一直記得它們,因為它們連結了我之後在突尼西亞、西西里所見的古代遺址及中世紀教堂;而我去這些地方則是因為我讀過的書籍吸引了我。
借用卡山札基斯的話,那些和母獅「浪費他們生命」的人,人生大事來自偶然遇到的書籍,而非人們。有些書籍展現了新世界,有些則印證我們的經驗。書籍能讓你迷途,能毀滅你,也能將你自環境的狹隘之中釋放出來。有些書籍重要到令人清晰地記得找到這本書和閱讀這本書時的情境。
書籍決絕在偶然之間改變你的生命;當然也無關設計。人們找到這些書,就像撿破爛的人在垃圾堆裡找到有用的東西,或像獵人湊巧遇到獵物。這樣的冒險精神需要警覺,哲學家華特.班雅明[ 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一八九二~一九四○,猶太裔德國哲學家。]曾說:一個人得學習在都市中迷途,才能找到迷途的重要意義。
某個十月一個陽光強烈、陰影斑駁的日子,我鬱鬱地忽視了樹葉的炫麗顏色,不經意的走入新罕布什爾州漢諾瓦(Hanover)一家書店。在後面的書架上,我找到了福樓拜[ 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一八二一~一八八○,法國小說家,作品有《包法利夫人》等。]的《薩朗波》(Salammbô)和札拉法[ 札拉法(Michel Zeraffa):一九一八~一九八三,法國歷史學家。]的《突尼西亞》(Tunisia);靠商店前段一張桌子上則放了李維[ 李維(Titius Livy):約西元前五九~西元一七,羅馬共和國初期和中期歷史學家,所著之《羅馬史》對後代史學寫作有巨大影響。
]的《漢尼拔戰爭》(The War with Hannibal)。於是,我見到了文明與王朝:努米底亞[ 努米底亞(Numidia):古羅馬人對自非洲北部至迦太基西部和南部的這一地區稱為努米底亞,大體相當於現在北非的阿爾及利亞。]、羅馬、迦太基;汪爾達和拜占庭;艾格萊卜王朝、濟里德王朝和哈夫西德王朝。還有君主們、將軍、聖者們、假先知們和智者:朱古達[ 朱古達(Jugurtha):約西元前一六○~西元前一○四,努米底亞最後一任國王(西元前一一八~西元前一○五)。由於羅馬難以打敗他,遂使馬略得到施展的機會,對羅馬軍隊進行重大改革。這場戰爭以朱古達向馬略的代表蘇拉投降而告結束。]、大西庇阿[ 大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西元前二三六~西元前一八三,古羅馬共和國貴族。]、漢尼拔[ 漢尼拔(Hannibal):約西元前二四七~西元前一八三,迦太基名將。]、蓋塞里克[ 蓋塞里克(Genseric):約三九○~四七七,汪爾達君主。]、聖奧古斯汀[ 聖奧古斯汀(St. Augustine):三五四~四三○,羅馬末期的北非主教,是早期教會史上偉大的神學家、哲學家、文學家,對天主教文化的影響僅次於聖保羅。一生著作三百多種,以《懺悔錄》最為聞名。]、聖陶納多[ 聖陶納多(Donatus):活躍於四世紀,著名的文法家,也是羅馬的修辭家,其學生之一為Eusebius Hieronymus,即後來的聖傑若米(St. Jerome)。]、查士丁尼[ 查士丁尼(Justinian):五二六~五六五,拜占庭帝國君主。]、伊本.赫勒敦[ 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一三三二~一四○六,阿拉伯的歷史哲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他是亞里斯多德以後、馬基維利之前這一時期中社會科學方面最著名的人物。]。
在《薩朗波》中,福樓拜描寫了迦太基人與其於西元前二四一年叛變的利比亞傭兵作戰。他對於一個有組織的國家抵抗一群無政府主義群眾的聳動描繪,深印我心。在福樓拜筆下,突尼西亞成了惡魔與殘破、血腥與淫穢之地。他描寫這些傭兵以硃砂塗身,「看來有如珊瑚雕像」;士兵們在燒焦的猴屍邊「吵雜地」鼾聲大作;獅子在路邊被釘到十字架上;野人們將牛油和肉桂塗在聖像臉上慶祝勝利;兒童則被犧牲,以取悅異教之神巴爾[ 巴爾(Baal):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主神。
]。迦太基女祭司薩朗波在利比亞傭兵的營帳找到傭兵首領時,全身散發出「蜂蜜、胡椒、焚香和玫瑰」的味道,而附近一頭穿過帆布篷破洞的大象,卻散發著惡臭。福樓拜描述屠殺男童之前,群眾突然遭逢暴風雨的效果,呈現了對於男童犧牲獻祭少見的感知。
李維撰寫羅馬與迦太基之戰,晚於福樓拜的《薩朗波》二十年。雖然許多戰爭都發生在西西里島,但戰爭的高潮卻是在突尼西亞。控制著西西里海峽(Sicilian Channel)的突尼西亞,守衛整個地中海西部長達一千年。有個秋天,我凝視著突尼西亞和西西里地圖:這兩個吸引人的地方,有沙漠,有杏樹覆蓋的山丘和廢墟。兩個地區性子暴烈的居民已經以同等的熱切信了基督教、多納圖斯異教[ 多納圖斯異教(Donatist heresy):為非洲基督教分裂派,擁護四世紀時與迦太基主教爭奪主教職位的多納圖斯,故得其名。此教派在四、五世紀興盛於非洲,到七、八世紀開始沒落。]和伊斯蘭教。他們的領土則由地中海的狹窄處,各自朝東和西而去;並且就像我後來明白的,各有自己的歷史和文化模式。
我懷著遊遍地中海地區的目標,搭機到法國,由此乘船到突尼西亞。延伸在我前方的冷冬彷彿生生不息。在總是有時間可以彌補錯誤,人們對於時間感覺不到責任壓力時,又何能在累積足夠的行動證明之前,重得無盡潛在可能的觀念?
*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個冰冷的午夜,我在巴黎里昂車站搭上前往馬賽的火車。黎明時,我在亞爾[ 亞爾(Arles):法國南部城市。
]附近醒來,迎面而來的是刺人的鹹味空氣和擠壓過的葡萄色柔和天空下的橄欖樹。平整的起伏田園呈現出植物的深綠色,清楚地被楊樹間隔,融入混亂的黃棕色山和陳舊黏土築成的下陷屋頂之中。北歐已然消失。我身上有一千元的旅行支票,但沒有回程票。
我離開了佛蒙特州的報社,並且不再任職。和許多我過去多年來遇到的自由記者一樣,我毫不喜歡做為大型媒體海外特派員的社會和專業身分,或豐厚的出差預算。我自己閱讀和研習,並把文章賣給報社,這讓我有剛好足夠的錢可以住在青年旅館和廉價的旅館裡,並且持續旅行。改變是我被迫服膺的信條。沒有錢打越洋電話,又是在傳真機和快遞發明之前,我只能依賴各地的郵局;並在那裡領到接受或拒絕的信件,或是支票與被退的文章。我的決定就看當下的偶然事件。日子真是無限的自由。
走出馬賽聖查爾斯車站的人群和喧鬧,我蹣跚地直接走入市區;在車站狹長的大理石階梯,看著筆直而擁擠的大荒直入舊港區(Old Port)。在低價位的百貨公司和厚玻璃板的報攤之間,戴著滑雪帽的黑人們購買上面標示「符合清真」的小吃——這是我第一次聞到地中海的垃圾及冷冽的氣息。風在厚重的雲層下吹掠。我覺得這裡和巴黎一樣寒冷,並聽到有如義大利語一樣,斷音似的阿拉伯語和法語交談。卡車正在卸下裝了魚類和農產品的板條箱。我走入一家陰暗的酒吧喝咖啡。室內的桌子全都堆疊在後頭。新藝術派(art nouveau)的帶狀橫飾為破碎和滿是塵埃的鏡子帶來一些光彩。角落裡有一彈珠遊戲檯,幾個男人在那兒閒聊,並圈選樂透彩券。我找到了一家一夜只要四塊錢的旅館;褪了色的黃色房間裡有潮濕的地板,加上外露的水管。旅館位於一條有許多小披薩店的街上,街上的阿拉伯男人則賣著金屬攤架上的廉價手錶和古龍水。
巴黎是一個擁簇著鍍金邊框的鏡子、刻意安排的店面和大量的博物館,某些街道還鋪圓石。馬賽則像粗厲的風,剝除了禮俗和傳統;一個充滿不正當營生的阿拉伯勞工移民的真空吸塵器。馬賽粗糙的邊緣(edge)優勢是它的誘惑力。它「像一名美麗卻不愛惜自己的美麗女郎在陽光下滲出汗水」,莫泊桑[ 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一八五○~一八九三,法國自然主義小說家,被譽為「短篇小說之王」,著名短篇作品有〈脂肪球〉等。]在十九世紀寫道。
馬賽是惡劣的侍者、塑膠椅、膠質桌巾,以及蒸鯡魚和鰻魚味道的混合體。這裡的生活是戶外的;人們對於室內和細節較少在意。來自小亞細亞海岸港市霍扎[ 霍扎(Phocaea):現今的土耳其愛琴海北部,古代為奧尼亞聯邦的一部分。]的希臘水手因為被受到半圓型劇場般山丘保護的深水港所吸引,在西元前六百年建立了馬賽。它的舊名為「馬薩里亞」(Massalia),在腓尼基文中意謂「新拓居地」,這也顯示最早來此的可能是腓尼基人。希臘人的「馬薩里亞」威脅到迦太基人的地區影響力。孟德斯鳩[ 孟德斯鳩(Montesquieu):一六八九~一七五五,出生於酒鄉波爾多附近的布列德(Le Brede),為法國社會學思想的主要先驅之一。]曾撰寫「迦太基人與馬賽人的漁場大戰」。希臘人雖然身陷高盧[ 高盧(Gaul):為現今法國的主體,西元前六世紀為羅馬凱撒大帝征服。]的羅馬殖民地之中,卻從來沒有和羅馬結盟,共擊迦太基。孟德斯鳩寫道:
羅馬人在西班牙向迦太基人展開的戰爭,對於扮演貨棧角色的馬賽卻是財富的來源。迦太基和科林斯的廢墟為馬賽人帶來更多的財富;而且,要不是在內戰中,人們得盲目地選擇一方,馬賽人在對於其商業毫不感到妒嫉的羅馬保護下,將會更加快活。
馬賽讓我了解到地中海的歷史是權力優先,美麗次之。羅浮宮內的精美紀念物是統治了蓬勃的商業和軍事戰略的富有王朝,能夠創造偉大藝術之前的物品。除了法國學者布勞岱爾[ 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一九○二~一九八五,法國著名歷史學家。]稱之為「羅馬夷平霸權」(在羅馬於西元一四六年殲滅迦太基之後),遍及地中海地區的古風和中世紀成為無法改變的權力平衡檔案。貧瘠的沙質土壤使得此區的人民不得不外移征討四方,然而,不論迦太基人、希臘人、汪達爾人、拜占庭人、威尼斯人或土耳其人,都無法控制整個海洋。我眼前這個城市是一段紛擾歷史的複製品:來自北非的阿拉伯人、義大利人、西班牙人、希臘人、科西嘉人和其他的移民,皆流入混亂的街道,多樣而混亂的人種和貿易關係,使得馬賽成為最有地中海風味的城市。
依照在古代的霍扎風潮,不但它自己的創建城市被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圖斯(Tacitus)形容為粗糙不堪,馬賽也被定位為商業本位,公共紀念物極少。那兒的歷史遺址皆反映了居民對於經濟存活的需求。兩座十九世紀的教堂風格沉重,陰鬱的風華散發出面對翌日的力量。瑪卓大教堂(La Major,即Sainte-Marie-Majeure)仿自拜占庭建築。它坐落於港口,靠近獻給月神戴安娜的異教神殿。守護聖母院(Nôtre Dame de la Garde)則建於俯瞰市區的凸岩上,其上鍍金的聖母雕像,有如一座巨大的金身護身符,由各個角度都看得見。
主要大道大麻路[ 大麻路(La Canebière):一說名稱源自大麻(canèbe),過去此地一度有座麻繩工廠;中世紀時即已在舊港邊的沼澤上種植大麻。]兩側林立著廉價的行李箱和玩具店。街道的名稱來自拉丁字「大麻」(cannabis),大約指附近在過去曾有一座繩索製造廠。我沿著大街前往二千五百多年前由霍扎希臘水手建立的舊港——這座廣大的長方型港口波動著油膩的灰色海水,邊上則是設有百葉窗的陳舊公寓建築。雨滴打在我身上,但我卻沒有雨傘。雨急急落下,快到令海水看來像覆上一層粗糙的玻璃。在滑溜的海濱空地上,人們穿著濕漉漉的工作服,在風中拍打著發出巨響的帆布下排著隊,等待冰凍成厚塊的鱸魚和小山似的生蠔。
我感到夜晚睡眠不足的痛苦寒冷,也不想回到潮濕又沒有暖氣的旅館房間;不但我的衣服在那兒無法晾乾,我在那兒也沒有什麼衣服可以換穿。但雨一停後,陽光自雲層中射出,港口的海水也跟著平緩下來。一時之間魚和海洋的腥味占據了我,縮小了和其他港口之間的距離,透露出各種可能性。我走向護衛著外海入口的中世紀橋頭堡時,衣服也開始乾了。
一名包著頭巾的老婦人趁著雨停,正在屋頂上晾衣物。一群戴著低頂圓帽的老先生聚在巷子裡玩法式滾球遊戲。在這些家居的一般生活中,我心有共鳴而感到我也是這個城市的一分子。見到如此一座不合時宜的城市,好像見到一名在家的婦女戴著浴帽,臉上卻抹了濃粧;我同時感到親切和失望,並從中感受到活力。「不同於夏日的停頓,冬天賜與榮耀的公民身分。」英國一位地中海權威派翠克.弗莫[ 派翠克.弗莫(Patrick Leigh Fermor):一九一五~二○一一,英國作家、學者和軍人。
]如此寫道。
太陽再度露臉,我覺得自己度過第一個危機。我沒有遭到搶劫,也沒有遺失護照。我只有經歷過所有旅行者都有過、短暫發作的寂寞感。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地中海的冬天:從突尼西亞、西西里到希臘,探索神秘水域最古老的文明與歷史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地中海的冬天:從突尼西亞、西西里到希臘,探索神秘水域最古老的文明與歷史
開啟一段與過往歷史的對話
地中海的歷史,是權力所寫就,而非美麗。
「年代看似久遠,她的遺跡卻讓人感覺靠近。」
突尼西亞控制著西西里海峽,守衛整個地中海樞紐長達一千年。然而,不論是迦太基人、希臘人、汪達爾人、拜占庭人、威尼斯人或土耳其人,都無法控制整個海洋;西西里的地理位置正說明了她,介於非洲迦太基人和歐洲希臘人的角力爭奪。希臘羅馬的文化和軍事勢力遠播,從這片水域的建築遺跡中清楚可見。其歷史恩怨的糾葛呼喚著卡普蘭一處處探尋與深究。
這趟旅程從羅丹在巴黎的雕像公園開始,行經馬賽的粗曠街道,直抵當時正為2004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大張旗鼓進行籌備的希臘雅典畫下旅途終點。卡普蘭隨著聖奧古斯汀和伊本.赫勒敦的足跡,從突尼斯的清真寺,到迦太基、羅馬和拜占庭的軍事要塞土耳其碉堡;或置身塞吉斯塔的希臘神殿中,恍如親睹雅典人入侵西西里的現場……
從一處遺跡到另一處遺跡,任由旅程帶領他進入歷史洪流裡的不同主場:柏柏人對迦太基的威脅;羅馬軍隊追討軍閥朱古達;拜占庭藝術的遺產巡禮;激發義大利文藝復興的中古世紀希臘哲學家吉密斯托斯;尋訪羅丹和克羅埃西亞的雕塑家伊凡.美斯特羅維克之間的關聯等等。這部地中海現場行旅,不僅僅是作者卡普蘭個人的回憶與溯往,同時深刻探索這片神秘水域最古老的文明與繁麗糾葛的歷史軌跡。
作者簡介:
羅柏.D.卡普蘭(Robert D. Kaplan )
被《Foreign Policy》雜誌譽為全球百大思想家的卡普蘭是美國知名記者、《大西洋月刊》資深主筆、地理戰略學者。
也是旅行名家,旅行足跡遍及七十多個國家,發表過四部與旅行有關的作品,包括一九九三年被《紐約時報書評》評選為該年度好書的《巴爾幹鬼魂:一段穿越歷史的旅程》(Balkan Ghoast:A Journey through History) 。他的另一部作品《阿拉伯專家》(The Arabists)同時被《紐約時報》選評為「值得注意之書」。
在一九八O年代與一九九O年初期的文章裡,他是第一位對巴爾幹即將來臨的巨變發出警示的美國作家。多年來的行腳與關注的焦點大都集中於戰火頻仍、種族分裂的第三世界。他尤其擅長運用旅行文學的手法處理新聞議題。
卡普蘭著作橫跨文化、政治、外交與旅行文學,作品有:《世界的盡頭》、《西進的帝國》、《歐洲暗影》、《南中國海》等書。
相關著作:《世界的盡頭:從西非到近東,從伊朗到柬埔寨,一場種族與文化衝突的見證之旅》
譯者簡介:
鄭明華
一九五八年生,輔仁大學英文系畢業。曾任職華視〈海棠風情〉節目企畫、採訪及總撰稿,以及《大地地理》雜誌資深撰述、總編輯。
著作有小說《私奔》。譯作:《威尼斯》、《西班牙》、《尋找聖靈戰士》、《再會,西貢》等。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母獅
聖潔寓存於美麗的記憶:葉子有如失重的青銅,歲月雕蝕,落入巴黎羅丹[ 羅丹(Augeuste Rodin):一八四○~一九一七,法國著名雕塑家。]雕刻花園的林木之間。對於羅丹,人體是自然終極的表現,裸體絕非墮落,因為它承受了天地萬物的榮耀和痛楚。我記得在這位藝術家的宅邸裡有一些奈內.馬利雅.里爾克[ 奈內.馬利雅.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一八七五~一九二六,奧地利著名德語詩人,曾當過羅丹的秘書。]所稱,雖然缺了手臂卻是完整的裸體軀幹雕像,以及一座腹部下垂,胸部鬆弛的女性美麗雕像。羅丹很清楚,四肢和青...
聖潔寓存於美麗的記憶:葉子有如失重的青銅,歲月雕蝕,落入巴黎羅丹[ 羅丹(Augeuste Rodin):一八四○~一九一七,法國著名雕塑家。]雕刻花園的林木之間。對於羅丹,人體是自然終極的表現,裸體絕非墮落,因為它承受了天地萬物的榮耀和痛楚。我記得在這位藝術家的宅邸裡有一些奈內.馬利雅.里爾克[ 奈內.馬利雅.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一八七五~一九二六,奧地利著名德語詩人,曾當過羅丹的秘書。]所稱,雖然缺了手臂卻是完整的裸體軀幹雕像,以及一座腹部下垂,胸部鬆弛的女性美麗雕像。羅丹很清楚,四肢和青...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章 母獅
第二章 白袍神父博物館
第三章 朱谷達之桌
第四章 保羅‧克利的伊斯蘭抽象概念
第五章 灰色之美
第六章 無言的神殿
第七章 赤土城市
第八章 西西里之旅
第九章 哈得良莊園
第十章 戴克里先皇宮
第十一章 度布洛文尼克崛起
第十二章 發出蠟燭爆裂聲的神奇小屋
第十三章 文學的拜占庭
第十四章 莫里亞和新柏拉圖派哲學
第十五章 地中海最後的帕夏
致謝
第二章 白袍神父博物館
第三章 朱谷達之桌
第四章 保羅‧克利的伊斯蘭抽象概念
第五章 灰色之美
第六章 無言的神殿
第七章 赤土城市
第八章 西西里之旅
第九章 哈得良莊園
第十章 戴克里先皇宮
第十一章 度布洛文尼克崛起
第十二章 發出蠟燭爆裂聲的神奇小屋
第十三章 文學的拜占庭
第十四章 莫里亞和新柏拉圖派哲學
第十五章 地中海最後的帕夏
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