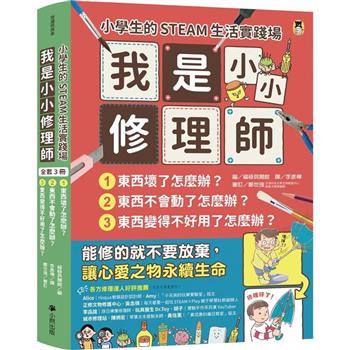圖書名稱:瑪瑪的最後擁抱
探知動物的情緒時,我們將會發現:
他們要訴說的心事,遠比我們所知道的還更多!
★ 榮獲2019筆會╱E•O•威爾遜 文學科學寫作獎
★ 《時代》雜誌世界最具影響力百大人物
★《探索》雜誌史上最偉大的47位科學思想家
這一切,要從一隻黑猩猩——瑪瑪過世前的擁抱開始說起。
瑪瑪是荷蘭伯格斯動物園黑猩猩群中的雌性首領,她和生物學家范霍夫非常親近。瑪瑪將死之前,范霍夫做了一件不尋常之事;黑猩猩力大無窮,若人類直接接觸黑猩猩,可能會受傷,但他前往瑪瑪晚上休息的籠子,給她人生最後一次擁抱。這個道別的過程拍攝了下來並且馬上瘋傳。這最後一次會面,感動了無數人。瑪瑪以滿臉的笑容迎接范霍夫,並且輕拍他的脖子好要他安心。人類一直以來都認為只有自己會用豐富的表情與肢體語言表達完整的情緒;事實上,所有靈長類動物也是。除了常見的地位競爭,靈長類也會記恨、也在意公平性、更會顧慮團體的和諧進行和解。如果說靈長類跟我們一樣,不如說人類才是靈長類的一員。
最重要的是, 動物不是只依賴弱肉強食而生存,他們也有完整情緒智能。
黑猩猩看到同伴溺水時,會奮不顧身解救對方,即便自己不會游泳。
獼猴偷走人類的手機,但若用幾粒花生米想換回來,他們才不屑。
當狗做錯事的時候,會垂下眼睛跟耳朵表示抱歉。
貓打完架之後,贏家往往會刻意在輸家看得到的地方背躺打滾。
魚如果心情不好,就會躲在暗處不想浮出水面。
透過瑪瑪的最後擁抱,法蘭斯.德瓦爾讓我們打開心胸與視野,讓我們知道人類和動物在許多方面其實是共通的,人類不該看動物為機械式、唯利是圖的生物體,而是隨時與群體跟世界不斷互動、交互感受,讓人類對於所處的生命世界,有更多欣賞與尊重。
作者簡介
法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
荷蘭裔美國人,烏特勒支大學生物學博士,全球知名動物行為學家與靈長類動物學家,美國國家科學院、荷蘭皇家藝術暨科學院院士,埃默里大學心理學系坎德勒講座教授、烏特勒支大學特聘教授、亞特蘭大葉克斯國家靈長類研究中心的生存環節中心(Living Links Center)主任。
德瓦爾常於《科學》(Science)、《自然》(Nature)與《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等重要期刊發表學術研究與寫給大眾閱讀的科普文章,第一本暢銷書《黑猩猩政治學》(Chimpanzee Politics: Power and Sex Among Apes)翻譯成20種語言出版,使他成為全世界最耀眼的生物學家之一,《靈長類的和解》(Peacemaking among Primates)則於1989年獲洛杉磯時報圖書獎肯定, 2007年入選《時代》(Time)雜誌世界最具影響力百大人物,2011年入圍《探索》(Discover)雜誌史上最偉大的47位科學思想家。
譯者簡介
鄧子衿
科學編輯與譯者,翻譯生命科學、與食物相關的書籍。
近期翻譯作品有:《我愛讀科學的故事》、《雜食者的兩難》、《廚藝之鑰》、《醫學之書》、《章魚的內心世界》、《美的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