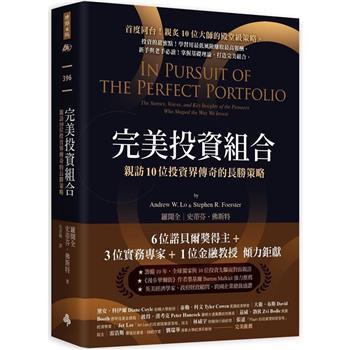圖書名稱:哈布斯堡帝國
哈布斯堡家族,歐洲歷史上最顯赫、統治領域最廣的王室
哈布斯堡是如何在一片充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中歐建立綿延數百年的統一帝國?
她又該如何面對工業革命、啟蒙思潮、法國大革命等時代變局?
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每日電訊報、文學評論 爭相報導
Amazon 4.1分、Goodreads 3.8分、豆瓣讀書7.9分 讀者好評
【內容簡介】
哈布斯堡家族,歐洲歷史上最顯赫、統治領域最廣的王室,曾統治過神聖羅馬帝國、奧地利帝國、西班牙帝國等諸多國家,稱霸歐洲達六百年。本書將講述從十八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奧地利的哈布斯堡帝國是如何在一片充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中歐,建立綿延數百年的統一帝國?帝國又該如何面對工業革命、啟蒙思潮、法國大革命等時代變局?
作者賈德森以綜覽全局的視角,發前人所未發的觀點,重新評價哈布斯堡帝國,讓世人認識帝國為何曾在如此悠久的歲月裡,對中歐數千萬人如此的重要。在哈布斯堡帝國解體前的幾十年和解體後的幾十年,有些觀察家把帝國貶為由彼此敵視的族群勉強拼湊成,且運作不良的集合體,貶為與時代脫節的帝國遺物。賈德森探究他們的動機,說明這些批評者的看法錯得有多離譜,事實上,曾有無數常民百姓,跨越了語言、宗教、地域、歷史的藩籬,忠於他們的「帝國」,曾有眾多官員、軍人、政治人物、學界人士,想出別出心裁的辦法來解決治理歐洲第二大國的難題。
《哈布斯堡帝國》是本大膽的翻案之作,摒棄了正在形成之諸民族其流於片斷的歷史,審視政府是如何弭合族群間的差異和隔閡,為帝國帶來長治久安。哈布斯堡的君王支持建設新學校、法院、鐵路,推動科學、藝術,使皇帝的權威穩穩屹立於中歐的諸文化、諸經濟體裡。帝國全境日益提升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哈布斯堡王朝統治的正當性,因為公民開始利用帝國的行政機構來造福自己的鄉里。
哈布斯堡帝國為了治理眾多的領邦和族群,祭出了諸多饒富新意的辦法,也遭遇許多解決不了的棘手問題。這些遺產仍深深影響帝國解體後繼之而起的中歐諸國,留下久久不消的印記。哈布斯堡帝國雖已逝去,但仍深深影響著現代的歐洲與世界。
作者簡介
彼得.賈德森Pieter M. Judson
荷蘭歷史學家,一九七八年畢業於美國斯沃斯莫爾學院,並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賈德森教授主要研究現代歐洲史、民族衝突、革命和反革命的社會運動,以及性別史,目前擔任義大利佛羅倫斯歐洲大學學院的十九、二十世紀歷史教授。
譯者簡介
黃中憲
政大外交系畢,專職筆譯。譯有喬納森.賴利-史密斯《十字軍戰爭全史》,彭慕蘭《大分流》,傑克.魏澤福《蒙古帝國》三部曲,法蘭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東尼.賈德《戰後歐洲六十年》,約翰.達爾文《未竟的帝國》、《帖木兒之後》,史蒂芬.普拉特《帝國暮色》、《太平天國之秋》、《湖南人與現代中國》,以及卜正民《維梅爾的帽子》、《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