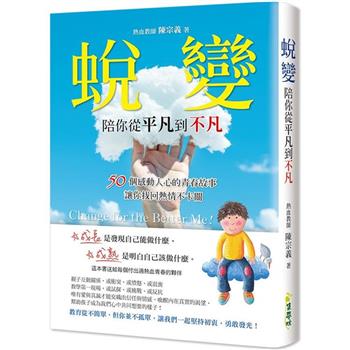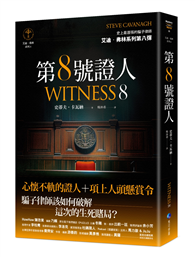圖書名稱:完美殘骸
索恩探長、雷博思探、哈利警探請小心了
新一代的警界超模盧克警探的魅力正在席捲全球!
犯罪小說天后海倫.菲爾德
盧克警探系列首部曲
★全系列亞馬遜讀者評價4.6星、全球最大書評網Goodreads 4.3星以上高分好評
★提名蘇格蘭麥基爾文學獎最佳小說
★入圍荷蘭青銅蝙蝠獎最佳處女作
★已售出美、法、德、法、義、波、泰等多國版權
★電影、電視劇版權授予Euston Films
余小芳(台灣推理作家協會理事)×杜鵑窩人(資深推理迷)×栞(文字工作者)×黃羅(推理讀書人)×劉仲彬(臨床心理師)——絕讚推薦!
完美的死亡將會留下完美的遺體——
一具屍體在偏遠的山區燒成灰燼,只剩下死者的牙齒和一小片碎布。同時,在愛丁堡某棟住宅的密室裡,另一名女子在黑暗中慘叫。
盧克.卡倫納督察到蘇格蘭警署就任的第一天,一樁兇殺案落到他手上。他得要證明一切,與剛認識的同僚艾娃.通納督察聯手對抗精心掩飾行跡的兇手。
第三名女子失蹤後,卡倫納一心只想保住受害者的性命——然而這些女子真正的命運遠比他想像的還要扭曲畸形……
猶如影集般快速而流暢的劇情節奏、活靈活現的描述,與詭譎多變的犯罪。除了精彩的案件,個性鮮明的角色也為故事增添精彩度,角色間的關係與火花更是一大看點!
作者簡介
海倫.菲爾德Helen Fields
海倫.菲爾德在英國東英吉利大學讀法律,接著進入倫敦城市大學法學院就讀。取得文憑後,她加入中殿律師學院,在刑法與家庭法的領域執業十三年,生下兩個孩子後,海倫離開法界,與丈夫大衛一同掌管電影製作公司,擔任腳本與製作人二職。《Perfect Remains》的背景設在蘇格蘭,對海倫而言,那裡幾乎像是她的心靈故鄉。目前她和丈夫、三個孩子、兩條狗兒住在漢普郡。
海倫熱愛推特,卻又覺得推特太容易上癮。可以在@Helen_Fields找到她。
譯者簡介
楊佳蓉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現為自由譯者,背負文字橫越語言的洪流,在翻譯之海中載浮載沉。近年譯有《只要活著:長崎原爆倖存者的生命故事》、《最後的戰役: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最後一刻》、《閣樓裡的小花5》、《黎亞:從醫病衝突到跨文化誤解的傷害》、《人皮盜獵者》、《迷蹤》、《比小說還離奇的12堂犯罪解剖課》等書。


 2021/09/20
2021/09/20 2021/06/17
2021/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