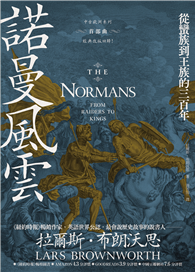第十章 山民
我們很快就碰到兩位山民跟我們打招呼,英俊健碩;雖然光腳走路,卻帶著庇里牛斯山當地人特有的優雅敏捷。帽上優雅裝飾著山區野花,身上散發的探險氣味令我十分興奮。
── 哈蒙德.德.卡邦尼耶荷,《庇里牛斯山之旅》(Travels in the Pyrenees, 1813)
歷史中,庇里牛斯山民經常受到外界不同眼光的想像,隨著對庇里牛斯山的態度一同改變。史特拉博語帶貶意地寫到阿斯圖里亞斯、坎特布連及庇里牛斯山蠻族的「粗俗野蠻」行為,例如睡在地上、吃山羊肉並「像女人一樣」蓄留長髮。這些伊比利山民喜歡運動,例如拳擊、跑步與武術;他們喝啤酒而非葡萄酒,隨著笛子與號角的音樂起舞,「以低姿上下蹲跳」。史特拉博寫作的時代,山岳在古希臘羅馬人的想像中,通常與原始蠻族有關。然而,在庇里牛斯山基督教化、並納入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朝聖之路後,此地居民仍被認為是非我族類。
《加里斯都抄本》形容巴斯克人為「勇猛族群;他們居住的土地是一片野蠻森林」。《加里斯都抄本》對於納瓦拉人的描述更嚴厲,他們被公認為「墮落、背信棄義、不忠腐敗、貪婪、酗酒、各種暴力、勇猛野蠻、厚顏無恥、無信無文、殘酷好辯,幾無美德可言,長於一切邪惡不公之事」。這些邪惡行徑似乎還包括了與動物進行「不倫通姦」,並據說導致納瓦拉人在驢馬後方加鎖,保護他們的獨享權利。這種不實際的可笑預防措施當然只存在作者個人的幻想之中。
十八世紀以降,對於庇里牛斯山民的形象描寫則漸趨正面。安娜.瑪麗亞.波特(Anna Maria Porter)的浪漫小說《白岩;或庇里牛斯山獵人》(Roche-Blanche; or, The Hunters of the Pyrenees, 1822)中的英國男主角克拉倫斯.威洛比在貝恩長大,透過與「熱愛身體行動且精神愉悅的庇里牛斯山居民」互動,發展出敏捷與力量。一八四○年,旅人記者亨利.大衛.英格利斯寫道:「我從未在庇里牛斯山民身上看見瑞士人令人困擾的罪惡─貪婪。山民與陌生人的接觸太過有限,因此未能澆熄他們自然的正義、慈善與慷慨……庇里牛斯山很少見到任何形式的犯罪;偷竊少見,謀殺更是前所未聞。」
法國製圖家艾瑪爾.達爾洛.德.聖索德(Aymar d’Arlot de Saint-Saud, 1853-1951),無數次進入西屬庇里牛斯山進行繪測,經常稱讚協助他的山民眼光敏銳,充滿求知慾。《西班牙庇里牛斯山地圖貢獻》(Contribution a la Carte Des Pyrénées Espagnols, 1892)書中,他羅列了「仁善、可親、慷慨、直率、誠實、對本地的驕傲」(作者自譯)為阿拉貢與加泰隆尼亞庇里牛斯山的西班牙居民主要的性格。比起他自己國家中「身心都比較不活躍」的山民,這些美德更讓他讚許。十九世紀的旅行書寫、畫作、明信片與旅遊海報,經常呼應這些描寫,讚美庇里牛斯山民的美德。庇里牛斯山納入現代世界的過程中,住在山間的人民也被「發現」。一如同一時期內「被發現」的地方,這些想像通常比較專注山民多采多姿的異國風情;也一如地景,通常是帶著浪漫主義透鏡描繪出來的。
牧羊人
動物畜牧業之外,很少有其他職業更能體現庇里牛斯山本質,也更被外界浪漫理想化。考古證據指出,早在新石器時代,牧羊人已經在庇里牛斯山放牧綿羊、山羊與牛隻,並囤積冬季飼料。有些學者主張山脈部分地區出現的大量史前石碑,是為了標誌通往高山牧地的路徑。在關於東庇里牛斯山的中世紀季節性牧群移動研究中,大衛.布蘭克斯(David Blanks)描述的畜牧經濟核心標誌在數世紀中從未改變。農家依靠綿羊、山羊與牛群提供奶、乳酪、羊毛、肥皂、肉及肥料,骨頭則用來製作容器、卡片、刀及笛子。
這類村落經濟中,每位家戶成員都有其角色:男人負責剪羊毛;女人則紡紗;年輕男孩放牧綿羊;女孩則負責送食物或送牛奶與奶油到山下。可能的情況下,少年會帶著牧群到最近的草地,當天則趕回主人家。但若草地很遠,這些少年可能會在高山上過夜,甚至度過整個夏天。通常由女孩組成的信使團,會從村裡帶來新鮮的麵包與訊息。十一月到五月中,這些動物則吃飼料。
光譜的另外一端則是大地主、修院或其他遙遠雇主,聘用專業牧羊人帶領大批羊群來回高山牧地。這些領薪水的牧羊人收取錢幣及食物,帶領羊群到高山牧地度夏,然後將牠們送回加泰隆尼亞,或甚至遠到瓦倫西亞過冬。有些人職業生涯中有多名雇主,後來自己也成為牲口飼主。穿越土地時,所有牧羊人都必須清楚谷地與村落之間訂定的《協議使用條約》,以及世俗與教會權威徵收的什一稅和其他要求,以乳酪、牛奶及羊毛支付。
一旦進入高山,這些牧羊人多少進入自治狀態。從一三一八至一三二五年,帕米耶(Pamiers)主教雅克.傅尼耶(Jacques Fournier)在富瓦伯爵領地蒙大猶(Montaillou)地區進行的卡特里異端宗教審判詰問中,我們可以得知比較有經驗的專業牧羊人(bergers),通常最多十人,帶著一百頭以上的牲口,群居在共享小屋中。夏季月份,他們照管牲口並製作乳酪與牛奶,放在特別挖出的洞或山澗的小「蓄水池」中保冷。小屋中則維持著嚴格階級,從屋長(chef de cabane,牧羊人領袖)一路到最低階的牧羊人移工,後者必須跟他們的牲口住在隔離出來的羊圈(cortals)中。這些中世紀牧羊人社群維持著嚴格規範。低階牧羊人不得先於領袖吃喝,破壞規則的人會遭毆打或禁食。
庇里牛斯山的世外桃源
這些中世紀牧羊人社群的獨立與行動能力,招來宗教審判的狐疑眼光;然而晚近時代裡,他們的形象大不相同。牧羊人是現代初期與舊制度(ancien regime)文學中的浪漫典型。一七七八年,以筆名德.讓利夫人(Madame de Genlis)廣為人知的法國大眾作家史黛芬妮─費莉西蒂.德.讓利(Stéphanie-Félicité de Genlis, 1746-1830),描述她在坎潘河谷遇到的真實庇里牛斯山牧羊人。她的筆觸完全符合當時瑪麗.安東妮宮廷中的流行。德.讓利的牧羊人描寫奠基在世外桃源的傳統中,她寫道,「古豎笛與風笛的粗獷聲響;牧羊人坐在岩石邊吟唱著鄉野氣息」或「庇里牛斯山的女兒們,每一位都驚人健美」帶著水果乳酪籃給她們的牧羊人祖父。眼見一名牧羊人送給愛人一束玫瑰花,德.讓利總結道:「若世上有幸福,就是這些行為,這些情感,希望永遠不變。」
這類思索通常伴隨著對牧羊人社群組織的細節描述。八、九歲的牧羊人會照看谷地正上方山坡上的羊群,年紀較大者則前進高山牧地。年輕牧羊人可以「爬上岩塊、跳過急流、無畏懸崖高度」,退休的牧羊人則在他們下方的谷地提供勞力、耕田或種植。十五歲時,少年牧羊人會從父親手中接過牧羊人手杖,父親則會接過鍬鏟,代表著農工的新角色,直到最終退休不再勞動,「躺在草地上……陷入深沉遐思」度日。
德.讓利對庇里牛斯山牧羊人的讚譽,也讓其他訪客頗有同感。「庇里牛斯山真正的居民,山中的本地牧羊人,雖然未經文明薰陶,或生活貧困,卻充滿活力、慷慨且高尚,即便困頓或遭遇厄運時也保持傲氣」,哈蒙德這樣描寫庇里牛斯山旅程中經常提供他遮風避雨之處的人。對哈蒙德來說,這些牧羊人體現了「真正的高貴」,是來自「種族而非氣候」。朱勒.米歇雷則描述「這些牧羊人的漫遊人生」是「南方最美好的一部分。這些游牧人,在永恆孤寂中伴星而行,半是天文學家,半是驅魔師,負重前行」。
庇里牛斯山牧羊人的生活,並不總是如外人所見的那般美好。前往高山草地季節游牧的牧羊人─艾斯提維斯(estives)─一出門就是幾個月的時間,與家人或牧羊人以外的其他人幾乎斷絕聯繫。在某些情況中,除了他們自己隨身帶進山的、像棺材一樣的木盒,或是阿列日省及庇里牛斯山其他區域可見的圓頂乾石堆積小屋─歐希(orris),他們幾乎無從遮風避雨。如果不是牲口群的主人,對牧羊人來說,付出這麼多時間與力氣,換得的物質回報卻是稀微的。「這些谷地豐美,但即便今日,土地耕種者也很少分得這些豐盛收穫。」阿薩.迪克斯在一八九○年代觀察到。「現在的庇里牛斯山農人或山人,一如過往,必須在貧困中養家。但他通常只能提供最微薄的食物給家人。毋庸置疑,就跟任何貧乏生活一樣,這種勉力維持生活的聯合焦慮,讓他與他們家人風霜憔悴。」季節游牧的牧羊人大半年都不見人影;夏日在高山上,冬天則回到低地,僅有短暫時間與妻兒見面。他們的妻子通常跟丈夫一樣孤寂,並不令人意外;阿拉貢庇里牛斯山的酗酒、早孕比例之高,足以證明。
羅莎.邦賀神采飛揚的庇里牛斯赤腳牧羊人畫作,或十九世紀法國明信片與「溫泉之路」鐵路海報裡,庇里牛斯牧羊人帶著手杖、羊群與牧羊犬走在原始山景前的景象,容易模糊了牧羊生活的嚴酷現實。這些法國明信片經常描繪帶著寬邊帽、穿著斗篷的西班牙牧羊人,是更「野蠻的」西班牙庇里牛斯山的狂野表現。二十世紀初,西班牙攝影師與藥劑師李卡多.康百赫.艾斯卡爾丁(Ricardo Compairé Escartín, 1883-1965),將幾張令人驚豔的高山西班牙牧羊人照片,收進他領先群倫的上阿拉貢地區民族誌研究中。康百赫是個狂熱的庇里牛斯山學者,牧羊人與農人穿著傳統服飾面對鏡頭的美麗照片,正是他有意識記錄下已經開始從山區消逝的習俗、服飾與傳統。十九、二十世紀初肖像中理想化的庇里牛斯山傳承與傳統,卻帶著一股鄉愁思緒,感懷那個已經被現代化徹底改變的社會。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黑暗山谷
這股改變的強度可以從佛斯卡山谷(黑暗山谷)中窺見,此地就在加泰隆尼亞庇里牛斯山的艾古埃斯托特斯國家公園中。山谷之名來自陡峭狹窄的邊坡,限制了冬季月份能射進谷地的日照。多數遊客從通往阿蘭山谷與法國的主要道路進入。離開蘇威特橋鎮(Pont de Suert)不久後,向右轉,進入一條大致沿著弗拉米賽爾河(Flamisell River)的道路。接著開上一條陡峭山坡之間的彎曲山路,山坡上仍舊布滿濃密橡樹與聖櫟,向上穿越一連串草原台地,間或點綴著加泰隆尼亞庇里牛斯山常見的平庸滑雪村。
直到二十世紀初,佛斯卡山谷幾乎完全與外界隔離。一千四百位居民住在十九個村落中,半封建農業社會由三大家族把持,沒有學校、電力或馬車步徑以外的道路。多數人穿著木鞋或光腳。一如幾世紀來的習慣,他們與牲口同住,主要靠牧養牛羊、馬驢育種或製作犁具、馬鞍或其他農家副業來維生。一九一二年加泰隆尼亞電力公司(Energía Eléctric de Catalunya,簡稱E E C)展開一項野心計畫,也打破他們與世隔絕的環境。E E C打算開發今日艾古埃斯托特斯國家公園境內三十七座冰斗湖的水力發電,供電給一百五十五英哩(兩百五十公里)外巴塞隆納的紡織工廠。
這個計畫是由艾米利.利烏.派利蓋特(Emili Riu i Periquet, 1871-1928)提出。這位出身附近索爾特城的記者、政治家兼企業家,聯合加泰隆尼亞與外國投資者,在一九一一年成立加泰隆尼亞電力公司。一九一二年夏天,四千多名加泰隆尼亞、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與土耳其工人進入佛斯卡山谷,無分晴雨在超過六千五百六十二英呎(兩千公尺)的高度工作,這些工人造出一條十九英哩(三十公里)長的公路,從最近的賽古爾村(Pobla de Segur)直接進入上谷地,此外還建立電話線、發電站及軍營式的營地。他們在十二座湖泊間,開鑿出全長九點五英哩(十五公里)的隧道網絡,將湖水引入一條大型洩洪道,從高山直洩下方一點九英哩(三公里)的卡普德拉村(Capdella)發電站。
一切在難以置信的二十三個月內完工。今日發電站仍舊營運,但得站在山谷上方、薩岩特蓄水池(Sallent reservoir)後的荒涼岩峰人工林後露出頭來,才會發現這個系統的驚人工程成就。從蓄水池搭乘纜車往上到漢托湖(Estany Gento),洩洪道由此將水洩到兩千七百九十英呎(八百五十公尺)的山下。過去驢車走的窄軌道,現在成為穿梭一連串狹窄隧道的健行路徑,繞過蒙策尼山脈,途經多已棄置的舊抽水站與其他工業建築。
一張舊照片顯示,一群利烏手下的工人穿著背心與草繩編底的涼鞋,站在湖面由滑輪拉繩控制的鐵桿上。就像完成紐約摩天大樓的工人照片一樣,他們也露出完成史詩任務的驕傲神情,以及一週七天,一天十一小時工作的肉體韌性。即便天氣狀況有時會迫使他們用冰爪、雪鞋及冰斧工作。原始的現場工作條件下,仍有約四千名工人最終落腳在卡普德拉。這個社區擁有自己的電影院、圖書館、網球場與食堂,還有加泰隆尼亞電力公司經營的旅館,就叫「電力旅館」。這些發展對山谷原住民來說有立即與長遠的影響。部分當地人宣稱「他們」的電力被奪走,地主則從加泰隆尼亞電力公司獲得永久補償,保證永久享有無償電力。大量生產的產品衝擊當地經濟,農民拋棄舊業,選擇電力公司比較好的薪資與工作,並開始將孩子送進公司學校。不過幾年時間,數世紀未曾改變的生活型態已經面目全非。在整個庇里牛斯山間,類似過程在不同地方以不同速度推進。
庇里牛斯山社會從來不只是牧民社會。早在西元前一世紀,法屬庇里牛斯山中部的羅馬行省就挖出金、銀、銅及其他金屬。現在的聖伯特航─德─康明居(Saint-Bertrand-de-Comminges),舊稱盧格度倫(Lugdunum),也設有大理石採石場。一七七八年,邊境城鎮普威格塞爾達中有兩千四百名婦女進行紡紗與毛襪編織。一八三七年,穆瑞觀察到卡洛爾山谷(Carol Valley)居民製作的羊毛襪,每年有三萬雙出口到波爾多、土魯斯及法國其他地區。一八九○年,《黑森林》(Blackwoods)雜誌報導「放牧職業只佔庇里牛斯山商業很小的一部分……由於四處可見的水力,許多村落都有磨坊與鋸木廠。部分山谷中……幾乎每個農人都有粗糙的小型石磨,將自己的大麥、蕎麥與玉米磨成粉。手織機數量很多,紡出農人們穿的粗羊毛布」。
如同佛斯卡山谷,庇里牛斯山的工業化破壞了地方村落經濟,卻也提供了農業之外更高薪的選擇,農民與牧羊人放棄土地,前往都市工作,或在休閒觀光業,或十九世紀開始四處興起的礦業、工廠與工坊,尋求新就業機會。在阿列日省的畢羅斯山谷(Biros Valley),許多當地人放棄牧羊,前往蒙大猶與布拉爾(Bulard)的含銀與含鋅鉛礦裡工作。法屬庇里牛斯山維克戴索社區(Vicdessos)中,一九一○年冶金工廠開張後,農場數量也大幅減少。
動物養殖產業化;社區共有土地使用與放牧路線有限制;人口減少;年輕人不願意接受辛苦低薪的工作。以上這些因素都構成牧羊人與飼主數量的長期減少。但庇里牛斯山的古老放牧世界從未全然消失。從貝恩庇里牛斯山區移民到美國的旅程中,主廚尚.路易.馬托克(Jean Louis Matocq)動人描述二十世紀中期庇里牛斯山的童年時光,相信他的中世紀先人應該也不會太陌生。住在三百年歷史的農場上,沒有水電、廁所,十一歲的他已經開始犁田、擠奶、牧羊並為冬天準備牧草。一八三七年,穆瑞寫到「庇里牛斯牧羊人(以狗及哨子)聚攏羊群的敏捷」。「在這些山中,看不到『趕羊』;」他寫道,「聚攏羊群或阻止牠們亂走,不需要『認識牧羊犬』;庇里牛斯山的牧羊人、他的狗與羊群似乎都很清楚彼此的職責;相互信任與情感將他們結合在一起。」
今日估計庇里牛斯山仍有上百萬頭綿羊;日落時高山草原上,庇里牛斯山犬(Patou)輕鬆聚攏羊群的景象,仍舊是庇里牛斯山最美的奇觀之一。在馬爾卡道山谷(Marcadau Valley)與奧索谷地,你仍舊可以看到卡其奶油色的庇里牛斯山乳牛,脖子上掛著巨大鈴鐺;還可以向牧羊人共享小屋購買新鮮製作的乳酪,或經過牽著滿載乳酪牛奶的騾驢;遇見從高山牧地下行的男女。牧羊人仍舊在每年夏天帶著羊群進行年度季節放牧,只是現在許多人用卡車或廂型車載運牲口,並騎摩托車或越野車去照看羊群。雖說如此,仍舊可以看到在高山上獨居的牧羊人,吹口哨或呼喚動物;他們彷彿是十四世紀阿列日或塞爾達涅牧羊人的後代,正如埃曼紐.勒華.拉杜里所說的「就像他呼吸的山風一樣自由」。
夜間工作
另一種十九世紀旅人也經常稱道的庇里牛斯山知名職業,卻大相逕庭。巴斯克語稱為「夜間工作」(gaulana)的走私,可以溯源至十六世紀,當時菲利普二世想將庇里牛斯山變成「異端邊境」,並將取締非法走私也納入宗教審判的職責之中。但不論是聖職或世俗執法人員都無法在山脈間施展權威,這片地域提供了無止境的潛逃躲避機會。十六世紀的庇里牛斯山多數區域仍舊是無法無人之地,盜匪、潛逃者、造假者、逃犯和燒炭、伐木與鑄鐵工比鄰而居。
許多盜匪走私者來自貴族,例如烏埃斯卡省希斯塔因山谷(Gistaín Valley)的聖胡安德普蘭(San Juan de Plan)領主菲利培.德.巴達西(Felipe de Bardaxí),他的匪團事業結合了搶劫、謀殺與跨境馬匹走私。巴達西也在法國宗教戰爭期間擔任西班牙王室間諜,與天主教軍隊共同對抗胡格諾派。也因此,他持續享有王室保護,直到他在村落接受聖餐禮時遭到部分敵人以斧頭砍殺。他的名聲如此響亮,以致聖胡安的居民以天主經及聖母經禱文慶祝他的死亡。這項傳統一直延續到一八八八年。
十八、十九世紀期間,法西兩國政府偶爾攜手合作打擊未稅品走私。一七二二年,巴黎與馬德里法院同意遣送「盜賊、刺客與遺棄者」返回各自國家,這類合作也包含走私客。一七七三年五月,一百四十名走私客暫時控制了邊境城市普威格塞爾達,並放出監獄裡遭到判刑的兄弟。回應此舉,兩國政府簽訂了一系列條約,允許軍隊跨越邊境追捕走私客。
一八三○年,西班牙政府祭出嚴格的反走私法,刑罰包含流放到安地列斯群島(Antilles)與絞刑。一八四二年,財政部為了在邊境執行海關禁令,將世紀初成立的準軍事組織卡賓槍隊,改隸屬戰爭部,以強化對庇里牛斯山邊境的管控。但這些努力並未生效。許多庇里牛斯山村莊谷地依靠這些帶貨人(paqueteros)維持繁榮與生存。有一次,在十九世紀的烏埃斯卡省阿伊薩(Aísa)的阿拉貢村落中,一名當地神父請求女王伊莎貝二世(Isabel II)赦免同村十二人。這些人因為搶劫政府商店內的貨物而遭逮捕,部分則為了躲避追緝而逃進法國。神父請求的理由是村裡已經沒有男人可以照顧動物與收成。
在阿拉貢與納瓦拉地區,走私是種專業或半專業活動,甚至到了需要一行上百名武裝人員護送騾隊,揹著家用物品、工具、橄欖油、菸草、火腿與槍枝穿越山脈的地步。阿拉貢地區的艾丘與安索山谷中,走私客經常與卡賓槍隊發生徹夜戰鬥。在安道爾,西班牙走私客利用共治公國位於法國境內的地理便利,逃避關稅;法國商人則利用安道爾對西班牙的免稅身分,從安道爾走私法國商品進入西班牙。十九世紀時,安道爾成為西班牙菸草走私進入法國的主要途徑,許多安道爾人開始特別為了法國市場種植菸草。
一如常態,壓制並無法阻絕價差及供需變化產生的產業。十八世紀,塞爾達涅成為西班牙金銀非法進入法國的主要入口。一八一八年,一名法國海關首長抱怨,工業織機與有經驗的工人透過塞爾達涅走私進入加泰隆尼亞,強化了當地紡織工業。第一次卡洛斯派戰爭期間,西班牙政府經常抱怨,卡洛斯派軍隊獲得法國走私客提供的火藥,法國當局則下令禁止邊境一帶居民擁有火藥,試圖阻止走私。
這些禁令卻未能阻止這些活動,甚至可能揠苗助長,這似乎是邊界禁令的常態。卡洛斯戰爭也造成西班牙對於走私制服、穀物、武器及士兵的需求大增。一八四○年第一次卡洛斯戰爭期間,從聖尚─德呂茲穿越法西邊界的泰奧菲爾.高提耶觀察到,「戰爭造成兩類物資的邊界交易:首先是戰場上撿拾到的子彈,其次則是人口走私。他們像成堆物品一樣外銷卡洛斯派人士,甚至還有標價;上校多少錢,軍官多少錢。一旦成交,走私客前來帶走他的人,送過邊界到達目的地。就像送交一打手帕或一百根香菸一樣。」英國卡洛斯派志願兵查爾斯.費德列克.海寧森後來回憶走私客帶著他「穿越十分陡峭危險的山道,平時沒經驗的旅人想到路上的自然凶險,大概就裹足不前了」。
由於走私對庇里牛斯山谷地經濟的重要性,也就不難理解收入豐碩又膽大的走私客經常被視為本地英雄。「艾丘之王」培德羅.布倫(Pedro Brun)在十九世紀初期與卡賓槍隊對戰無數,導致伊莎貝二世對他懸賞通緝。布倫索性親自從阿拉貢家鄉前往馬德里宮廷,此舉贏得女王賞識,因而迅速獲得釋放。庇里牛斯山走私客也常被外界視為迷人角色。法國海報與明信片經常描繪穿著多彩服裝、帶著毛瑟槍、身負貨物的西班牙走私客,爬上孤寂山徑。古斯塔夫.多海就畫下武裝走私客靠在山邊的動人肖像。甚受歡迎的法國插畫家保羅.格瓦尼(Paul Gavarni, 1804-1866)也畫下他在庇里牛斯山旅程中遇見的幾位走私客,畫面極富異國風情且浪漫,並從中取為自己的筆名。
這類形象經常以哈蒙德從羅蘭隘口下山時遇到的走私客為基礎:「從這人的面容上,我可以感受到大膽與自信的結合;濃密糾結的鬍鬚漫入墨黑捲髮;寬闊胸膛坦露著,強壯緊繃的腿腳裸露;全身上下的衣物就是一件簡單背心;腳上所穿的就像羅馬與哥德人的風格,從腳跟而起的一片牛皮像皮包包覆,以兩條繫帶在踝上交叉打結固定。」
一八七三年,哈蒙德協會創始成員法國詩人菲德希克.蘇特哈(Frédéric Soutras, 1814-1874),出版名為〈山岳回響〉(Les échos de la montagne)的三百五十行詩作,讚美來自奧爾山谷(Vallée d’Aure)艾斯東桑村(Estensan)的走私客布希斯.德.艾斯東桑(Brice d’Estensan)槍殺兩名關稅人員的事蹟。對蘇特哈來說,布希斯是真正的反抗者,「山峰上的獵人/冰河之側/看到臆羚/他想到關稅人員」,代表山谷人民智退財政官員的壓迫,逍遙山中追求無數的庇里牛斯山女性。走私客的描寫也並非總是如此美好。亨利.羅素曾告訴法國山岳俱樂部,他與夥伴在加爾瓦涅的牧羊人共享小屋,曾遭「四名可惡的西班牙人(設計)……腰上帶著閃亮短劍、斧頭與刀」。雖然兩名友人遭斧頭挾持,羅素與另一人逃出,在森林中躲了一晚,直到走私客離去。兩名人質毫髮無傷。
多數走私客並非盜匪,而是庇里牛斯山兩側平民。一八三○年代,塞爾達涅一名法國軍官抱怨走私貿易已經「導致人民放棄一般工作。這些邊境區域沒有一個居民願意接受誠實輕鬆的工作與薪水,反而熱切擁抱走私事業。對他來說只看到苦工,對他人而言則是價值與樂趣」。二十世紀初,西班牙季節性移工經常用收入購買手錶與其他物品,未稅帶回村落。住在邊境附近的法國男女也慣常進行所謂的「家庭走私」(pacotille),跨越邊境到西班牙商店購物,法國邊管人員通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些西班牙人甚至就將店開在邊境邊,販售肉品、新鮮蔬果、葡萄酒、烈酒及香菸。
二十世紀多數時間,跨越庇里牛斯山的走私物沿著大致模式:工業製品從法國進入西班牙,農業產物則從西班牙進入法國。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個模式曾短暫反轉,庇里牛斯山走私客將所謂的奢華物資送進法國佔領區中,包含盤尼西林、蕾絲、線、糖與橄欖油,帶回來的貨物款項則以現金、珠寶與黃金支付。許多走私客也走私人口跨越庇里牛斯山進入西班牙,包含潛逃的猶太人、盟軍飛行員與自由法國支持者。戰後,貨物走私再度回到戰前模式,走私客再度從法國挾帶球型軸承、銅、精密儀器及其他工業製品進入西班牙;而酒類、綿羊、驢子、牛隻與馬則走相反路線。一九六○年代,走私開始減少,因為邊界兩側的物價差別降低,走私成本則上揚。一九七○年,走私已經成為邊緣活動;到了一九九五年,西班牙正式加入申根區時,走私就跟邊界本身一樣,成了不合時宜的歷史產物。
今日,走私歷史則成了吸引觀光的「名勝」。在安道爾,聖胡利亞德洛利亞(Sant Julià de Lòria)的菸草博物館展示《孤獨星球》指南所稱的「吞雲吐霧與走私的頹廢樂趣」。旅遊書籍仍舊邀請讀者一訪曾以「薩雷共和國」聞名的法屬巴斯克薩雷村(Salé),此地擁有漫長的走私歷史。其他庇里牛斯山專業也同樣納入文化遺產產業鏈中。露德的庇里牛斯山博物館中,觀光客可以在精美整修過後的貝恩農舍中觀賞田犁、鋤頭、攪奶桶、家具及牧羊人人型的漂亮展示。
其他庇里牛斯山博物館則致力於木塞工業、本地民俗服飾、農業施作、礦業、鹽業、民族誌與民俗傳統。在阿拉貢庇里牛斯山,每年春季都會舉行競賽,紀念過去將樹幹捆在一起送下高山的「筏夫」(navateros)。當地協會以傳統方式綑綁木身成筏(navatas),控制這些木筏沿著湍急河流而下。法屬與西屬庇里牛斯山間,健行者與訪客可以參加年度牧羊人節慶(fêtes des bergers),伴隨牧羊人進入高山。部分庇里牛斯山村莊仍舊慶祝的習俗傳統,可遠溯至前現代歷史中的神話迷信,這些也是庇里牛斯山過往的一部分。
|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寫給庇里牛斯山的情書:蠻荒與瑰麗、澎湃與抒情,一個歷史與想像中的野蠻邊境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寫給庇里牛斯山的情書:蠻荒與瑰麗、澎湃與抒情,一個歷史與想像中的野蠻邊境
改變的,是我們觀看他的方式。
王公貴族 騷人墨客 政治人物 異議分子
教士 巫師 獵人 農民 巫師 走私犯 登山客 旅行家
他們沒入庇里牛斯山的幽谷、陡壁、冰川、密林、狼熊之中,留下深刻的足跡。
馬修.卡爾領我們走進群山,與山對話, 觀看交融在庇里牛斯山地景裡的歷史、文學與生命。
《地中海史詩三部曲》作者羅傑.克勞利盛讚:
「馬修.卡爾深刻研究後,寫下這本豐厚而引人入勝的歷史篇章,精彩傳奇故事,熱烈勾劃歐洲最鮮為人知之地的獨特之美。」
#庇里牛斯山可以是野蠻的
文豪大仲馬說過「非洲始於庇里牛斯山」。伊比利半島曾被穆斯林摩爾人統治,透過這座崎嶇炙熱的山徑,法蘭克人成功抵禦了摩爾人的威脅,但自此以後,山的另一側被視為野蠻非洲的延伸、歐洲文明的南限。
#庇里牛斯山可以是分裂的
西元一六五九年,法西兩國簽訂《庇里牛斯條約》,從此確立兩國的邊界。許多王公領土、信仰教派,以山為界,人們有意識地以山勢阻擋對側的滲透。如果說山稜界線界定了法西兩國,不如說法西以山定義了自己。
#庇里牛斯山可以是神聖的
雄偉山勢總讓人們興起讚嘆之情,人們建立教堂、見證顯靈,造就知名的聖地牙哥朝聖之路。同時,萬物有靈信仰也流竄在山民之間,引起宗教法庭獵捕「恬不知恥的巫師」,駭人的審判以神之名展開……
#庇里牛斯山可以是共榮的
自古以來,山民就在這裡放牧,人們立起鄉約,分享肥沃的草地與山泉,讓山稜兩側的牧民都能使用,即便在戰爭期間也絲毫不改。邊境是一片獨立的地帶,讓遠走他鄉的遊子,憑著記憶,多年後再次歸返。
走進野蠻、魔幻、激情的地景之中
我們踏下的每一步,是回憶、是過往,也是自身的探索與對話。山本身雖然擁有許多面貌,但對山的感官都是由我們後建的,它可能是美好、恐怖甚至迷幻的。山,仍舊不動,橫亙在大地上,不論人性如何留下痕跡,都會堅毅見證。
▁ ▃ ▅ ▇ 各方推薦 ▇ ▅ ▃ ▁
「馬修.卡爾為這片美麗而戲劇化的土地,織就一幅無與倫比的多彩織錦。古往今來的居民,包含牧羊人、走私客、士兵、間諜、聖者、異端、盜匪與怪人,都呈現在這部細密研究的庇里牛斯山情書之中。」
——《阿爾卑斯山:從漢尼拔到海蒂的人類史》作者史蒂芬.歐席亞(Stephen O’ Shea)
「馬修.卡爾同時登上研究與岩石的高峰,無愧為當代首屈一指的『庇里牛斯山學家』。」
——《邊境管控的臭臉女士:從貝爾格勒到烏蘭巴托的地下龐克之旅》作者法蘭茲.尼可萊(Franz Nicolay)
「卡爾為西班牙與法國之間的山脈分野,寫下一段魔幻紀錄:此地的巫師異端、偏遠村落、古老的獨立傳統及多樣交雜的語言。優美文字精心交織著作者本人的旅行記事與庇里牛斯山歷史。」
——劍橋大學地中海史榮譽教授、《偉大的海:地中海世界人文史》作者大衛.阿布拉菲雅(David Abulafia)
作者簡介:
馬修.卡爾Matthew Carr
著有多部紀實作品,包含《血與信仰:肅清西班牙的穆斯林》(Blood and Faith)、《壁壘歐洲》(Fortres Europe)、《謝曼的鬼魂》(Sherman’s Ghosts)與《烈火機器:恐怖主義史》(The Infernal Machine),以及小說《卡爾多納的惡魔》(The Devils of Cardona)。作品散見《紐約時報》、英國《觀察家報》與《衛報》等媒體。目前定居英國。
譯者簡介:
林玉菁
紐約市立大學政治學博士班,劍橋大學印度研究碩士,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曾任職IFRC國際紅十字與紅星月會聯合會美洲辦公室,雲門基金會,北藝大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及國內外NGO組織。現為專職口譯、筆譯。
章節試閱
第十章 山民
我們很快就碰到兩位山民跟我們打招呼,英俊健碩;雖然光腳走路,卻帶著庇里牛斯山當地人特有的優雅敏捷。帽上優雅裝飾著山區野花,身上散發的探險氣味令我十分興奮。
── 哈蒙德.德.卡邦尼耶荷,《庇里牛斯山之旅》(Travels in the Pyrenees, 1813)
歷史中,庇里牛斯山民經常受到外界不同眼光的想像,隨著對庇里牛斯山的態度一同改變。史特拉博語帶貶意地寫到阿斯圖里亞斯、坎特布連及庇里牛斯山蠻族的「粗俗野蠻」行為,例如睡在地上、吃山羊肉並「像女人一樣」蓄留長髮。這些伊比利山民喜歡運動,例如拳擊、跑...
我們很快就碰到兩位山民跟我們打招呼,英俊健碩;雖然光腳走路,卻帶著庇里牛斯山當地人特有的優雅敏捷。帽上優雅裝飾著山區野花,身上散發的探險氣味令我十分興奮。
── 哈蒙德.德.卡邦尼耶荷,《庇里牛斯山之旅》(Travels in the Pyrenees, 1813)
歷史中,庇里牛斯山民經常受到外界不同眼光的想像,隨著對庇里牛斯山的態度一同改變。史特拉博語帶貶意地寫到阿斯圖里亞斯、坎特布連及庇里牛斯山蠻族的「粗俗野蠻」行為,例如睡在地上、吃山羊肉並「像女人一樣」蓄留長髮。這些伊比利山民喜歡運動,例如拳擊、跑...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地圖一 一七一七年古地圖
地圖二 當代庇里牛斯山周遭
前言:來自聖山
第一部:完美邊界
第一章 土地
第二章 消失的邊界
第三章 「非洲始於庇里牛斯山」
第二部:跨越庇里牛斯山
第四章 學者、朝聖者與吟遊詩人
第五章 戰區 第六章 安全天堂
第三部:魔法山脈
第七章 拓荒者:「發現」庇里牛斯山
第八章 訪客
第九章 失落王國
第四部:世界之上的家園
第十章 山民
第十一章 野東西
第十二章 鬼城
後話:過去的未來——二十一世紀中的庇里牛斯山
致謝
註解
地圖二 當代庇里牛斯山周遭
前言:來自聖山
第一部:完美邊界
第一章 土地
第二章 消失的邊界
第三章 「非洲始於庇里牛斯山」
第二部:跨越庇里牛斯山
第四章 學者、朝聖者與吟遊詩人
第五章 戰區 第六章 安全天堂
第三部:魔法山脈
第七章 拓荒者:「發現」庇里牛斯山
第八章 訪客
第九章 失落王國
第四部:世界之上的家園
第十章 山民
第十一章 野東西
第十二章 鬼城
後話:過去的未來——二十一世紀中的庇里牛斯山
致謝
註解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