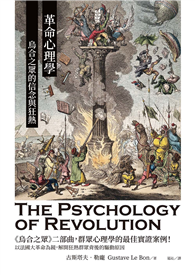圖書名稱:艾爾多安的崛起
為何歐美西方討好他、俄羅斯敬重他、中東各國師從他?
艾爾多安到底有何魅力與技巧,讓可能分崩離析土耳其比過往更堅強?
二十一世紀以來,你看到的土耳其,就等於艾爾多安!
想到土耳其,你可以問問看自己:這是個民主國家?還是集權統治國度?
是世俗化的伊斯蘭資本主義典範?還是逆行倒施的宗教保守右派?
這些疑問,終歸一人:艾爾多安!
土耳其共和國建國百年, 唯一與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相提並論的政治人物!
一九二三年,土耳其共和國取代鄂圖曼帝國成立,領導獨立戰爭的軍官凱末爾,理所當然成為土耳其的第一任總統。而土耳其也在他去世前,徹底改造成現代國家。凱末爾被賦予了「阿塔圖克」這個稱呼──「土耳其的國父」──顯見其偉大。
「阿塔圖克已經死了八十一年,他仍舊活躍在今日土耳其人的想像中。」
就算再怎麼保守的伊斯蘭主義者、再怎麼厭惡西方霸權、再怎麼不屑世俗主義的迂腐,甚少土耳其人膽敢貶損凱末爾,但這也給了艾爾多安崛起的舞台。身為藍領階級出身、對信仰的堅定,他成為相對於凱末爾的逆流,一個不同於過往歐化的資產階級;他聆聽人民的需求,了解他們身為公民想要發聲的欲望。人民不要一個只會迎合西方的土耳其,而是乘載信仰靈魂,一個有國格、有地位的國家。
「他是天生的演說家,技巧高超的政客,也是天才民粹主義者;戰爭的領袖。」
艾爾多安強調土耳其的本質與尊嚴,讓他在國內普遍受到歡迎。他也明白在地緣政治裡的重要性,在西歐、中東與前蘇聯之間,他不僅扮演緩衝的角色,而且扮演得極好!土耳其擁有北大西洋公約國中規模第二大的軍隊,跟以色列的關係也比其他中東國家更和睦,也歡迎上百萬敘利亞、伊拉克難民。艾爾多安或許並不擅長戰爭本身,但深諳政治的兩面藝術,他觀察情勢何時對他有利,並進一步把將國家捲進獨裁統治的陰影下。
「那個一度願意學習、願意傾聽外界聲音、傾聽批評的人已經遠去。」
那個在伊斯坦堡平民區叫賣、給家裡添補家用,深知土耳其的階層斷裂、需要為低階平民發聲的領袖艾爾多安,已經不在了。隨著歐美的軟弱與背叛,艾爾多安已明顯感到不耐煩。國內少數民族與境外勢力眉來眼去,讓他窮於應付卻得不到鼓勵。最重要的是,二〇一六軍方帶頭、以世俗主義精神為輔的政變失敗了,更讓他本人更加多疑、剛愎自用。但土耳其人的支持似乎沒有顯著削減,追隨著艾爾多安,盼望著土耳其能更偉大。
當艾爾多安承諾他要洗滌土耳其的靈魂,而這個靈魂漸漸等於他自己時,土耳其該怎麼走下去?
作者簡介
漢娜.露辛達.史密斯Hannah Lucinda Smith
擔任倫敦《泰晤士報》駐土耳其特派員期間,報導武裝衝突、軍事政變與艾爾多安總統的爭議性崛起。這段期間,她也進入敘利亞反抗軍佔領區、伊拉克對抗伊斯蘭國的前線,並加入二〇一五年湧入歐洲的大規模難民潮進行報導。
譯者簡介
林玉菁
紐約市立大學政治學博士班,劍橋大學印度研究碩士,政大新聞系。曾任職IFRC國際紅十字與紅星月會聯合會美洲辦公室,雲門基金會,北藝大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及國內外NGO組織。現為專職口譯、筆譯。譯有《中國的印度戰爭》、《業的盡頭》、《榮耀之城伊斯坦堡》、《達文西傳》、《印度:南亞文化的霸權》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