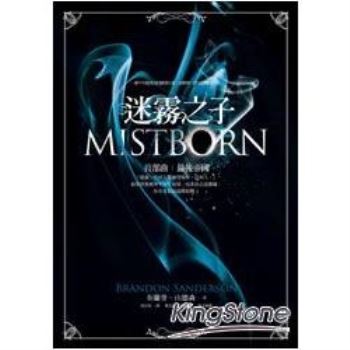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座金閣寺。
它魔性、不可方物的美,一步步把我們逼向黑暗深淵。
你該如何與之共處?也許,只有令其毀滅……
★ 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三島由紀夫樹立西方文壇聲譽的最高傑作
★ 日本文學翻譯名家劉子倩傾力重現原典,以洗鍊幽微的文字,帶領讀者窺見細膩、瑰麗且乖張的三島式語言之美
★ 全書採硬皮精裝形式,由設計師許晉維操刀,以「侵蝕心中美麗信仰」為裝幀概念,極具收藏價值
★ 何謂美與惡?孤獨與永恆?毀滅與重生?建築師、文學迷、哲學家、創作者與文化旅人都需要的一本常備書
「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始得解脫!」
進入三島由紀夫【美與爆裂世界】必讀經典
本書取材自1950年一名年輕僧人林承賢火燒金閣寺的真實事件。在現實世界中,犯嫌向警方供稱:「我忌妒金閣寺的美,所以把它燒掉了……」在小說中,主角溝口將心靈寄託於金閣寺的美,藉此逃避他對自我價值的扭曲與幻滅。
《金閣寺》自1956年問世以來即受各方盛讚,公認本作為三島美與爆裂哲思之集大成者,被翻譯成多國語言,亦被視為是三島由紀夫角逐諾貝爾文學獎、樹立西方文壇聲譽的最高傑作。
關於金閣寺,三島由紀夫想說的是:
美的毀滅,遠比美的本體更令人目眩神迷……
金閣不是無力。絕非無力──但它是一切無力的根源!
金閣寺的美之所以令人畏懼,是它的美讓人看到自身的醜陋。正如小說所言:
「一般而言,有生命的東西都不具備金閣那種嚴密的一次性。人類只不過是接收大自然各種屬性的一部分,用可替代的方法傳播、繁殖而已。
殺人若是為了消滅對象的一次性,殺人就是永遠的誤算。我如是想。因此金閣與人類越發呈現明確的對比;另一方面,從人類容易毀滅的身影中,反而浮現永生的幻影,從金閣的不壞之美,反而飄來毀滅的可能性。
像人類這樣注定會死的生物是不可能根絕的,而像金閣這樣不滅的東西反倒可以消滅。為什麼人們沒有察覺這點呢?我的獨創性不容置疑。」
作者簡介:
▋三島由紀夫
本名平岡公威,一九二五年出生於東京。一九四七年自東京大學法學部畢業,通過高等文官考試,隨後進入大藏省任職,隔年為了專心從事寫作而從大藏省離職,開始專職作家的生涯。
三島由紀夫在日本文壇擁有高度聲譽,其作品在西方世界也有崇高的評價,曾三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也是二戰結束之後西方譯介最多的日本作家之一。
三島對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深為讚賞,他對日本二次大戰後社會的西化和日本主權受制於美國非常不滿。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帶領四名「盾會」成員前往陸上自衛隊東部總監部,挾持師團長要求軍事政變,期使自衛隊能轉變為正常的軍隊,但是卻乏人響應,因而切腹自殺以身殉道,走上了日本武士最絢爛的歸途。
主要著作有《豐饒之海》四部曲、《假面的告白》、《金閣寺》、《鏡子之家》、《盛夏之死》、《憂國》、《反貞女大學》、《不道德教育講座》等。
譯者簡介:
▋劉子倩
政治大學社會系畢業,日本筑波大學社會學碩士,現為專職譯者。譯有小說、勵志、實用、藝術等多種書籍,包括三島由紀夫《憂國》;川端康成《伊豆之旅》;谷崎潤一郎《春琴抄》、《痴人之愛》、《陰翳禮讚》、《瘋癲老人日記》;太宰治《女生徒》;夏目漱石《門》、《少爺》、《虞美人草》;宮澤賢治《銀河鐵道之夜》等日本文學作品,皆為大牌出版。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從小,父親就經常對我提起金閣。
我出生的地方,是舞鶴往東北的日本海伸出的冷清海岬。父親的故鄉不在那裡,在舞鶴東郊的志樂。他在眾人企盼下入了僧籍,成為偏僻海岬的佛寺住持,在當地娶妻,生下我這個孩子。
成生岬的佛寺附近沒有合適的中學。因此之後我離開雙親膝下,寄居父親故鄉的叔父家,從叔父家徒步往返東舞鶴中學上學。
父親的故鄉是陽光普照之地。但一年之中每逢十一月、十二月,即便看似萬里無雲的晴天,一天也會有四、五場陣雨。我易變的心情,或許就是在這種土地養成。
五月的傍晚,放學回來後,我從叔父家二樓的書房眺望對面的小山。滿眼新綠的山腰被夕陽照亮,彷彿於山野中央建了一座金屏風。看著那個,我不禁遙想金閣。
雖然透過照片和教科書經常見到現實中的金閣,但在我心目中,父親描述的金閣幻影更勝一籌。記憶中父親從不曾說現實中的金閣金光閃閃,但據父親表示,世間沒有比金閣更美的東西,而我根據金閣這個字面及發音想像出來的金閣也非同凡響。
有時看到遠處的水田在陽光下閃爍,我就覺得那一定是看不到的金閣的投影。形成福井縣與這京都府界線的吉坂嶺,正好位於正東方。太陽就是從那山嶺升起。明明和現實中的京都反方向,我卻看到山間朝陽中,金閣向著清晨的天空聳立。
如此這般,金閣在各種地方出現,卻無法在現實生活中看見,這點與此地的大海很像。舞鶴灣位於志樂村一里半之處,山巒阻隔看不見海。但這片土地總是瀰漫海的預感。風中有時也帶有海的氣息,海上波濤洶湧時,就會有許多海鷗逃來飛落田間。
我生來體弱,無論賽跑或吊單槓都輸給別人,且天生口吃,令我越發內向自閉。再加上大家都知道我是佛寺的孩子。頑童們模仿口吃和尚誦經來取笑我。說書人講的故事中,有個角色是口吃的捕快,他們每到這種段落就會故意出聲起鬨,非要叫我念經給他們聽。
無庸贅言,口吃在我與外界之間設下一道障礙。我無法順利發出第一個音。那第一個音,就像是我的內在與外界之間的門鑰匙,鑰匙卻無法順利開門。一般人藉著自由操縱語言,內在與外界之間的門始終敞開,可以讓空間通風良好,我卻做不到。因為鑰匙生鏽了。
我的口吃,在急著想發出第一個音之際,也像是拼命掙扎試圖逃離內在的黏鳥膠的小鳥。好不容易掙脫時,已經太遲。外界的現實,在我掙扎之際,有時似乎的確停下手好整以暇地等我。然而等著我的現實已非新鮮的現實。即使我費盡力氣終於抵達外界,外界也總在瞬間變色、錯位……而且只有那個看似適合我的、已失去鮮度半帶腐臭的現實橫亙眼前。
不難想像,這樣的少年對於權力會抱持二種相反的心態。我喜歡歷史上對暴君的記述。我若是口吃又沉默的暴君,臣子想必都得看著我的臉色整天提心吊膽過日子。我根本沒必要用明確流暢的話語將我的殘暴正當化。我的無言,就已將一切殘暴正當化。我平時就是如此幻想著把蔑視我的教師和同學通通處刑,同時也幻想自己成為內在世界的國王,成為沉靜洞察真理的大藝術家。我的外表雖貧窮,但我的內在世界比任何人都富足。懷抱某種自卑感難以釋懷的少年,如此暗自認定自己是天選之人,豈非理所當然?我總覺得這世間某處,正有自己還不知道的使命在等著我。
……我想起這麼一則插曲。
東舞鶴中學有廣闊的操場,被起伏徐緩的群山環繞,是新式的明亮校舍。
五月的某一天,中學畢業後現就讀舞鶴海軍機關學校的某個學生,利用假期回母校玩。
他曬得很黑,壓低的制服帽簷下露出俊挺的鼻樑,從頭到腳儼然是少年英雄。面對我們這些學弟,他大談軍校紀律嚴格的痛苦生活。而且那本該是悲慘的生活,他的語氣卻彷彿在談論極盡奢侈的豪華生活。舉手投足之間洋溢驕傲,年紀輕輕就已了解自己的謙虛有多少分量。他那綴有蛇腹形裝飾線的制服胸口,就像海上乘風破浪的船頭雕像昂然挺起。
他在走下操場的兩三層大谷石台階坐下。周遭有四、五個聽得入神的學弟,五月的各色花卉,包括鬱金香、甜豌豆、歐洲銀蓮花、雛罌粟等盛開在斜坡的花圃。而頭頂上,有日本厚朴綻放大朵白花。
敘述者和聽眾們都如某種紀念雕像文風不動。而我隔著二米距離,獨自坐在操場的長椅。這就是我的禮儀。是我對五月繁花、洋溢驕傲的制服、開朗笑聲的禮儀。
話說這位少年英雄,比起他的崇拜者們,似乎更在意我。只有我看似沒有拜倒在他的威風下,這傷害了他的驕傲。他向眾人詢問我的名字。然後呼喚初次見面的我:
「喂,溝口。」
我保持沉默,認真凝視他。他投向我的笑臉,帶有類似當權者的阿諛。
「你不會回話嗎?你是啞巴嗎?」
「他、他、他、他口吃。」
他的崇拜者之一替我回答,大家都扭著身子笑了。嘲笑是多麼炫目的東西啊。於我,同齡少年那種少年期特有的殘酷笑容,看似光芒璀璨的葉叢閃閃發亮。
「搞了半天是口吃啊。那你要不要來我們海機學校?甚麼口吃的毛病,包你一天就矯正過來。」
我不知怎地,當下突然做出明確的答覆。無關個人意志,話語就這麼在瞬間流暢迸出。
「不要。我要當和尚。」
眾人鴉雀無聲。少年英雄低下頭,摘下身旁的草莖叼在嘴裡。
「是喔,那麼過幾年後,我也要麻煩你了。」
那年太平洋戰爭已爆發。
……當時的我,的確萌生某種自覺。我在黑暗世界張開雙手等待。總有一天,五月繁花、制服、惡意的同學們,都會投入我張開的雙手之中。我自覺已把整個世界拖到底層牢牢抓住。……但這種自覺,要成為少年的驕傲未免過於沉重。
驕傲必須是更輕盈、更明快、清晰可見、燦然生光。我渴望肉眼可見之物。我渴望任誰都看得見,可以成為我的驕傲的那種東西。比方說,他腰上掛的短劍就是。
所有中學生憧憬的短劍,著實是美麗的裝飾。海兵的學生據說都拿那短劍偷偷削鉛筆,但是故意拿如此莊嚴的象徵用於日常瑣碎用途是多麼灑脫帥氣啊!
湊巧他把機關學校的制服脫下,隨手掛在粉刷白漆的欄杆上。還有他的長褲,雪白的內衣也是……那些東西在簇簇花朵旁散發年輕人的汗水味。蜜蜂誤以為是一朵花,停在這潔白發亮的內衣上。綴有金線裝飾的制服帽,就像之前在他頭上一樣,壓得很低地端正掛在某根欄杆上。他受到學弟們挑戰,此刻去後面的土俵玩相撲了。
那些隨手脫下的衣物,給人榮譽之墓的印象。五月數量驚人的繁花,加深了這種印象。尤其是帽簷漆黑反光的制服帽,掛在一旁的皮帶和短劍,徹底與他的肉體分離,反而散發抒情式美感,那本身幾乎等同回憶……換言之,看起來就像少年英雄的遺物。
我確認四下無人。相撲場那邊響起叫喊聲。我從口袋取出生鏽的削鉛筆小刀躡足走近,在那美麗短劍的黑色劍鞘背面,劃下兩三條難看的刀痕。……
……以上的記述,或許令人立刻斷定我是個有詩人氣質的少年。但到今天為止,別說是詩了,我連手記都沒寫過。我本就欠缺用其他能力來彌補不如他人的能力,企圖藉此超越他人的那種衝動。換言之,我太過傲慢以致無法成為藝術家。成為暴君和大藝術家的夢想始終只是夢想,我完全無意實際動手去達成甚麼。
不被人理解成了我唯一的驕傲,因此我沒有萌生那種想讓人理解的表現慾。我認為自己宿命性地未被賦予肉眼可見的特質。唯有孤獨逐漸臃腫肥大,猶如一隻豬。
▋第一章
從小,父親就經常對我提起金閣。
我出生的地方,是舞鶴往東北的日本海伸出的冷清海岬。父親的故鄉不在那裡,在舞鶴東郊的志樂。他在眾人企盼下入了僧籍,成為偏僻海岬的佛寺住持,在當地娶妻,生下我這個孩子。
成生岬的佛寺附近沒有合適的中學。因此之後我離開雙親膝下,寄居父親故鄉的叔父家,從叔父家徒步往返東舞鶴中學上學。
父親的故鄉是陽光普照之地。但一年之中每逢十一月、十二月,即便看似萬里無雲的晴天,一天也會有四、五場陣雨。我易變的心情,或許就是在這種土地養成。
五月的傍晚,放學回來後,我從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