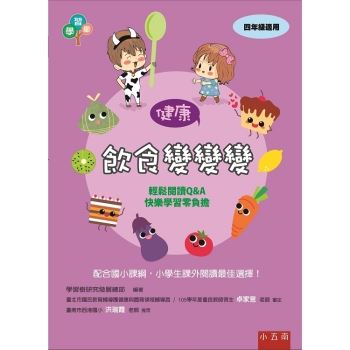大自然不美味了嗎?
不久前,我在脫口秀節目上帶了點東西給眾來賓品嘗:雲杉(Picea abies)與花旗松的樹枝。雲杉是德國最常見的樹種,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花旗松就較鮮為人知:它是北美西海岸的針葉樹種,並在那裡長成了巍峨的參天古木。在過去的幾十年,花旗松被大舉拓植到德國;不過,這當然不是節目的著眼之處。我之所以選擇花旗松的樹枝,是因為它們有著宜人的橘皮味──至少我個人這麼認為。演員阿克西爾.普拉爾(Axel Prahl)與表演藝術家伊爾卡.貝辛(Ilka Bessin)毫不遲疑地咬了一口,隨即面露嫌惡地癟起嘴來:他們完全不喜歡它的味道!這種反應與一般大眾無異。森林的味道主要就是酸味、苦味,以及介於兩者之間的細微變體。我們覺得美味的東西,像是成熟的漿果與堅果,通常都是供不應求,一年之中最多只出產幾個星期。春天的嫩芽新葉起初嘗起來就酸酸的,之後還會變得又酸又苦。樹皮下有透明的形成層,用小刀就能將其剝落,形成層的營養非常豐富,含有糖分與其他碳水化合物,味道有點像紅蘿蔔,但除此之外都是苦味;森林中的食物普遍如此。
我敢肯定,在遙遠的過去,祖先大多數的飲食嘗起來與今日截然不同。因為,如同我們的生活環境,人類的飲食也經歷了某種演化。只有獲得顧客青睞的東西,才能持續擺在商店架上賣。所以生產者會千方百計以最能引誘味蕾的方式去調整自家的產品,他們的方法愈來愈複雜,也愈來愈準確;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很難抗拒某些食物的原因之一。糖、鹽、脂肪,所有的這一切都藉由增味劑加強,所攝取的食物已超過了人體的需求。於是乎,我們日益遺忘天然或未經加工食物的滋味。我指的不是蔬果,因為經由育種,蔬果也朝著類似的方向改變──愈來愈甜,苦味則愈降愈低。相較於大自然的有滋有味,我們或多或少像在吃著某種單調的雜燴,唯有某些味道特別苦或特別酸的異類能脫穎而出,例如咖啡或什錦酸菜(mixed pickles)。
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的舌頭永遠無法被寵壞,抑或是讓舌頭上的味覺中樞、也就是舌乳頭,完全麻木。一個舌乳頭含有一百個味蕾,每個味蕾又含有一百個味覺細胞;這些細胞不是很耐用,每十天就會被更新一次。因此,若在進食中造成某種損害,例如飲用過熱的飲料導致燙傷,舌頭會很快地自我修復。
在舌乳頭為數將近一百的情況下,人類具有將近一萬個味蕾。如果覺得這個數量很多,不妨去比較一下馬的舌頭:大約有三萬五千個味蕾。為何馬需要這麼多的味蕾?草場上生長種類數以百計的草和藥草,其中不乏有毒的草。此外,馬無法看到自己嘴唇正前方的東西──牠們又大又長的頭部擋住了視線。如果在進食時什麼也看不到,那就必須依靠自己的舌頭。為此,必須先將有疑慮的草放入口中,如果不是該吞下肚的草,就得再迅速吐出來。馬很擅於做這樣的事情,我養的兩匹母馬就是這樣:如果藥草的味道不好,就會在咀嚼過程中被優雅地推向口腔邊緣,繼而通過嘴唇退回到曠野之中,觀察這個過程十分有趣。
說到舌頭,它其實並非人類唯一能藉以品嘗味道的部位。且讓我們先回過頭來看看鼻子。迄今為止,已知在食物中約有八千種可聞的揮發性物質。令人訝異的是,這類氣味多半在呼氣時才會被聞到,人類則有四分之三的味覺印象是基於鼻子的感知。想想感冒就知道了:這時食物的味道驟然變得索然無味,頓時失去了所有吃東西的享受。
因此,下回在森林中漫步時,除了透過觀察針葉與樹葉的形狀來探索樹種之間的差異,不妨也像伊爾卡.貝辛和阿克西爾.普拉爾一樣,咬咬看雲杉的樹枝,看看針葉裡究竟藏著哪些味道與香氣,想必會很有意義。
如同前面所說,我們對口腔裡味覺感應器的搜索尚未結束。從字面上來說,幾乎得走到「食物之旅」的盡頭,也就是進入腸道。如同腸道會一起嗅聞,其同樣也會一起品嘗,因為腸道中也有感應器,而且還是一般認為只會出現在鼻子裡的那種感應器。這些細胞不像我們的味覺,很容易受到甜味劑的蒙蔽。為小腸所感受的糖,通常會引發激素的釋放,並會對我們的意識發出「飽足」的信號。然而,甜味劑製品所能觸發的這類信號,卻遠遠弱了許多,於是身體就會要求更多的食物。因此,光是基於這個原因,倘若想減肥,攝取使用代糖的低卡製品並不會特別有效。
現代的化妝品、洗潔劑、薰香蠟燭和諸如此類的其他製品,不僅充斥於我們的口鼻,也充斥於我們的腸道。可是,到底誰會把化妝品、洗潔劑和薰香蠟燭吃下肚?答案很簡單:我們根本不必吃下肚,它們就能透過皮膚或呼吸道進入腸道,甚至到達人體的所有其他角落。這可謂是一支名副其實的「無敵艦隊」,藏身於調味食品中侵襲受體。根據德國聯邦風險評估研究所(Bundesinstitutfur Risikobewertung)的說法,在食品生產中使用的香精約有兩千七百種(主要都是人工製造)。如果把這個數目拿來與自然界中的香精相比,似乎就顯得小巫見大巫;迄今為止,人們已在自然界中發現了將近一萬種的香精。然而,這種純粹的統計數字卻是騙人的。事實上,在日常生活中,只有當中的極少數能觸及我們的感官。畢竟,我們所品嘗的並非世上所有的水果,多半就只是家鄉所出產的水果──至少在全球貿易盛行之前是如此。
如今,我們的腸道充斥著陌生的香精,數量多到令人髮指,這也可能會導致腸道時不時「抓狂」,或是引發各式各樣的疾病;如同前面所說的,根據不同的香精類型,腸道感知到香精後,會觸發某些分泌物的分泌與某些活動的變化。然而,這一切與森林有何關係呢?別著急,因為我們已經針對這個生態系統做好了準備,連同它的氣味與味道,應該都能與之和諧相處。相反地,人工添加物卻會給身體帶來不必要的負擔,這也就是為何,時不時走入森林,並且在森林裡待上一時半會兒,藉以緩解鼻子、嘴巴與腸道的負擔,絕對非常有益。畢竟,人體之所以如此形塑,完完全全是為了適應在森林中湧入感官的一切。如果還能來點低度加工、不含添加物的天然食物當點心,森林浴的效果絕對會加倍。
我們比自己所想的更好
我在前段最後的一些篇幅中指出,我們的感知能力絕對沒有退化,這點非常重要。人類的感官跟許多動物比起來都毫不遜色,只是如同其他所有物種,在我們的特殊需求下趨於完善。這樣看來,人類這種動物其實再正常不過了。儘管如此,為何我們總要貶低自己的感官能力,總是把自己拿來與能力更強的物種比較,而不與那些我們略勝一籌的物種比較?
我覺得,許多疼惜自然的人都殷殷盼望,不要成為這個星球的統治者。關於環境破壞的種種報導,關於氣候變遷的種種末日宣告,都令我們顯得相對其他生物是那麼地高高在上,以至必須打破與生態系統的所有其他居民之間的連結與共同性。這令人感到痛苦,不單單只是因為人類對自然造成的種種影響。
但若果真如此,等於認為人類是這個眾生愚魯且無助的星球上唯一理智的物種。我們每天都被芸芸眾生所圍繞:狗兒和貓咪、小鳥和松鼠、蝴蝶和蒼蠅──牠們都沒那麼聰明,因此受到人類壓迫或滅絕。單單就這種印象本身,就造成了一種排斥感。
無庸置疑,有些物種特別精於某些知覺。舉例來說,相較於我們的雙眼,猛禽的眼睛對細節的解像力高了四倍,讓牠們能從幾公里高的地方一眼就發現老鼠。禿鷹或隼等物種,甚至內建某種的望遠鏡,能擴大牠們的部分視野,促成更精確的遠距觀察。
鯊魚的嗅覺令人難以置信。即使在一比一百億的稀釋度下,仍能聞出魚血。這裡我要澄清一下:儘管有各式各樣的傳言,但這項長處並不適用於人類的血液──我們根本不在鯊魚的獵物清單上,因此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牠們對我們其實完全無動於衷。
我們終究會在所有的物種身上發現某些特殊成就,而每種生物也確實都擁有在所處生態環境中生存所需的某些能力。回歸我們最初的比較,狗需要一個靈敏的鼻子,藉以追蹤獵物,這是牠們的狼祖先所賦予的。有別於人類的世界,在狗的世界裡,眼睛與舌頭的能力無須那麼完善,耳朵的能力則更是如此。牠們完全適應牠們的生活環境,正如我適應了我們的。這也是為何相互比較沒什麼意義,因為如此看來,每個生物所擁有的能力並無優劣之分。
人類的感官仍與數千年前的祖先一樣功能完整,可讓我們仔細感知所處的環境。然而,這個環境並非主要是由書桌、沙發與速食店所組成,而應該是由森林與大草原所組成──至少直到如今仍是如此。針對森林與大草原,我們有著精良的裝備,可以隨時(在經過幾個星期的訓練後)跟上野生動物。
我們始終是一個大型共同體的一部分,配備了出色的感官,讓我們得以充分掌握並品味所處的生活空間。這些感官也讓我們察覺到其他物種的種種能力,從而也增強了我們的同理心和關懷。從古至今人類與自然的連結從未斷裂,只不過是暫時遭到忽略。基於對此共同體的完全歸屬感,種種環保舉措逐漸浮現出另一道截然不同的曙光。
我們不必硬要外出保護自然,也不必放棄接觸自然,只為了保護某些被假定是弱小的甲蟲或鳥類免於滅絕。不,只要採取任何有助於保護地球生態系統的措施,就能同時保我們自己和生活品質,這其實只是因為人類是這個整體中,一個完整的部分。因此,對「保護自然」的最佳詮釋便是:純粹的自我照顧。
|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人類與自然的祕密連結:發掘與自然共生的證據,找回人、動物與植物被遺忘的聯繫與需求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人類與自然的祕密連結:發掘與自然共生的證據,找回人、動物與植物被遺忘的聯繫與需求
★《紐約時報》暢銷作家,《樹的祕密生命》、《動物的內心生活》及《自然的奇妙網路》作者彼得・渥雷本最新力作!
我們本來就在一起、也一直在一起,
我們始終是大型共同體的一部分。
親近自然,是一種健康的本能與需求;
保護自然,是一種純粹的自我照顧。
我們的嗅覺其實跟狗鼻子一樣靈敏?
人類也具有動物那種能預見危險發生的感知能力?
為什麼我們的免疫系統對森林有這麼多正向反應?
樹木跟人一樣聽得見聲音、感覺得到痛?
植物有意識嗎?
德國森林看守人、知名生態作家彼得.渥雷本,
揉和生物學、地球科學等研究與自身長達數十年的觀察,
帶領讀者走進森林,
從植物如何喚醒我們被各種聲光科技、加工食品麻痺的感官知覺、
森林的綠色如何平緩情緒、植物氣息如何穩定血壓、大自然藴藏的各種靈丹妙藥,
到植物是否有脈搏、有沒有意識、有沒有聽覺與痛覺等討論,
讓我們見識到人與自然有著驚人的共同性與相似的能力,
並且以各種方式交織而行,彼此依存、相互扶持。
在相依相伴了三百萬年,長時間交流與適應的過程中,
人類各種感官功能與身體系統,與自然構成緊密相連的共生系統。
即便現代文明科技似乎讓我們與自然間有所隔閡,
但這份連結一直都在,至今完好無損。
透過相關科學證據與條理清晰的論述,
渥雷本將這道幾乎被遺忘的相互作用與不易被察覺的默契,
清楚展示在我們眼前。
人類並非萬物之靈,
而是如同其他所有的物種,
只是複雜精緻的地球生態系統的一部分,
我們也是按照和其他所有物種一樣的規則在運行。
唯有當我們理解到,保護自然不單只是攸關其他的物種,
更重要的是攸關我們這個物種自身,
我們緊密連結、沒有界線、休戚與共,
在完全歸屬的感覺下,保護自然才能發揮作用。
【好評推薦】
植物生態與人文作家│胖胖樹 王瑞閔
作家│王盛弘
荒野保護協會前理事長、暢銷書作家│李偉文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副教授、傅爾布萊特哈佛公衛學院訪問學者│余家斌
國際珍古德教育及保育協會中華民國總會理事長│金恆鑣
(依姓氏筆畫順序)
作者簡介:
彼得・渥雷本(Peter Wohlleben)
1964年生於德國波昂,從小便立志成為大自然的守護者。從內卡河邊羅騰堡(Rottenburg am Neckar)應用科技大學林業經濟系畢業之後,在萊茵法爾茲邦(Rheinland-Pfalz)森林管理局擔任公務員長達二十年之久。如今他在故鄉埃菲爾創辦森林學院,並於世界各地致力推動森林復育。他是許多電視節目的來賓,經常受邀前往各地演說或授課,同時也是專注於森林暨自然保護的主題的知名作家。
他以林野及自然保育主題授課及寫作,其著作已翻成三十多國語言,更以《樹的祕密生命》、《動物的內心生活》與《自然的奇妙網路》三部著作撼動了全球人心。他於2019年獲頒德國環境與自然保護聯盟的「巴伐利亞自然保護獎」,表彰其對於生態保育充滿感情且不落俗套的知識傳播。
譯者簡介:
王榮輝
曾就讀東吳大學政治系、政治大學歷史系與法律系。其後前往德國哥廷根大學(Universitat Gottingen)攻讀碩士,主修哲學、西洋中古史與西洋近現代史。通曉英、德、法、日與拉丁文等外文。2009年起,擔任台北歌德學院特約翻譯。
章節試閱
大自然不美味了嗎?
不久前,我在脫口秀節目上帶了點東西給眾來賓品嘗:雲杉(Picea abies)與花旗松的樹枝。雲杉是德國最常見的樹種,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花旗松就較鮮為人知:它是北美西海岸的針葉樹種,並在那裡長成了巍峨的參天古木。在過去的幾十年,花旗松被大舉拓植到德國;不過,這當然不是節目的著眼之處。我之所以選擇花旗松的樹枝,是因為它們有著宜人的橘皮味──至少我個人這麼認為。演員阿克西爾.普拉爾(Axel Prahl)與表演藝術家伊爾卡.貝辛(Ilka Bessin)毫不遲疑地咬了一口,隨即面露嫌惡地癟起嘴來:他們完全不...
不久前,我在脫口秀節目上帶了點東西給眾來賓品嘗:雲杉(Picea abies)與花旗松的樹枝。雲杉是德國最常見的樹種,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花旗松就較鮮為人知:它是北美西海岸的針葉樹種,並在那裡長成了巍峨的參天古木。在過去的幾十年,花旗松被大舉拓植到德國;不過,這當然不是節目的著眼之處。我之所以選擇花旗松的樹枝,是因為它們有著宜人的橘皮味──至少我個人這麼認為。演員阿克西爾.普拉爾(Axel Prahl)與表演藝術家伊爾卡.貝辛(Ilka Bessin)毫不遲疑地咬了一口,隨即面露嫌惡地癟起嘴來:他們完全不...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前言
近幾年來,許多國家都逐漸浮現出一股對自然生活的復興:森林浴搖身一變,成為療法的一種,在日本還能以此開立診療單;與此同時,人們益發肆意砍伐森林,使氣候變遷更形加劇。置身於所有這些矛盾之中,實在難以找回自己在自然中的一席之地;即便沒有人會蓄意破壞環境,我們的日常生活卻深陷消費主義的牢籠無法自拔。
值此關頭,歸咎罪責與悲觀預言恐怕都無濟於事。一味把世界末日抬出來,恐嚇大家一旦越過此臨界點,氣候就再也無法恢復正常;這只會令人想到昔日的宗教裁判所,與目前亟需的正向動機背道而馳。
與其如此,不妨隨...
近幾年來,許多國家都逐漸浮現出一股對自然生活的復興:森林浴搖身一變,成為療法的一種,在日本還能以此開立診療單;與此同時,人們益發肆意砍伐森林,使氣候變遷更形加劇。置身於所有這些矛盾之中,實在難以找回自己在自然中的一席之地;即便沒有人會蓄意破壞環境,我們的日常生活卻深陷消費主義的牢籠無法自拔。
值此關頭,歸咎罪責與悲觀預言恐怕都無濟於事。一味把世界末日抬出來,恐嚇大家一旦越過此臨界點,氣候就再也無法恢復正常;這只會令人想到昔日的宗教裁判所,與目前亟需的正向動機背道而馳。
與其如此,不妨隨...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前言
1.森林為什麼是綠色的?
2.自然中的聽覺訓練
3.腸道是延伸的鼻子
4.大自然不美為了嗎?
5.觸摸有助思考
6.第六感訓練
7.野豬──森林裡的大白鯊
8.我們比自己所想的更好
9.與樹木親密接觸
10.一切都是從火開始的
11.帶電的樹
12.樹木也有心跳?
13.蚯蚓旅行去
14.受膜拜的樹
15.動植物的界線正在崩落
16.森林的語言
17.森林浴──深深沉浸吧
18.自然藥局的急救箱
19.樹也要看醫生?
20.嚮往理想世界的本能
21.向孩子學習
22.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23.鄉村生活──城市生活悖論
24.樹木也時尚
25.歸路艱難
...
1.森林為什麼是綠色的?
2.自然中的聽覺訓練
3.腸道是延伸的鼻子
4.大自然不美為了嗎?
5.觸摸有助思考
6.第六感訓練
7.野豬──森林裡的大白鯊
8.我們比自己所想的更好
9.與樹木親密接觸
10.一切都是從火開始的
11.帶電的樹
12.樹木也有心跳?
13.蚯蚓旅行去
14.受膜拜的樹
15.動植物的界線正在崩落
16.森林的語言
17.森林浴──深深沉浸吧
18.自然藥局的急救箱
19.樹也要看醫生?
20.嚮往理想世界的本能
21.向孩子學習
22.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23.鄉村生活──城市生活悖論
24.樹木也時尚
25.歸路艱難
...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