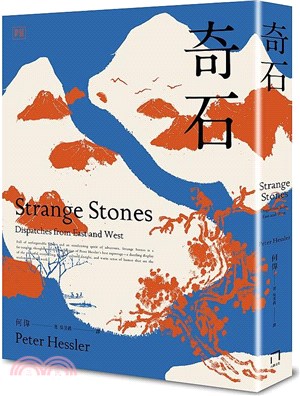《時代雜誌》評價:「最好的長篇報導!」
★
在中國城鄉與美國西部之間縱情遊走,不變的是犀利細膩的人情觀察
當今非虛構類寫作的最佳範本
何偉繼「中國三部曲」,精選改寫發表在《紐約客》的深度報導
======================
當中國在上個世紀的九零年代高速發展後,書寫中國本身乃至於這個國家對世界的意義,變成了一件十分具有挑戰性的事情。何偉──來自美國的青年,以十年時間記錄底層社會的適應與衝擊;這些專屬中國偏鄉與底層人民的故事,最後成就了非虛構寫作經典「中國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尋路中國》。而《奇石》有如番外篇,以更寬廣的視野縱情記錄何偉生活在中國與美國兩地時的靈光之念;它也是三部曲人事地物後續發展的追蹤,同時詳細留下何偉書寫背後的心路歷程。
「中國就像是顆奇形怪狀的石頭,每個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樣子。
想接近真正的中國,唯一方法就是在中國長時間生活。」──何偉
何偉是如何開始學會觀察人群?他的第一篇中國紀實之作寫了什麼?那些出現在《尋路中國》、《甲骨文》書中的有趣旁線人物,他們完整的生命故事為何?《江城》的三峽大壩之水淹沒城市時,呈現出何種景象?何偉隨和平工作團到達中國時獨自一人,後來舉家搬遷回到美國中西部寫作,這過程中有多少同伴?發生了什麼趣事?在本書皆有生動呈現。
何偉在他旅途中所隨手撿拾的奇石,有的粗糙刮人,有的光滑潤手,有的圖案繁密,有的簡單純色,鼓脹的口袋裝滿了他沿途收來的石頭。人生無非一趟漫遊之旅,何偉不斷逼促自己向前踏往未知,《奇石》則是其與中國社會正面碰撞十年的精華總結,他一次又一次地用幽默生動的真實故事,寫出中國處於變化中的奇特面貌,恰如其分地表現出中國的各種多樣面。
「非虛構寫作的樂趣就是尋找說故事和報導之間的平衡點,
找出一個能夠兼顧暢所欲言和觀察入微的方式。」──何偉
何偉熱愛描寫不斷遷移的人物,喜歡那些覺得自己和環境有點格格不入的人物,深深被不斷在尋求和逃避的移民及移居者所吸引。如他所說,有些人不斷在改變,有些人夢想著返鄉,還有一些人以各種方式展現「創造性的笨手笨腳」。然而,何偉與這些人的交談總是橫生趣味,因為他們學會了以外人眼光來看自己的環境;同樣地,何偉在書寫中總是帶有本地居民以及外國觀察者的雙重眼光,讓他除了能生動描寫人物面貌與地方的特殊環境,還增添了許多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聞趣事。
本書收錄的文章寫於二○○○年至二○一二年,閱讀本書,將是認識何偉這個人和他如何進行「非虛構類寫作」的最好途徑。無論中國或世界,只要在何偉筆下,你就讀得到跟奇石一樣題材另類、視角多維的故事。
好評推薦
「何偉的作品平靜而充滿自信,以絕妙的語調和姿態賦予他所描繪的時刻生命。他知道何時應該參與行動,何時應該等待事情發生。」
──史景遷,《紐約時報》書評
「讀這本書……這些是最好的長篇報導。」
──法里德.札卡利亞(Fareed Zakaria),《時代雜誌》(Time)
「敏銳地觀察發人深省的細節,是個動人的說故事高手。」
──《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
「何偉的筆觸是一種細微而幽默的第一人稱,輕易地引領讀者走過那些曾幾何時充滿情調但又平凡的地方。……他有一種能準確且大範圍描寫人物的天賦」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本書充滿啟示……精采絕倫……持續呈現何偉講述故事的天賦,這些故事是用幽默與深有同感的方式相互理解彼此的文化差異。何偉是真實故事的人性訴說者,一個敏銳的觀察者,一個作家。」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一部易於親近、充滿人性且具有覺察能力的作品……這並不是教會你世界經濟或地緣政治的那種通用書,《奇石》的閱讀趣味極高,文筆流暢的同時卻充滿見識。」
──《明星論壇報》(The Minneapolis Star Tribune)
======================
◎當代非虛構寫作的最佳範本,何偉「中國三部曲」系列——
《江城》(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
在幽緩的時光流程中,在變動劇烈的城鄉景觀內外,
何偉依江而居,感受與學生和涪陵人相處的日常點滴,
書寫出一部連中國人自己都未能體察的心態史和底層故事。
──何偉非虛構書寫的發源地,「中國三部曲」的最初起點!
《甲骨文》(Oracle Bones: A Journey Through Time In China)
如何評價九○年代的中國?
何偉以親訪實證、考古調查為經緯,再以西方記者的筆法布局出恢弘格局。
他讓人物來口證中國變化、讓古物來見證歷史滄桑。
──今日中國似乎就是為了何偉的寫作而存在!
《尋路中國》(Country Driving: A Journey Through China from Farm to Factory)
在一個人人奔走於途,卻又不知自己將走向何方的躁動國度裡,
何偉用帶著人性暖意的目光,記錄中國各個角落裡的人生悲歡百態。
構築出平凡小民在現代中國經濟快速起飛、社會急遽變動時代下的處境。
──何偉就像是當代的馬可波羅,徹底顛覆你對轉型中國的想像!
《奇石》(Strange Stones: Dispatches from East and West)
想接近真正中國,唯一方法是在中國長時間生活。
只要在何偉筆下,你就讀得到奇形怪狀的中國。
──繼「中國三部曲」,精選改寫《紐約客》的深度報導!
作者簡介:
何偉(Peter Hessler)
生於密蘇里州哥倫比亞市,於普林斯頓大學主修英文和寫作,牛津大學英國文學碩士。何偉自二○○○年至二○○七年間曾擔任《紐約客》駐北京記者,同時也是《國家地理雜誌》、《華爾街日報》與《紐約時報》的長期撰稿人。二○一一年至二○一六年擔任駐開羅記者,為《紐約客》撰寫中東報導。二○一九年舉家遷往中國四川,並於四川大學匹茲堡學院授課。
何偉最膾炙人口的作品為「中國三部曲」:《江城》(River Town)曾獲Kiriyama環太平洋圖書獎,《甲骨文》(Oracle Bones)入選二○○六年美國國家圖書獎,《尋路中國》(Country Driving)獲選《紐約時報書評》百大書籍;此系列與專欄合集《奇石》(Strange Stones)成為中國觀察與非虛構寫作的必讀書單。另著有《埃及的革命考古學》(The Buried),為他派駐開羅時的政治與社會觀察。
二○○八年,何偉因卓越的報導而獲得美國國家雜誌獎;二○一一年,何偉以其筆下「敏銳觀察中國平凡百姓如何應對改革時代社會快速變遷的複雜生活」之紀錄,再獲麥克阿瑟基金會(MacArthur Foundation)表彰。
譯者簡介:
吳美真
雲林虎尾人,政治大學西洋文學系畢業、紐約大學英美文學博士肄業,曾任大學兼任英文講師,目前為專業譯者。譯有《野草: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沙郡年記》、《星星、雪、火》、《微物之神》、《孤獨及其所創造的》、《大洋洲的逍遙列》、《汀克溪畔的朝聖者》等書。
章節試閱
〈胡同因緣〉
過去五年,我住在北京商業區一條小胡同的一棟公寓樓房裡,那地方位於紫禁城以北約一英里。我居住的這條胡同沒有正式名稱,始於西,經過三個九十度轉彎,然後朝南而去。從地圖上看來,它的形狀奇特,有點像問號,或半個佛教的萬字符號,而它還有一個特點:位於老北京少數倖存區域的其中一個區域。和今日中國所有的城市一樣,首都北京瞬息萬變,因此,為了跟上發展的腳步,當地最大的地圖出版社每隔三個月,就得更新一次北京地圖。然而幾百年來,我居住的這個社區的佈局大致沒變。第一張詳盡的北京地圖於一七五○年完成,正值偉大的清朝乾隆皇帝統治中國之時,而在這張地圖上,這條胡同的路線和今日一模一樣。北京考古學家徐蘋芳告訴我,我居住的這條街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紀,當時,北京諸多區域原先都是在元朝統治下規劃出來的。而元朝也留下了「胡同」二字,這是一種蒙古語,但是在漢語裡,這兩個字被拿來表示「巷弄」。當地人稱我的巷弄為「小菊兒」,因為它連接一條較大的「菊兒胡同」。
我住在一棟現代的三層樓房裡,但是樓房四周盡是磚塊、木頭和瓦片蓋成的平房,而這正是胡同的特色。這些建築物立在灰色的磚牆後,以致來到老北京的訪客往往有一種分隔的印象:牆跟著牆,灰磚連接著灰磚。然而事實上,胡同社區的一大特色就是聯絡和活動。也許有許多家庭共用一個入口,而雖然舊住宅有自來水,卻很少有私人浴室,因此,公廁在當地生活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在胡同裡,許多東西都是共用的,包括胡同本身。即使在冬天,居民也會裹著厚厚的衣服,坐在路邊和鄰居聊天。街頭小販經常穿梭於此,因為胡同太小,無法建造超市。
這兒車輛稀少。和我居住的胡同一樣,一些胡同太窄,汽車無法通行,而日常生活的聲音,完全不同於你想像中一個住著七百萬人口的城市中心該有的聲音。通常我天亮即醒,而當我坐在書桌旁,我可以聽見居民邊拿著夜壺前往這棟樓房隔壁的公廁,邊和鄰居寒暄。到了八、九點,小販傾巢而出,踩著三輪車往來於胡同,各各都以自己的招牌吆喝聲叫賣產品。賣啤酒的婦人嗓門最大,一遍又一遍喊著:「買─啤─酒──!」早上八點鐘,這種叫聲令人分心,但是幾年來,我已學會欣賞其中的音樂。賣米小販的叫賣聲較尖銳,賣醋的較低沉,而磨刀的祭出打擊樂器,不斷以金屬板製造喀噠聲。這些聲響具有撫慰人心的效果,讓我想到即使足不出戶,生活儘管失衡,但仍然可以持續。我依然會有烹飪油、醬油,以及當令的蔬菜和水果。冬天到了,我可以買一串串的大蒜。一個賣衛生紙的小販天天踩著三輪車經過,而煤也不缺,偶爾我也可以吃吃冰糖葫蘆。
我甚至可從收破爛的那兒賺幾塊錢。在平日,每隔半小時就有一個收破爛的踩著平板三輪車經過,要買紙箱、紙、保麗龍,以及破損的家用電器。他們按公斤買舊書,按平方英寸買壞掉的電視。電器可以修理或拆成零件,而紙和塑膠會賣給回收中心,賺取薄利,賺取微不足道的利潤。不久前,我把一些沒用的家當堆在公寓門口,然後邀請每一位經過的收破爛的進來,看看這些東西可以賣多少錢。結果我的一疊舊雜誌賣了六毛二,一條燒壞的電腦線賣了五分,兩盞破損的臺燈共賣了七分,一雙破皮鞋賣了一毛二,兩個壞掉的掌上型電腦(Palm Pilots)賣了兩塊三毛七。我一直在寫一本書,而我把修改過的這本書的手稿賣給一個收破爛的,他秤了重,然後給我一毛五。
四月底的一天,我坐在書桌旁,忽然聽到有人叫喊著:「長—頭—髮!長—頭—髮!」那是一種新的吆喝聲,於是我去到胡同查看究竟,而我發現一個男人已經將三輪車停在那兒。那人來自河南,他為那地方一間生產假髮和接髮的工廠工作。我向他打聽生意,而他將手伸入一只粗麻袋,然後取出一條長長的黑色馬尾。他說那是他以相當於十塊美金的價錢,向另一個胡同居民買來的。
他來北京是因為天氣暖了,是剪頭髮的時候了,而他希望回河南之前,能夠買到一百磅重的好頭髮。他說最後,大多數的頭髮都外銷到美國或日本。
我們交談時,一名婦人匆匆自隔壁房子出來,手裡拿著紫色絲帕包裹的東西。她小心翼翼打開絲帕,裡頭有兩束厚厚的頭髮。
「我閨女的頭髮,」她說,並解釋那是她女兒上回剪髮時,她留下來的。
絲帕裡的每一束馬尾約有八英寸長,而那人拿起一束,讓它懸在那兒,像釣線上的魚。他眯起眼睛評估一番,然後說:「太短了。」
「什麼意思?」
「對我沒用處,」他說:「得長些才行。」
婦人嘗試和他商量,但沒用,最後就拿著頭髮回家了。當那人離開時,他的吆喝聲在胡同迴響:「長—頭—髮!長—頭—髮!」
──
我搬入「小菊兒」後不久,北京加速展開申辦二○○八年奧運會的活動,而奧運光環的蛛絲馬跡開始顯現在胡同。為了推廣體育活動,並改善北京市民的健康,政府建造了數百個戶外健身處。上了漆的鋼鐵設施出自政府的一番好意,但顯得十分怪異,彷彿設計者匆匆朝一間健身房瞄一眼,然後憑記憶設計出那些東西。在健身處,市民可以以手轉動巨輪,可以推動沒有阻力的大槓桿,或蕩搖錘,像公園的孩子。在大北京地區,這類健身處隨處可見,甚至長城邊的小農村也有它們的蹤跡,在那兒,這類設施讓農民可以選擇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一天辛辛苦苦花十二小時採收胡桃後,他們可以藉著不斷轉動巨大的黃色輪子來維持健康。
然而,沒有人比胡同居民更加感激這類健身設施。健身器材散佈在舊城區,塞入狹窄的胡同裡。黎明和黃昏,它們尤其忙碌,老人群聚閒聊,並蕩幾圈搖錘。在溫暖的夜晚,男人悠閒地坐在器材上吞雲吐霧。胡同裡最主要的消遣,就是和左鄰右舍在街巷閒蕩,而健身站正是提供這種消遣的好地方。
二○○○年年末,全北京市一項奧運前的運動,就是改善衛生設施,為此,政府在菊兒胡同入口興建公廁。這項改變十分戲劇化,就彷彿一道亮光,從奧林帕斯山直接臨照胡同,促成了一間了不起的建築物的誕生。這間建築物有自來水、紅外線自動沖水馬桶,以及中文、英文和點字告示牌,此外,它的灰色屋瓦讓人想起傳統的胡同建築。公廁的不銹鋼板列著詳盡的使用規則,例如:「3:每一位使用者可以使用一張免費普通草紙(長八十釐米,寬十釐米)。」一對夫妻住在一間小房間裡,他們是公廁的全職管理員。政府明白,沒有一位自重的北京市民願意在公廁工作,所以他們特地從內地招來許多對夫妻。這些人多半來自貧窮的安徽省,而工作分配的原則十分合理:丈夫打掃男廁,妻子打掃女廁。
菊兒胡同的這對夫妻也把他們的幼兒帶來了,而他就在公廁前開始學走路。這種場景出現在首都各地,或許有一天,這些孩子會變成北京版的「午夜之子」。一個世代的學步幼兒在公廁長大,奧運後十年,他們將成年,並為祖國貢獻衛生上的光榮成就。在這期間,菊兒胡同的居民盡情利用新公廁前受到細心呵護的公共空間。當地修理自行車的老楊在那兒存放工具,以及多出來的自行車。秋天時,包心菜小販就睡在廁所旁的那塊草地上。隔壁煙店的老闆王兆新在廁所入口旁放了幾張破沙發,還有人帶來棋盤。然後,折疊椅出現了,擺滿啤酒杯的木頭櫥櫃也擺在那兒了。
過了一段時間,由於這地方堆滿傢俱,而許多人每晚來報到,因此,王兆新宣佈「W.C.俱樂部」成立了,而且人人都可加入,雖然誰來當主席或政治局委員仍有爭議。由於我是外國人,我加入「少年先鋒隊」的層級。週末夜晚,俱樂部在廁所前舉行烤肉,王兆新供應香煙、啤酒和白酒,而新華社的司機曹先生把報紙上的新聞拿來品頭論足一番。燒炭烤架由一位姓楚的殘障人士照料,由於行動不便,此人取得駕駛小型機動車的許可證,因此,他可以輕易穿過胡同,將羊肉串運來。二○○二年夏天,中國男子足球隊打破紀錄,首次踢進世界盃,所以W.C.俱樂部弄來一部電視,將插頭插入廁所,然後毫不留情地把他們的國家隊嘲弄一番,因為在世界盃期間,他們沒有踢進一球。
──
王兆新婉拒主席頭銜,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最佳人選,因為在這裡,就屬他經歷最多社區的變化。一九五一年,即共產黨取得中國政權後兩年,他的父母搬進菊兒胡同。當時,北京十五世紀初期的佈局依舊完好如初,在世界主要的首都中,這座幾乎未受現代化或戰爭波及的古老城市顯得獨樹一幟。
北京曾有一千多間廟宇和寺院,但幾乎全被共產黨解散,或改作其他用途。在菊兒胡同,和尚被趕出一間叫圓通寺的喇嘛廟,然後,許多家庭搬入廟裡,包括王兆新的父母。在此期間,共產黨鼓勵其他無產階級成員佔領富人宅第。早先,這類私人胡同住宅建造在寬敞的露天庭院周圍,但是在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這些院落多半擠滿簡陋棚屋,或臨時搭建的建築物。先前一個家族居住的四合院,可能變成二十幾個家庭的住處,而北京人口因為不斷有新來者湧入而持續膨脹。接下來的二十年,北京重要的城門多半遭到共產黨拆毀,氣派的城牆(某些地方高達四十英尺)也是如此。一九六六年,王兆新還是一個六歲大的小學生,卻已加入兒童自願工作隊,而這個工作隊協助拆毀一部分離菊兒胡同不遠的明朝城牆。一九六九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政府為了興建地鐵站,而拆除附近的安定門。到了毛澤東於一九七六年過世時,老北京大約有五分之一已被摧毀殆盡。
一九八七年,王兆新的弟弟在北京麵廠找到了第一份工作,然而不到幾個月,這個十八歲的年輕人就被和麵機絞斷了右臂。之前不久,王兆新已決定投入零售業,希望在新的市場經濟中,躋身成功行列。弟弟出事後,當他選擇商品,他必須考量弟弟的殘廢。他認為水果和蔬菜太重,而賣衣服得用兩手幫忙顧客看看衣服是否合身,也得用兩手折衣服。但是,香煙很輕,所以王氏兄弟選擇賣香煙。
一九九○年代和二○○○年代初期,當王氏兄弟在菊兒胡同賣香煙,房地產開發商賣掉了大部份的老北京。城市受到保護的地區寥寥可數,而部分原因就是地方政府部門從房地產開發中吃到甜頭。每當一條胡同的命運被決定了,其上的建築物就會貼上一個加了圓圈的偌大「拆」字,就像無政府主義者在塗鴉中塗上英文字母A一樣。
當房地產開發商橫行北京,這個字變成一種驅邪物——北京的藝術家拿它的形狀進行引人發噱的創造,而北京居民開起「拆」的玩笑。在W.C.俱樂部,王兆新曾說:「我們住在『拆』那兒。」這句話的最後三個字聽起來像中國的英文China。
和我認識的許多北京市民一樣,王兆新務實、脾氣好、不濫情,而他的慷慨眾所皆知,左鄰右舍都叫他「王老善」。W.C.俱樂部舉行烤肉時,他總是大方付出,也總是最後離開。他曾說,政府遲早要繼續拆這兒的房子,但他不會滿腦子想著未來。在「『拆』那兒」住了四十多年讓他明白一件事:沒有一樣東西是持久的。
──
(中略)王老善有關「『拆』那兒」的預言應驗了。幾年來,他預言政府會來拆房子。二○○五年九月,政府終於判定他那棟公寓大樓必須拆除,而他不吭一聲就搬出去了。他已經賣掉煙店,因為利潤過低,而現在,沒有人會懷疑誰是真正的主席,因為他才離開胡同,W.C.俱樂部就樹倒猢猻散了。
那時候,老北京的四分之三已經遭到拆除,剩下的四分之一主要是公園和紫禁城。過去幾年,不少人抗議這種破壞,並打官司,而這類爭論往往只是局部性的:居民抱怨因為政府腐敗,他們得到的補償減少了,而他們也不喜歡遷往太遠的郊區。然而,北京人很少針對北京城面臨的整體問題表達關注。
很少人談到建築物的保存,也許這是因為中國人的過去觀和建築物沒有什麼關聯,這一點和西方不同。中國人很少拿石頭來蓋房子,所以過去幾個世紀,他們每隔一段時間,就得換掉容易腐朽的建材。
胡同的本質主要在於精神,而不在於建築物。重要的不是磚塊、屋瓦和木頭,而是居民和環境互動的方式,而這個環境一直在改變,製造了王老善這類務實、足智多謀、能屈能伸的居民。這樣的人沒有理由因為現代化的第一次入侵而受到威脅;恰恰相反,這種情況往往能夠激發胡同精神,因為居民總是立即找到創意十足的方式,將麥當勞或奧運公廁融入日常生活之中。然而,當入侵變成全面破壞時,這種韌性也可能讓人變得消極,而這就是老北京的一個諷刺:最迷人的胡同特質,反而促成了胡同的毀滅。
二○○五年,北京政府終於制定新計畫,來保護仍然殘留在商業區北部和西部的幾個零散的舊區,包括菊兒胡同。異於以往,這些胡同不會放在市場上供房地產開發商隨意大興土木。政府宣佈的優先事項是「保存老城風貌」,而政府也設立一個十人諮詢委員會,遇到重大計畫,就會徵求他們的意見。諮詢委員會的委員包括建築師、考古學家,以及城市規劃專家,其中部分委員曾公開批評政府大肆破壞北京城。一位委員告訴我,基本上,這些措施來得太晚了,但是這項新計畫至少應該保存少數倖存胡同的基本佈局。然而,在這個佈局內,改建破敗的地區已經勢在必行——胡同已經變得十分珍貴,所以現在,它們在新的經濟體系中獲得了認可。
我居住的這個社區變化之快令人眼花繚亂。二○○四年,酒吧、咖啡館和服飾店開始湧入南鑼鼓巷。這條巷弄是一條安靜的街,和菊兒胡同交叉。如果有人提出好價錢,當地人樂意放棄自己的家,而這裡的商店保持傳統建築風格,但也讓老城區顯得更加高級和世故。現在,如果我只能在這個社區活動,我可以使用無線上網,可以買到民間手工藝品,也可以買到你想得到的各種混合飲料。這條胡同有美甲店,也有紋身館。街頭小販和收破爛的仍然十分活躍,但已經有一群群帶領遊客參觀胡同的三輪車夫加入他們的行列,而大多數的遊客都是中國人。
最近一個週末,王老善回來看我,而我們一起走過菊兒胡同。他讓我看看他出生的地方。「我們就住在那兒,」他說,並指著菊兒園飯店的現代四合院。「以前那是寺廟。我父母搬進來時,廟裡還住著一位喇嘛。」
我們繼續朝東行進,經過一扇懸在胡同高牆、高出街道三英尺的古老紅門。「以前那兒有樓梯,」他解釋:「我小時候,那是大使館。」
十九世紀,這座四合院曾歸一位滿族貴族所有。一九四○年代,蔣介石把它當成北京辦公室。共產黨取得中國政權後,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元老董必武接收這地方。一九六○年代,這座四合院成為南斯拉夫大使館。如今,由於滿族人、國民黨、共產黨和南斯拉夫人都離去了,所以這座四合院恰如其分地被稱為「友誼賓館」。
這就是胡同因緣——地方不斷地改頭換面,權貴總有倒下的一天。幾條街以外,清朝末代皇帝的婉容皇后的娘家,已變成糖尿病診所。而在菊兒胡同,權傾一時的清朝將領榮祿的美麗西式宅第一度變成阿富汗大使館,然後又變成今日的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一幅巨大的米老鼠畫像就掛在門上。
王老善經過奧運公廁(他說:「不像我在時那麼雜亂了。」),然後,我們來到他自一九六九年以來居住的那棟三層樓房,那棟難以形容的樓房。那不是一棟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物,因此,政府批准將它拆除,裡頭的電和暖氣已被切斷。我們爬到樓上,進入一條廢棄的走廊。「那是我剛結婚時所住的房間,」他說,並在一扇門前停下來。「那是一九八七年。」
那一年,他的弟弟失去一條胳臂。我們繼續沿著走廊行進,來到一間公寓,王老善和妻子、女兒、父親及弟弟最近就住在那兒。牆上依然貼著她女兒的畫,包括一張馬的素描,此外還有英文字Merry Christmas(聖誕快樂)。「這是放電視的地方,」他說:「這是我父親睡覺的地方,我弟弟睡那兒。」
搬出去後,這一家人就分散了。現在,他的父親和弟弟住在北邊的一條胡同,而他和妻女暫時住在一位離家的親戚家。政府給王老善一棟破舊建築物的一小部分,作為拆掉他的公寓的補償。那棟建築物位於鼓樓附近,他希望春天時,能夠將它整修一番。
來到外面時,我問他在胡同住了將近半個世紀,會不會捨不得離開。他想了想,然後說:「你知道,我住在這裡時,發生了不少事,也許傷心事還比開心事多呢!」
我們往西走出胡同,途中,我們經過北京千禧商貿有限公司的廣告。那一天回家時,我看到一排三輪車載著中國遊客,他們裹著厚厚的禦寒冬衣,手裡拎著相機,穿梭於古老的街道。
(本文節錄自:「胡同因緣」)
〈胡同因緣〉
過去五年,我住在北京商業區一條小胡同的一棟公寓樓房裡,那地方位於紫禁城以北約一英里。我居住的這條胡同沒有正式名稱,始於西,經過三個九十度轉彎,然後朝南而去。從地圖上看來,它的形狀奇特,有點像問號,或半個佛教的萬字符號,而它還有一個特點:位於老北京少數倖存區域的其中一個區域。和今日中國所有的城市一樣,首都北京瞬息萬變,因此,為了跟上發展的腳步,當地最大的地圖出版社每隔三個月,就得更新一次北京地圖。然而幾百年來,我居住的這個社區的佈局大致沒變。第一張詳盡的北京地圖於一七五○年完成,正...
目錄
│前言
│野味
│胡同因緣
│長城尋訪
│齷齪的遊戲
│海灘高峰會
│大城女孩
│沉入水中
│鈾礦工的寡婦
│奇石
│恕我直言
│長大要做什麼?
│我的四次汽車事故
│國內國外
│地主隊
│汽車城
│中國巴比松畫派
│回到西方
│唐恩醫生
謝詞
│前言
│野味
│胡同因緣
│長城尋訪
│齷齪的遊戲
│海灘高峰會
│大城女孩
│沉入水中
│鈾礦工的寡婦
│奇石
│恕我直言
│長大要做什麼?
│我的四次汽車事故
│國內國外
│地主隊
│汽車城
│中國巴比松畫派
│回到西方
│唐恩醫生
謝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