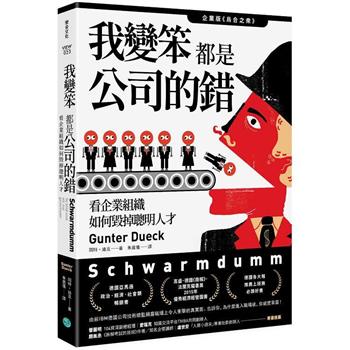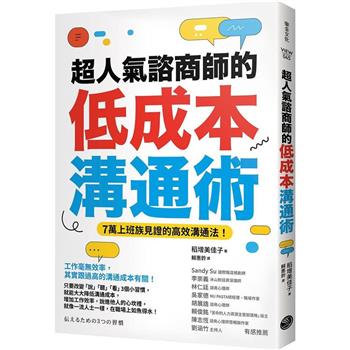第一章【單車之旅】節選
阿姆斯特丹的一天,從我抱著蹣跚學步的兒子出門開始。我把孩子固定在腳踏車把手間的座位上,再想辦法將他穿著運動鞋的短胖小腳放上腳踏墊,接著我們便上路,穿梭在常迎著徐徐微風的安靜社區間。這個區域叫舊南區(Oud Zuid),你只要看看任何一位荷蘭藝術大師的畫作,就能想像我們騎著腳踏車的早晨是何等光景。它帶有一種白色的潔淨,彷彿剛被清洗過的質感。舉個例子,這裡的光線冷靜而清醒,絲毫沒有地中海陽光那種帶著橘色微粒的光芒。這一帶的房屋多為三、四層樓高的磚造建築,全都建於二十世紀的前二十年;當時這是一座活力充沛的勞工階級城市,正從多條運河匯聚的市中心迅速向外擴張,空氣中仍飄著鯡魚和烘咖啡豆的氣味。
我們騎車經過公寓大樓的一樓,其中有些公寓中間有一扇窗戶未裝窗簾,我總認為這項荷蘭傳統與他們那根深柢固、追求開放的態度有關。這種窗戶讓人從外頭就可一覽無遺地看見客廳,彷彿屋內住戶認為自己的生活值得在博物館展示。當我們騎車來到一條運河邊,兒子會爆出一連串的尖叫聲,我有一陣子不曉得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後來才發覺,安東尼是在模仿海鷗叫聲──牠們在水面上瘋狂地飛翔俯衝。
我們會騎經幾家商店,經過某家麵包店時,早晨的空氣通常瀰漫著肉桂香。角落的單車店櫥窗內展示著堅固耀眼的新款單車,最近看到的是荷蘭皇家(Gazelle)和巴塔佛斯(Batavus)的一系列淺色車款;這兩家廠商生產荷蘭腳踏車已長達一世紀。櫥窗右邊一道敞開的門能通往位在地下室的修車廠,我對裡面瞭若指掌。下樓的樓梯兩側設有混凝土溝槽,是供腳踏車輪胎使用的。
偶爾我會變換路線,拐入賀伯瑪堤道(Hobbemakade),此時右邊是一段看來略顯荒涼的運河,雜草一路長到搖晃船屋停靠的碼頭,左邊則是一個殘存的紅燈區,堪稱是阿姆斯特丹數個紅燈區當中最小、最不受注意的一個。阿姆斯特丹的中央紅燈區(De Wallen)可說是另類的迪士尼樂園,嘈雜中帶著某種破舊髒亂的歡樂氣氛,除了喝醉的男性觀光客之外,手挽著手漫步的情侶,甚或家庭,都會到那裡逛逛。相形之下,這裡只有三、四個櫥窗,領有市府核發執照的性工作者就坐當中展示自己,而前面是一條住宅區街道。我始終想不透顧客要怎麼找到她們。然而,即使在早上通常也至少有一位女子值班,身穿泳裝坐在凳子上,邊抽著菸,或是無精打采地滑著手機。她有時會對安東尼揮揮手,朝他微笑。另一個櫥窗可能是空的,放著一張凳子,椅凳上有一條摺著的皺毛巾,像是有人坐過。皺毛巾、性工作者除了偶爾跟陌生人短暫性交易之外,整天盯著街道露出的無聊表情──這些小細節讓這座城市包容賣淫的狼籍名聲脫離了情色感官與理想主義的範疇,進入極為世俗的領域。跟其他任何地方一樣,在這裡住上一段時間後,再奇特的事物也會變得平淡無奇。再過去兩間是另一個店面,那是一家廣告公司,它的公司名稱「Strangelove」(奇愛)可能會讓人以為是在刻意嘲諷鄰居,但我認為根本不是,我敢說他們根本沒注意到隔壁在做什麼生意。
阿姆斯特丹學派(Amsterdam School)這種建築風格,最初正出現在我住的這個區域。此風格擁有正規的美學標準,包括其技術符碼和以社會主義為主的哲學基礎,但對我來說,它就是一種適度結合奇異與冷漠的討喜組合。雖然其媒介是磚塊(還有什麼比磚塊更冷漠的?),但卻產生出無窮的趣味變化:宛如塔樓的圓角;裝飾藝術風格的嵌入雕像,似乎在嘲笑這種材料的堅硬度(一個女孩身邊圍繞著兔子,嬰兒支撐起一個門廊);長達一個街區的公寓大樓,靈感可能源自遠洋客輪或結婚蛋糕。
從運河帶和阿姆斯特丹馳名的十七世紀市中心騎腳踏車來到這個區域,頂多耗時五分鐘。不過,百年前開發者在規劃時,肯定認為有必要將這個新興區域與這座城市的歷史連結起來。如果畫家林布蘭造訪緊鄰我家這一帶,可能會覺得有些熟悉,因為這地方雖然在他那時代仍是一片沼澤田野,但如今街道名稱大都採用許多曾在他工作室裡接受指導、或與他競逐繪畫委託權的畫家的姓名:佛蘭斯‧范‧米里斯(Frans van Mieris)擅長為富裕階級繪製精緻的小型肖像畫;尼古拉斯‧馬斯(Nicolaas Maes)筆下常出現禱告或用餐中的老百姓,除了特別強調人物臉孔,他同樣注重桌上發亮的麵包或陶壺;菲力普斯‧佛飛曼(Philips Wouwerman)專門畫狩獵場景,以描繪難以駕馭的馬匹聞名。
在我住的區域成形時,這些人都已是輝煌歷史上的人物,因此尼古拉斯‧馬斯街與佛蘭斯‧范‧米里斯街的名字立刻為這個新區域賦予了阿姆斯特丹黃金年代的光芒──那個短暫、卻出人意料地成為全世界最大城市的年代。時至今日,這些街道上的房屋依然尊貴高雅。不過,當你像我們晨間之旅的路線一樣遠離市中心之後,路上的房屋就益見平凡樸素。一個世紀前,這座城市的規劃者似乎不想讓它聲名遠揚,以免削弱了黃金年代的顯赫光輝。另一方面,一九○五年,也就是這個區域較偏遠的地方正進行規劃之際,附近的市立現代美術館(Stedelijk Museum)正展出全荷蘭首度的梵谷特展。這位荷蘭畫家於一八九○年辭世,他的故鄉過去對他完全漠視,但此時他們顯然不得不對他另眼相看。但此時他的名字在中產階級眼中依然無足輕重,誰都沒料到那些濃烈的鮮豔漩渦竟然禁得起時間的考驗。我認為正是因為如此,梵谷街,這個地區唯一一條街名在今日仍讓人耳熟能詳的街道,竟也是最樸實的一條,坐落於一個由單調住宅構成的街區。
那條街也是我們這段小旅程的終點。我跳下腳踏車,幫安東尼解開帶子,把他抱上人行道。在我按門鈴時,他打開和他差不多高的信箱蓋,對著信箱內大喊。一位三十多歲的摩洛哥婦女前來開門;她戴著頭巾,身穿及地長袍和涼鞋。她面容和善,邊對安東尼微笑,邊跟他說過了一個週末他又長大了:「你已經是個大男孩了!」安東尼會玩一個遊戲,企圖爬樓梯上樓,而不是進入公寓裡。伊曼和老公在阿姆斯特丹已經住了十年,有兩個年紀還小的女兒。她丈夫是公車司機;她則是領有執照的「gastouder」(代班家長),也就是美國所說的日間保母。一雙深邃大眼、滿頭捲髮的四歲女兒瑪娃從她身後冒出來,不斷大聲打招呼。
伊曼和我聊了幾分鐘。幾個星期前,她問安東尼的母親和我是否能簽一份支持她妹妹的文件,她想前來阿姆斯特丹探親。一開始我有點困惑:我本以為有意移民者才需要取得這類支持聲明,單純來探親的人應該不必。後來我才得知,荷蘭現在要求來自某些國家(也就是貧窮國家,更精確地說,穆斯林國家)的人必須提出各種申請,包括請居民擔保,就算他們只是想來看看運河和鬱金香。於是我們簽了那份表格。幾個星期後,伊曼說她妹妹的申請被駁回,原因是:她「onbetrouwbaar」(不值得信任)。伊曼透過移民律師詢問詳細原因,得到的答覆是因為她妹妹在荷蘭有「親屬」,政府擔心她可能滯留荷蘭。伊曼不解。她和丈夫是荷蘭合法居民,有繳稅,做事循規蹈矩,家人在家裡都說荷語。可是,他們合法居留的事實卻成為不值得信任的理由。過了許久,那項決定有所逆轉,伊曼的妹妹獲准前來探親,但這正是這個時代的一道難題:一座在歷史上以支持包容的理念而聞名的城市,如今似乎打算為包容劃出奇怪的新疆界。
每週有一天,在將安東尼送到伊曼那兒後,我不會直接回家,而是利用一個上午的時間探索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包容疆界。我會走另一條路線,將車停在貝多芬街角落(此時已再度進入這一區較時髦的地段,這裡很適合響亮的名字,附近還有魯本斯街和巴哈街),細細品味街角花店的亭子、買一束彩色鬱金香或淡紫色玫瑰,再走幾步,按下門鈴。我在樓上和一位老婦人相見,她留著藍灰色短髮,下巴有稜有角,一雙眼睛如鳥般銳利。她是法芮達‧曼科(Frieda Menco)。我們用標準荷蘭語打招呼,互吻三下,我向她遞上花束,她微微抱怨我不該這麼客氣,然後我們一起進入她的公寓。這客廳和飯廳寬敞明亮,擺放著現代主義風格的家具。咖啡桌上鋪著桌巾,桌上有餅乾、巧克力、一壺咖啡和兩個咖啡杯、一壺水、一只插著花的花瓶。
我們坐下來。我打開錄音機,開始閒話家常。她的臉隨後轉向透過窗戶如流水般灑入的陽光,說:「好,我剛剛說到哪裡?」
外頭有一個人正大吼大叫,不,是很多人,那聲音聽起來雜亂無章。列車突然傾斜,擁擠的人群倒向一側,尖叫聲此起彼落。十六歲的法芮達已經接連兩天兩夜都坐在一名陌生中年男子的膝蓋上。運牛車廂內擠滿人,原本似乎該充滿驚恐氣氛,可是列車持續快速前進卻帶來了一陣死寂。空氣因為他們排泄物的臭味而凝結,角落有個桶子充當馬桶,但位置高得離譜,因此為了上廁所,她不但得在眾目睽睽下進行這項私密行為,還得在桶子邊緣維持身體平衡,盡量不弄倒桶子。車廂沒有窗戶,門一關上就伸手不見五指,既黑暗又悶得要死。她偶爾瞥見她的父母,他們擠在車廂另一邊,眼神驚恐,但仍透出壓抑不住的堅定希望。法芮達是他們唯一的孩子。
最後,她來到外面,站在地上。更多喊叫聲出現,遠處混亂一片。那裡有一座絞刑台,正掛著一具屍體擺盪著。現場的人開始邊跑邊叫,他們在這裡被推擠成一列列。此時有些人擠到他們當中──他們同為猶太人,每個人都穿著藍白條紋的囚服──緊貼在他們面前低聲說:「如果你有什麼值錢的東西,交給我,不然他們會搶走。」有些新來的人交出首飾;而法芮達什麼都沒拿出來,因為她一無所有。他們排成四列,兩列是婦女和女孩,兩列是男人和男孩。她和母親排在最右邊那列,再來是另一列女性。雖然她還不曉得,不過第二列的人被視為不適合勞動,要直接送進毒氣室。她看到父親排在第三列。士兵和軍犬負責維持秩序,他們身穿制服,頭戴德軍鋼盔──也就是那種惡名昭彰、看來嚇人的勺形頭盔。但是這些東西此時還沒給人那種感覺,沒有後來象徵的沉重意義。
一個恐怖的問題出現了,逼著她找出解決方法:就在眾人踉蹌地往前移動時,他父親站的那一列和她與母親這一列之間的距離愈來愈寬。
接著發生了出乎意料的事情,她看到父親似乎經過盤算,做出一個違反他平常個性的魯莽決定。他往前衝,跑過那個開放空間,忘卻那個真空地帶,穿過站在他和她之間的第二列婦女,無視於戴著鋼盔、拿著槍、身穿灰色制服的士兵。他來到她身邊,氣喘吁吁,鬆軟、圓潤、溫柔的臉靠近她。他是個藝術家,但迫於生活所需而走上商業之路。喬爾‧布隆梅特(Joël Brommet)是個專業的櫥窗設計師,也教授平面設計函授課程。法芮達是他的心肝寶貝,她會擔任他的工作助手,轉動占據他們阿姆斯特丹家中客廳一角的那台油印機,印出散發油墨味的紙張;每一張紙上面都印著細心打字的課程內容,開頭都是「敬愛的學生」。她還會摺妥講義,裝進棕色信封,好寄至全國各地的城鎮與鄉村,給那些希望跳脫種田或捕魚工作、追求光鮮生活的年輕人。有時候,她會跟著父親出差,到店家欣賞他最新的作品。父親讓她看到自己如何精心製作櫥窗的每個細節:價格標籤、標示牌、仔細擺放的模特兒。法芮達最早的記憶就與父親有關。當時她大約三歲,開心地在舒適的公寓床上昏昏欲睡。「你可以為我摘下月亮,放在櫥櫃上嗎?」她還記得那個櫥櫃,還有自己認為銀色圓月放在上面會是很棒的裝飾。他回答說:「如果妳乖乖睡覺,我就去拿一道長長的梯子,幫妳把月亮摘下來。」
一陣風吹過波蘭平原。有人喊出命令,一名黨衛隊衛兵看到她父親脫隊,往他的的方向走去。喬爾‧布隆梅特摟著太太,吻了她一下:「再見。」接著,這位櫥窗設計師跟所有人一樣乖乖地服從,遵守命令,回到自己的位置。此後法芮達再也沒見過父親。
一個德國年輕人抓住法芮達的手臂,命令她伸出手臂、掌心向上。她覺得一陣刺痛,有枝筆在她左前臂下側的柔軟肌肉上草草刺上「A25080」。
隊伍延伸到一間寬廣的大廳內。接著,程序快速進行,婦女和女孩開始脫衣,赤裸站著,衣服落在地板上。她們低著頭,雙手交叉在胸前,這時她被一種全新的恐怖情緒所吞噬──她低下頭,頭髮被剃光,眼睜睜地看著自己一撮撮的髮絲落在地上。當汽油澆在她頭上時,另一陣噁心的震驚感襲來。她們靜靜站立,赤裸、顫抖、滴著汽油,心中升起一種恐怖陰沉的憂慮。「我們的心已死……」
話說到一半,法芮達停了下來,給了我一個道歉的眼神。她的眼神流露出兩種痛苦,一種是過去的驚恐,另一種則是小小的惱怒,但後者卻放大了,因為那是現在進行式。微弱的陽光輕撫著她閃著銀色光澤的皮膚。「不,這個我們談過了……」
我告訴她沒關係,每次再聊一次她的某段故事,我都有新收穫。不過,我明白法芮達對自己太嚴厲了。她高齡八十六,飽受腸道問題所苦,那是在奧許維茨集中營感染傷寒與痢疾所留下的後遺症,背痛與脖子痛是囚犯每次企圖逃走後遭受的凌虐懲處所造成的(上次見面,我跪在她客廳地板上,她指導我做出他們被迫一次維持數小時的姿勢,頭上還舉著沉重的石塊),她還有各種因年紀大而經常出現的病痛,然而她的腦筋非常清楚,清楚到老是擔心自己的腦子不再靈光。失去記憶令她不快,她努力熟悉上網技巧,也常開車出門,讓自己熟悉所住區域的街道。寄給我的電子郵件若是有個小錯,她會再寄一封補充說明,更正那個錯誤。
她是在附近出生的。當時的舊南區是阿姆斯特丹的猶太人中心,至今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如此,然而戰爭摧毀了它的核心(一九四○年的阿姆斯特丹有八萬名猶太人,如今大約只有一萬五千名)。法芮達童年的家是一戶位在寬廣的南阿姆斯特爾大道(Zuider Amstellaan)上的公寓,那條路在戰後更名為羅斯福大道。公寓位在二樓,面對街道。我的電腦裡有法芮達最珍視之物的掃描副本,那是一張她大家族的照片,拍攝地點在那間公寓飯廳的餐桌前,他們坐在一起吃飯,慶祝她祖父的七十五歲生日。餐桌旁十七個人當中,有十二個人不久後便過世,大多死在奧許維茨集中營。飯廳中的家具已經消失在歷史巨輪下,除了我們每週聊天時法芮達常坐的椅子後方擺的那只五斗櫃,那是她母親在戰後找到的。
戰前,因為童年的親密感,法芮達非常了解她所住的區域:包括大人來來去去而忽略的角落,而且她認識每個人。童年住家外面的轉角是一座三角形公園,公園邊有一些小巧的公寓樓房。其中一棟的二樓,也就是梅爾維德廣場(Merwedeplein)三十七號,住著一對猶太夫婦和他們的兩個女兒。她記得那一家人相當時髦,或許是因為他們幾年前才剛從德國移民過來,所以看起來散發著些許的異國風情。大女兒瑪格(Margot)比法芮達小兩歲,小女兒小她四歲,這位小女生後來成為全世界最知名的女孩──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法芮達記得瑪格文靜寡言,安妮則是街坊的調皮鬼,聰明伶俐。不過,大致而言,她們「只是普通的女孩子」。她會跟她們一起跳繩。她對法蘭克家最深刻的記憶,是受安妮之邀去到他們的公寓。安妮在樓梯間裡要法芮達安靜點,因為她母親正在午睡。那一幕就此留在法芮達腦海裡,因為那個概念頗為奢侈,她自己的母親從來不睡午覺。
如果在這裡先暫停一下,說說我為什麼起心動念,撰寫一本書來談我住了五年多的城市,應該不為過。總之,我要先解釋一個在賓州西部長大、後來待在紐約的美國人,為何會覺得這座歐洲城市如此迷人,甚或如此必要。如果跳脫剛才那一幕,拉遠來看,我們會發現,一九三八年左右那兩個在阿姆斯特丹某個樓梯間講悄悄話的猶太女孩,渾然不知一場世紀大屠殺即將降臨,而且其重要性與影響力甚至高過她們當中一人日後獲得的名聲。這兩個女孩即將面臨的危險與我們多數人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形成強烈對比,但如今我們這種生活也碰上各種新危機。她們後來在奧許維茨集中營再度相遇,命運的作弄卻讓瀕死的那人最後過著富有、充實、複雜的生活。巧合的是,我們這種生活方式的起源,我們視為「現代」生活的起源,與收留我的這座城市其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那種關係並非十分明顯。如果你向某人提起你住在阿姆斯特丹,得到的反應可能是一個低聲輕笑。你朋友的目光會望向一旁,搜尋模糊記憶中前來阿姆斯特丹旅行的往事。對方會告訴你,阿姆斯特丹是個瘋狂的地方。
那不只正確,多多少少也是官方的政策。約伯‧科恩(Job Cohen)在二○○一至二○一○年曾擔任阿姆斯特丹市長,某天晚上我在位於紳士運河(Herengracht)畔、建於十八世紀的市長官邸內訪問他,他告訴我:「瘋狂在阿姆斯特丹是一種價值。」他的意思是瘋狂是件好事,不過有許多人難免質疑,包括某些市民。強占建築物,也就是強行進入一個不屬於你的地方住下來的行為,在一九七一年合法化,只要該建物已有一年無人使用即可。雖然那條法律在二○一○年修改,不過還是常可見到建築物破舊不堪的外牆上掛著布條,聲稱居住者藐視公權力。這座城市一年有五千至七千五百名領有執照的性工作者,大多在街邊的櫥窗裡工作,其餘的則在合法妓院內上班。如果你對於如何在紅燈區尋娼覺得緊張與困惑,不妨向轄區警員求助。你可以在「咖啡館」(Coffee Shop)的菜單上點大麻,上面的大麻商品可能分成不同類別,例如室內、室外和外國種植,再細分成名為濕婆、白寡婦及大象等等的各種產品。儘管賣淫合法,並且受到管制(只有歐盟公民才能賣淫,因為它與其他工作一樣都需要工作許可證),但大麻交易在荷蘭卻屬於一種奇特的類別「gedogen」(應屬非法,但官方容許)。
所以,是的,這是一個瘋狂的地方,你可能會認為此地因為過於混亂,終年都有天塌下來的危險。然而,這座城市大部分地方仍保有傳統的沉著,瘋狂之處實在少之又少,少到讓人以為住家附近的人食用的唯一毒品,是某種中產階級的鎮靜劑。荷蘭人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真面目,那就是他們是十分傳統的民族,從他們堅持修剪整齊(也必須說,相當缺乏品味)的花園,到職場上彷彿永無止盡的會議(包括開會來討論進一步會議的時程)都是明證。於是瘋狂透過幾種方式融入了這樣的文化:阿姆斯特丹以其包容的傳統為榮,他們有一個道理是說,對於無論如何都會發生的活動,最好予以合法化,並進行管理。沒有人宣稱這個方法完全成功。在性交易與軟性毒品交易的案例中,大眾長久以來認為,阿姆斯特丹作為這類產品唯一受官方包容的地方,多少導致了這裡成為大麻黑市商人的全球總部。
可是,如果這種瘋狂為真,那麼如下的描述也所言不假:阿姆斯特丹的規模與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市(Columbus)相當,也就是說人口不算多,約有八十萬居民;它與加拿大薩克其萬省薩斯卡通(Saskatoon)處於相同緯度,也就是說位置偏北。不過它影響現代世界之深,或許世上沒有任何城市足以匹敵,它在美國留下的印記,尤其深入美國認同的核心。
這些說法之所以正確,全基於同樣的理由。阿姆斯特丹以一樣東西聞名(除了運河、大麻咖啡館以及性工作者之外),那就是破爛、古老、飽受誤解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一詞。多數人認為,阿姆斯特丹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地方,它的自由經常令人感到可笑或不可置信地搖頭。之所以這麼說,我所用的自由主義的定義等同於不受約束、開放與寬容。但是這個詞還有另一個更高深的意義,那其實與個人自由有關。
當然,英文的「liberal」來自「liber」,拉丁文的「自由」,而它也成為「liberty」、「libertarian」以及「libertine」等相關英文字的字源。「liberal」是在歷史上被殘酷地往不同方向拉扯的一個單字。目前已知此單字在英文書寫作品中最早出現於威克理夫(Wycliffe)翻譯的《聖經》,出版時間約是一三八四年。在許多聖傳中屬於次經一部分的《馬加比二書》(2 Maccabees)中有一段文字寫道,推羅(Tyre)的人是「最自由的」,容許埋葬遭不義手段害死的人。在此,率先推動讓《聖經》以通俗口語呈現的中世紀教會改革者威克理夫忠實地從拉丁文「liberalissimi」翻譯過來,但是當時英文裡已經有了這個字。英國詩人喬叟(Geoffrey Chaucer)一再使用它,通常是指「充沛之意」,就像「youre liberal grace & mercy」(你充滿慈悲寬容)。
從很早開始,此字就兼具正負兩面的意涵。在《奧賽羅》中,莎士比亞筆下的愛米莉亞違抗丈夫伊阿古要她保持沉默的命令(而他也打算謀殺她),她哭喊道:「不,我會像北風一樣自由發言。」意即如北風那般瘋狂而放縱。在《亨利六世》下篇,莎士比亞利用這個字來代表寬宏大量:
我信任他們;因為他們是軍人,
機智、有禮、寬宏大量,精神飽滿。
他甚至提及「自由藝術」(the liberal arts),用這個名詞指涉的意思與我們今天的用法相同。它也代表體積龐大,例如「她的大胸脯」(her liberall brest)或「一個肥胖大漢,襯衫前襟上掛著層層下巴,大鼻子(liberal nose)上掛著夾鼻眼鏡」。
「liberal」這個字在今天遭遇的尷尬處境是,它在美國與歐洲的意義似乎相反。這是因為它的根本意義──自由,可用在南轅北轍的事情上。十九世紀的歐洲商人不想受關稅箝制,喜歡用「自由主義」表達政治立場,也就是限制政府干涉公共事務。在美國,它的用法比較偏向社會正義與個人自由,因此意味著政府必須多加干涉,以實現那些自由。所以,荷蘭自由黨(Liberal Party)的自由市場政綱就會被認為多多少少與美國脈絡下的自由相反。
在「liberal」後面加上「ism」,它就變成一個意義更廣的字,涵蓋許多宏大的思想;這些概念彼此相關,不分高下。「liberalism」(自由主義)在英文中的起源並未久遠。它最早出現在一八一六年《晨間紀事報》(Morning Chronicle)的一篇文章中,文中報導西班牙國王判決「十五個被控自由主義之罪者服苦役與流放等刑罰」。西班牙國王的用法涉及了該字的政治意涵,以及個人可自由選擇政府的概念。因此,自由主義與民主密不可分。它也有經濟上的意義,資本家據此宣稱,個人權利中的一項基本要素就是擁有財產的權利。
自由主義的所有用法殊途同歸,皆以個人為中心。就這個角度來看(我也將在本書中採取這個角度),這個字描述的是現代與中世紀之間的一條斷層線:它代表人與中世紀的決裂,擺脫以教會與君主的傳統智慧為中心的知識及權力建構而成的哲學。
此外,自由主義在歷史上包含了對個人自由與個人權利的支持,而且支持的不只一個人,而是每個人,活在世上的每個人。自由主義的根源又與阿姆斯特丹的根源關係密切,我們甚至能更進一步地說自由主義誕生於阿姆斯特丹。當然,這樣的說法可能會遭受抨擊,甚至我自己就會加以抨擊。自由主義是一個分散的概念,由一些同樣分散的觀念構成,例如正義、道德、私人財產等等。就像我們身邊的氧氣,你不能說自由主義起源自一個特定的地方。若要列出一份無可爭辯的偉大自由主義理論家名單,當中將包括洛克(John Locke)、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伏爾泰(Voltaire)、亞當‧斯密(Adam Smith)、彌爾(John Stuart Mill),以及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如果要認真表揚地理上的自由主義聖地,我們可以提出巴黎、倫敦,以及傑佛遜在美國維吉尼亞州山丘上的蒙蒂塞洛山莊(Monticello estate)。
這些都沒錯。不過,思想皆有其歷史與起源,深植於人們心中和他們的奮鬥、身體、外觀或情感動盪、他們對新時尚與品味的追求,以及他們亟欲擺脫任何束縛的渴望之中。精神分析在十九世紀末維也納上流階層的客廳中成形;爵士樂誕生於二十世紀初,當時身為黑奴後裔的美國南方黑人一波波地逃離種族歧視壓迫,在美國北部充滿活力的工業城市展開新生活。同樣地,數量驚人的各種力量在始於十六世紀末的一個世紀裡匯聚於阿姆斯特丹,孕育出大眾與彼此及政府關係的新思維。阿姆斯特丹黃金年代的故事是一個歷史上的經典,其生動性與重要性媲美美國南北戰爭或希臘古典時期的故事。這座城市的興起十分突然,就連活在那段時期的人都感到驚奇。它的構成元素與人物具有標誌性的地位,而且互有關聯──世界第一個股票市場的成立;林布蘭與同時期畫家所創作的世俗藝術的發展;官方包容政策的擬定;知識自由氛圍的醞釀,引來歐洲各地的思想家,開創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出版中心;以及阿姆斯特丹著名的運河開挖,改變了市容。現代人把「家」當成個人私密空間的概念,甚至也能回溯到這個時期的荷蘭運河屋。
在這些概念或實際上的各種突破底下,是對個人箝制的鬆綁,而它的起源來自宗教改革與第一波科學實驗,同時也與阿姆斯特丹的地理及社會條件有關。這些要素構成了一個新型的地方:一個自由主義的溫床。
這些力量匯聚在十七世紀阿姆斯特丹一名年輕猶太人的腦海中。當今嚴肅的思想家相當倚重史賓諾莎(Baruch Spinoza),視其為引導者,他的重要性或許比其他任何知名的哲學家都來得高。神學家、電腦科學家、哲學家,以及膽敢面對真正大哉問者無不仰賴史賓諾莎的學說。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與史賓諾莎身處現代性的中心點有關,當時自由主義的各種力量與今日思想家的世界觀正開始出現。如同莎士比亞只可能出現在他那個時代──在英語吸收了中世紀盛行的拉丁文、諾曼人入侵時的中世紀法文,以及其他令這個語言的表達力如此豐富的影響因素之後──史賓諾莎影響了現代政治思想、倫理學以及神學的革命性哲學,這只可能出現在十七世紀晚期的阿姆斯特丹,也就是在這座城市的包容、世俗權力取代了教會權力,以及第一個真正的現代自由貿易文化等原則建立之後。史賓諾莎參與過盛行於咖啡館與書店內的哲學辯論;他著迷於公開的解剖示範;商船與遊艇從港口出發,迎風航向全球各地的景象;還有人民代表(popular representation)的構想。阿姆斯特丹在富強全盛期所帶來的這些成果,全都沸騰、濃縮、精煉到了史賓諾莎的哲學裡。而它就從那裡,以及其他許多來源,進入了更寬廣的世界。
因此,本書雖然談一座城市,但同時也談一個思想。阿姆斯特丹的歷史屬於所有人,因為生活在西方民主社會中的每個人,無論處於政治光譜的哪個位置,全都是自由主義者,我們的生活均奠基在自由主義之上。
雖然自由主義是我們最珍貴的一項文化資產,但它也可能過分伸張、遭到輕視或揮霍。我們必須細心面對自由主義,因為它涵蓋的範圍實在太廣,從立憲政府到民主選舉、信仰自由、民權、自由貿易等,以至於我們認為那是永恆的普世價值。可是,自由主義當初從一個真實的時空中出現,此後在各個時代如火焰般搖晃,而它也有可能於未來熄滅。
(本文節錄自第一章「單車之旅」)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自由之城:反抗權威、宗教寬容、商業創新,開啟荷蘭黃金年代的阿姆斯特丹(全新修訂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46 |
二手中文書 |
$ 379 |
史地 |
$ 408 |
旅遊 |
$ 422 |
文化研究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自由之城:反抗權威、宗教寬容、商業創新,開啟荷蘭黃金年代的阿姆斯特丹(全新修訂版)
從反抗西班牙的獨立戰爭、燦爛的「黃金年代」,到德軍入侵的二次大戰
阿姆斯特丹的崛起和強盛、失落與再起,都和自由主義息息相關
阿姆斯特丹的百年城市史,正是自由主義的一頁發展史!
==========
阿姆斯特丹,一座吹著「自由主義」之風的偉大城市,它重視個人自由、反抗權威,包容不同的膚色、性向與信仰。在它引領荷蘭、開啟黃金年代之前,原本只是一座十三世紀建於水壩濕地上的小漁村,然而它善用獨特的地理環境,與海爭地,發展出有別於歐洲傳統的社會與信仰自由,這個差異最終也導致世界歷史產生劇烈變動。
如今,這座城市往往讓人聯想到它「大膽」、「創新」、甚至有點「瘋狂」的那一面,而在數百年間貫穿這些偉大進展的,便是「自由主義精神」。自由主義就像現代與中世紀之間的一條分割線,代表人擺脫過往以教會與君王為中心的知識及權力建構。阿姆斯特丹特殊的條件讓自由主義得以在此茁壯成長,而自由主義也進而形塑出這座城市的獨特樣貌。換句話說,阿姆斯特丹的城市發展史正是自由主義精神在歐洲乃至全球落地生根的發展縮影。
▉宗教寬容政策,打造異教徒的避風港
在本書中,作者羅素・修托指出,大麻和性交易,均充分展現了荷蘭詞彙「Gedogen」的精神,亦即「應屬非法,但官方容許」;而若是進一步探究包容的概念,則會從中推得「自由主義」的結論――正是因為包容異己、重視個人權利的自由主義思想,讓阿姆斯特丹得以從一個與海爭地的小漁村,逐步發展為今日全球的商業與金融重鎮。
十六世紀,奉天主教為國教的西班牙屢次迫害異教徒,這些來自西班牙的猶太人、安特衛普的新教徒紛紛避走對宗教相對寬容的阿姆斯特丹,同時也將手工技藝、金融體系帶進該城,為阿姆斯特丹日後的崛起打下梁基。為了追求自由,阿姆斯特丹市民在奧蘭治親王威廉一世的號召下,起而反抗西班牙的獨裁統治;其獨立革命的經驗和精神,深深影響一個世紀後的美國獨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
▉商業創新,藝術與思想齊放的黃金年代
十七世紀,荷蘭邁入了偉大的「黃金年代」。台灣人都知道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於一六○二年在阿姆斯特丹成立,這是人類史上第一間股份有限公司;同年,史上第一間證券交易所也在阿姆斯特丹成立,顯示當時的阿姆斯特丹已具備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日後更發展出經濟自由主義。事實上,倫敦的金融體系正是移植自阿姆斯特丹;而今日被視為全球金融中心的紐約,其前身正是荷蘭人創建的「新阿姆斯特丹」。
哲學思想、文化藝術也在此時百花齊放。哲學家史賓諾莎在阿姆斯特丹發展他的哲學理論,笛卡兒、洛克等人因母國封閉的政治氛圍,曾短暫避居阿姆斯特丹,受當地的知識自由氛圍薰陶;畫家的創作主題也從原本的宗教畫逐漸轉為風俗畫,大師林布蘭的《夜巡》生動描繪了阿姆斯特丹民兵隊巡邏時的場景,彷彿告訴世人:城市的安危由市民親自守護,而非傳統的封建騎士。
▉互為表裡的阿姆斯特丹與自由主義
二戰時期,阿姆斯特丹遭受無情戰火蹂躪;戰後,復甦中的阿姆斯特丹又經歷了來自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的挑戰與改革,像是質疑權威的「挑釁運動」、鋪天蓋地的「全球化浪潮」、以及毀譽參半的「多元文化主義試驗」。但無論遭遇了什麼,自由主義一直都是阿姆斯特丹的城市基調,引領這座城市邁向未來。
作者羅素・修托根據他在阿姆斯特丹居住多年的生活經驗,用田野訪談、細心觀察和故事鋪陳,娓娓道出自由主義和阿姆斯特丹之間難分難捨的深厚羈絆:自由主義形塑了阿姆斯特丹的城市樣貌,例如重視個人隱私的運河屋成為都市的特色景觀;而阿姆斯特丹也成為思想家的避風港,讓自由主義得以持續發展茁壯,兩者可謂互為表裡、一體兩面。
◎本書2017年曾以《阿姆斯特丹:一座自由主義之都》書名出版◎
國際書評
「內容豐富,描述眾多歷史事件,巧妙結合重大文化趨勢與個人故事。」──《紐約時報》
「書中迷人的歷史敘述,充滿一座近千年的繁忙貿易城市散發出來的色、香、味。」──美聯社
「羅素・修托不只善於說故事,也懂得挖掘事情的根源。」──《英國衛報》
「透過阿姆斯特丹具啟發性的歷史,讓讀者得以探索這座城市與其思想精神。」──《西雅圖時報》
「羅素・修托愛阿姆斯特丹,而我愛這本書。」──約伯・柯恩,阿姆斯特丹前市長
「羅素・修托巧妙地描述了阿姆斯特丹是在幾代人的共同努力中,從原本的溼地建造而來……,這座城市以自由和寬容的精神,展現了它是如何吸引全歐洲最有朝氣的人們,來創建一個自由的公民和經濟社會,並在一個世紀後成為美國的榜樣。」──杰夫・比克斯,時代華納執行長
作者簡介:
羅素・修托Russell Shorto
畢業自喬治・華盛頓大學。歷史學家、作家與記者,擔任《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e)特約作家、二○○八至二○一三年間曾擔任阿姆斯特丹約翰‧亞當斯學院(John Adams Institude)院長。著有《革命之歌》(Revolution Song)、《笛卡爾的骨頭》(Descartes’s Bones)以及《世界中心的島嶼》(The Island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譯者簡介:
吳緯疆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自由譯者。譯有《洋風和魂》、《里約熱內盧》、《烽火巴黎眾生相》、《一口漢堡的代價》、《不安的山谷》、《成為黃種人》、《旅行的異義》、《自戀時代》(以上均為八旗出版)、《馬基維利,請教我如何出人頭地》、《被壟斷的心智》、《美國世紀締造者》、《地球與人》等書。
章節試閱
第一章【單車之旅】節選
阿姆斯特丹的一天,從我抱著蹣跚學步的兒子出門開始。我把孩子固定在腳踏車把手間的座位上,再想辦法將他穿著運動鞋的短胖小腳放上腳踏墊,接著我們便上路,穿梭在常迎著徐徐微風的安靜社區間。這個區域叫舊南區(Oud Zuid),你只要看看任何一位荷蘭藝術大師的畫作,就能想像我們騎著腳踏車的早晨是何等光景。它帶有一種白色的潔淨,彷彿剛被清洗過的質感。舉個例子,這裡的光線冷靜而清醒,絲毫沒有地中海陽光那種帶著橘色微粒的光芒。這一帶的房屋多為三、四層樓高的磚造建築,全都建於二十世紀的前二十年...
阿姆斯特丹的一天,從我抱著蹣跚學步的兒子出門開始。我把孩子固定在腳踏車把手間的座位上,再想辦法將他穿著運動鞋的短胖小腳放上腳踏墊,接著我們便上路,穿梭在常迎著徐徐微風的安靜社區間。這個區域叫舊南區(Oud Zuid),你只要看看任何一位荷蘭藝術大師的畫作,就能想像我們騎著腳踏車的早晨是何等光景。它帶有一種白色的潔淨,彷彿剛被清洗過的質感。舉個例子,這裡的光線冷靜而清醒,絲毫沒有地中海陽光那種帶著橘色微粒的光芒。這一帶的房屋多為三、四層樓高的磚造建築,全都建於二十世紀的前二十年...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章・單車之旅
自由主義在歷史上包含了對個人自由與個人權利的支持。自由主義的根源又與阿姆斯特丹的根源關係密切。自由主義是一個抽象概念,但根源卻能在真實的地方找到,也就是我所生活的城市。穿梭於阿姆斯特丹,往昔會以各種方式讓你留下深刻印象。灰濛濛的天氣裡,海鷗在中世紀運河上斜飛時,可能帶給人難以言喻的憂鬱感傷。爬上西印度公司昔日倉庫的閣樓,一種神祕的愉悅感油然而生,表面黏糊的老橫梁依然散發出淡淡菸草香;這個地方在四個世紀前塞滿了菸草葉。這股香氣不禁令人想起塑造出今日世界的那些開發行動與不可思議的探險...
自由主義在歷史上包含了對個人自由與個人權利的支持。自由主義的根源又與阿姆斯特丹的根源關係密切。自由主義是一個抽象概念,但根源卻能在真實的地方找到,也就是我所生活的城市。穿梭於阿姆斯特丹,往昔會以各種方式讓你留下深刻印象。灰濛濛的天氣裡,海鷗在中世紀運河上斜飛時,可能帶給人難以言喻的憂鬱感傷。爬上西印度公司昔日倉庫的閣樓,一種神祕的愉悅感油然而生,表面黏糊的老橫梁依然散發出淡淡菸草香;這個地方在四個世紀前塞滿了菸草葉。這股香氣不禁令人想起塑造出今日世界的那些開發行動與不可思議的探險...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