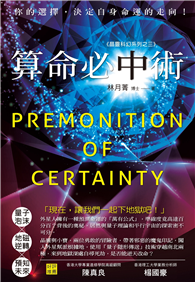「雞同鴨講」的尷尬與愉悅
聽過不少對法國人的批評,其中之一是他們多不會說英語,即使會說的也只和你說法語云云。我覺得此說有失公允,上別人家做客,只能客隨主便,入鄉隨俗。再說交流的手段不只是語言,其實「雞同鴨講」也有它特別有趣的地方,既尷尬又開心。
1996年第一天去巴黎坐地鐵時,進了地鐵站就糊塗了,不知東南西北。看到一個長得像華人的姑娘,便上前問路。她果然有四分之一的中國血統,會說一兩句英文,一兩句廣東話。可寒暄之後,就無法深入了。她拿著地圖嘰裡呱啦說了半天,我一個字也聽不懂。猜想她是說要轉車,可我用英文問她在什麼地方轉車時,她不知道我說什麼。這時候,車來了,她便把我拉上了車,在車上她又指著車廂裡的線路圖比劃了半天,我仍不得要領。這時,旁邊一位會說英語的女士主動走上前來,我總算得救了。這位婦女告訴我她和我乘坐的方向相同,要我跟著她走。這時,小姑娘才松了一口氣。
後來我才知道巴黎的地鐵有多麼複雜,又有多麼方便。地鐵有市區和郊區兩種。市內共有13條線,分別稱為M1─M13,M是法語Metro(地鐵)的縮寫。這些線路在交通圖上是用不同的顏色標記的。如M1為黃線,M2為藍線。通往郊區的鐵路線有四條,分別稱為A線、B線、C線和D線。
計劃去某地時,首先要弄清楚下面幾個問題:乘坐哪條線;這條線的起點和終點分別叫什麼名字;在哪裡轉車。如果不用轉車,到站以後,順著出口的標記(Sorter)出站;而如果要轉車,下了中轉站以後,得找中轉的標記(Correspondence),然後順著標誌找到中轉站。有時候,下車的地方離中轉站有好幾百米,而且要拐彎或上樓下樓,如果不注意沿途的標記,很有可能從出口出去了。再進來,得重新買票。我那次若沒有那位婦女帶路,真不知該怎麼回家。
和那位法國婦女一塊兒呆了一二十分鐘,因而有機會聊了聊。她告訴我,巴黎市區的房租很貴,作為兩個孩子的母親,她根本不可能在市區租房子,所以每天坐地鐵。好在巴黎的地鐵很方便,她每天在路上只需40分鐘。這位婦女告訴我,法國人認為中文是世界上最神祕,最難學的語言。我告訴她,我認識的幾位法國學者,中文都棒極了。
在墨爾本住慣了的人,在巴黎很容易迷路。因為墨爾本的街道成規成矩,很容易找;而巴黎呈圓形,它的街道是由一個一個的圓點向四面八方放射而成的。也就是說,到一個交通口,一般不是四條路,而是八條路,十條路。就算拿著地圖,也常常得問路。
問路問多了,就問出經驗來了。2001年再去法國時,我已經會幾句簡單的法語,每次便用法語開頭:bonjour, Ou̍ est(您好,哪裡是……)。法語中問路的表達有好幾種,我選擇了最容易的一種。說完Ou̍ est,便拿出我事先準備好的地址(往往寫得大大的,以免別人看不清楚)。接下來就會有各種情形發生,有的人會邊說邊打手勢,這就好辦,我只用記住一個手勢,到有岔路時再如法炮製;有的人不用手勢,哇啦哇啦地解釋。這個時候,我會待路人說完以後,打著手勢問Gauche ou droite(左還是右)?路人一般就會用改用手勢指點。我還是採用老原則,至少記住路人所指的第一方向。不過,儘管這樣,還是有麻煩有不得要領的時候。2005年我和一個朋友去法國南部玩,就遇到一次。我們詢問香水博物館的地點,一位年長的法國婦女握著我的手,熱情洋溢地給我說了足足五分鐘。手勢可能不在她常用的範圍之內,她完全忽視我的手勢。把站在一旁的朋友樂的夠嗆,說我倆「聊」得真開心。法國女士滿面笑容不停地解釋,我微笑著頻頻點頭,完全不像是兩個語言不通的人。
有一次在巴黎郊區問路,問到兩個西班牙的婦女,年輕的會說一點英語,因無法給我解釋清楚車站的位置,她們便自告奮勇帶我去。年輕女孩告訴我她只有幾歲時就嚮往巴黎,現在終於能生活在這裡,覺得很幸福,尤其能住在森林邊上。她喜歡巴黎的一個原因是因為這裡有許多民族的人。她吃過中國菜,覺得好吃極了,她很希望有機會去中國。每次聽到有人誇中國,我都非常高興。接近車站時,我連連向她們道謝。
在巴黎的半年裡,最長的一次問路化了三個小時。一個週末的晚上,接到我在墨爾本單位祕書的緊急電話,要求我第二天一定把一份材料電郵回去,以申請研究資金。而單位週末沒人值班,我無法進去,得找一個能用英特網的地方。在火車站遇到到兩個香港來的小女孩,便向她們打聽。2001年在巴黎還很難看亞洲人,尤其不在旅遊點的話,見到她們覺得很親切。可她們只知道蓬皮杜中心附近有一個,卻沒有準確的位址。結果我花了三個多鐘頭,問了若干個人,用遍了我所知道的所有的問路方法才找到。是一個叫Easy everything的地方,一個國際性的公司。上網20法郎一個小時,下載要另外加錢。
我在巴黎的同事不懂中文的至少會英語,唯一要單獨打交道的是大樓的門衛。按照規定,最後離開辦公室的人要用鑰匙把門鎖好。我沒有鑰匙,祕書告訴我,可以請樓下的門衛幫忙。有一天,我發現自己是最後離開的,可是不知道鎖門該怎麼講,就把辦公室房間的號碼寫在一張紙上,走到門衛身旁,把紙給他看,做一個鎖門的動作,然後用法語說聲謝謝。他懂了,連連點頭,上樓去鎖門。那以後,我便不擔心晚下班和早上班了(辦公大樓開門時間是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
鎖門或問路都是屬於比較簡單的交流,碰到複雜的事情時就有些麻煩。比如在銀行,我去的那個支行沒有懂英語的。我第一次取錢時,去了三次都不得要領,最後只好請同事陪我去。有次到取款機上取款也遇到了麻煩,以往把卡塞進去,摁了密碼以後,就可以摁錢的數目了。可是那天摁了密碼以後卻出了一系列選擇,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一下就傻了。沒辦法,只好向過路的人請教,算我運氣好,遇上一個會英文的,她告訴我得選擇貨幣,因為歐元已經開始使用了。
我喜歡看演出,剛到巴黎沒兩個星期,就冒冒失失地看了一出法語的話劇。而就是這次的嘗試,體會到「雞同鴨講」的歡愉,以後看什麼演出都不膽怯了。
那是一個星期五,吃了晚飯以後,到街上閒逛。經過一個小小的劇場(後來聽說是巴黎最早的劇場之一,可惜忘了名字)時,有不少人在買票,想一定不錯,再看看演出時間,7點到8點,時間也合適,就決定去看。當時我既不知道演出的類別,也不知道名目,夠可笑的。
劇場相當小,一共只有十排位置,每排只能坐五到七人,前面有一個不大的舞臺。當晚演出的是一個只有六個演員的獨幕喜劇(之所以知道是喜劇,因為觀眾們笑聲連連),我一共只聽懂了三五個單詞,劇情完全沒看懂,但覺得非常有趣,因為我可以不停地根據他們的肢體語言和表情揣度他們的對話。其中有一段特別有意思,在兩三分鐘裡,四個演員坐在那裡,面對觀眾,互相之間不交流,沒有一句臺詞,沒有一個肢體動作,全部靠面部表情來發展劇情。雖說我不知道具體內容是什麼,但可以猜出這四個人各有各的想法和目的,都想和別人交流但都不願意首先發言。四個人的不同性格,通過他們的面部表情在這幾分鐘裡全表現出來了。
在蒙馬特高地附近,有個名叫狡兔的酒館(Au Lapin Agile)。法國著名畫家安德列‧吉爾(Andre Gill)1875年的畫作,一隻手拿酒瓶的兔子敏捷地從湯鍋裡跳出,是這個酒館外牆上的招牌畫。酒館裡面的牆上也有很多畫,其中有一幅是畢卡索的畫像。很多年前,酒館的少東家在一次搶劫案中被殺,這裡曾一度被稱為「暗殺者酒館」。畢卡索以及畫了《舊巴黎蒙馬特區》的風景派油畫家鬱特裡洛(Maurice Utrillo)等人,常在這裡徹夜逗留,畢卡索還畫了一張《在狡兔酒館》的油畫。現在,酒館晚上有演出,我和同事在那裡欣賞過法國民歌。
演出於晚上九點開始,門票130法郎,包括一杯酒水。酒館中間放了兩張方桌,是演唱者的座位,四周坐滿了觀眾,大約有三十來個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本地人。
九點正,七位歌唱家在鋼琴的伴奏下唱了起來。這七個人年齡都在40以上,兩女五男。其中兩個年長的男士,聲音很渾厚,有一個女中音的音色也很特別。他們演出的前半部分大多為合唱,也有領唱和齊唱,後半部分多為獨唱。我最喜歡聽的是合唱,雖說一句歌詞也沒有聽懂,但聽到了法國人的悲傷與歡樂,憂鬱與奮發,還有浪漫和激情。
貴婦街附近有一家電影院,星期五下班時我總要到那裡拐一下,看看有什麼好電影。有一次,看到電影廣告Chaos,似乎很有意思,就去看了。電影情節頗為複雜:女主角目擊一個向她和丈夫求救的女人被打傷,良心受到責備,主動去醫院看護傷者,於是捲入了一場與販毒賣淫集團的鬥爭,其中一場戲就在我們單位附近的十二號地鐵站拍的。幾個主要演員都演得很好,雖然我幾乎沒聽懂兩句話,卻好像全看懂了。
‧‧‧‧‧‧‧‧‧
不眠的西雅圖
1998年的秋天,我在西雅圖住了六個星期。那座城市的風景,那座城市的人,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西雅圖座落在美國的西海岸,素有綠寶石之城的盛譽。綠湖,聯邦湖,華盛頓湖象三顆晶瑩的綠寶石鑲嵌在西雅圖的大地上。湖上人家是那兒幸運的居民,不少人家的客廳面湖而立,透過大的落地窗,湖上的美景一覽無餘。客廳外是一條几米長的小橋,橋墩上拴著一條小小的船。天氣好的時候,主人會走出客廳,解開纜繩,蕩舟散心。
我有幸在綠湖的一戶人家裡住了兩個星期,飽覽了湖上的景色。綠湖是個人工湖,圍繞綠湖走一圈,大約要兩三個小時。在環湖的小路上,從清晨到傍晚,都有健身的人群。跑步競走的男女老少的虎虎生氣,常常和湖邊漫步尋食的水鴨水鳥的悠然自得相應成趣。有一次,我看到五個正在垂釣的老翁,個個屏息斂聲,盯著自己的魚杆兒。而在離他們不遠的地方,一隻龐大的魚鷹卻若無其事地在小橋上踱著方步,一點兒也不理會橋下游來遊去的小魚兒。
一般的城市都是伴水而立的,但有山又有水的卻不多,西雅圖就在這不多見的城市之中。站在西雅圖,居然能看見一座終年積雪的雪山。不過,要看清楚雪山的真面目還挺不容易。我在的時候,西雅圖天氣欠佳,晴空萬里的日子很少,在大多數的時候,雪山都隱藏在雲霧之中。華盛頓大學的噴水池前是看雪山的好地方。在無雲的大晴天裡,它會赫然矗立在噴水池的前方。不過,不知是因為光線還是雲彩的緣故,它給你帶來的會是夢幻般的神祕。望著它,一種飄然欲仙,入仙化境的感覺會從你的腳下升起,然後慢慢地侵入你的全身。你會突然覺得自己不是處在一個現實的世界裡。不過,這種感覺不會維持很久。一陣微風就能帶來一片雲彩,而雪山也就隨著雲彩消失了。我拍了不少雪山的鏡頭,有照片,有錄像。拍攝之際雪山確實在我的鏡頭裡,可洗出來的照片,放出來的錄像,居然都沒有雪山,只有幾朵厚厚的雲,著實讓我失望。
不過,我有幸看過一次雪山的真面目,而且看得很清楚,雖然只是短短的一瞬間。有一天,我坐在朋友的車裡,當汽車在高速公路上行駛時,突然,大雪山擋在我們的面前。那麼巍峨,那麼真切,我似乎都感到了雪山所散發而出的寒氣。可就是那麼一刹那。待我扭頭尋找它時,它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西雅圖的楓樹十分吸引人,滿城都是。按說我不是沒有看過楓樹,香山的金秋,嶽麓山的紅葉我都欣賞過,可真沒有看過西雅圖那麼漂亮的楓樹。我們常說紅楓,但紅與紅之間其實是很不一樣的。有的紅得火爆,大膽,象壓抑了千年突然噴射的火山;有的紅得羞澀,嫺靜,象初戀姑娘的顏容。
大自然是很懂得色彩的搭配的。有古典式的搭配:紫紅、深紅、桔紅、淺紅,鵝黃、淡黃、金黃、土黃,抑而從深到淺,抑而由淺至深。此色和彼色之間有著的是不露痕跡的過渡;有現代派的組合:在一大片金燦燦的黃葉之中,突然冒出一團火。這團火打破了黃色的和諧,以它那弱小而充滿活力的身軀,向黃色挑戰。
在眾多的楓樹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兩棵,一棵被我稱為鵝黃楓,一棵被我稱為五彩楓。
第一次看到鵝黃楓時是在一個難得的好天氣裡。那一天,天空藍得象一塊寶石,沒有一絲雲彩。我背著書包穿過華盛頓大學的一片小樹林。突然,眼睛一亮,一棵不尋常的楓樹挺立在我的面前。一般來說,秋天的楓樹的葉子,如果是黃色的,顏色都比較深,比較暗,黃得深沉,黃得蒼涼。而這棵巨型的大楓樹的葉子卻是鵝黃色的,像剛剛孵出來的小鴨的絨毛,黃得嬌嫩,黃得叫人憐愛。這棵楓樹在秋日已不再強烈的陽光下,散發出春天的朝氣。不過,幾天以後,當我拉著大學的一位教授去看那棵鵝黃楓時,它的葉子全變了,變成了金黃,以致我懷疑自己第一次時是不是看錯了。
五彩楓我幾乎每天都能看到,因為它就在去圖書館的路上。每一次看到它時,我都覺得自己是在閱讀人生。五彩楓的樹頂是紅顏色的,跟下來是土黃、深黃、淺黃、深綠、淡綠、嫩綠,真難想像同一棵樹上的樹葉怎麼能有那麼多不同的色彩。我曾經拿著攝像機拍那棵樹,看著色彩在陽光下變幻,看著時光在陽光下留連,最後定格在樹稍上。原來,生命的盡頭是一簇紅色的火焰。追求生活的多姿多彩,讓生命的最後一刻仍顯現光華,我想,這是我應該追求的人生。
有朋友聽說我要去西雅圖,告訴我那是一個很浪漫的地方,一部有名的電影《不眠的西雅圖》(Sleepless in Seattle)展示了那裡的風情。那會兒我不曾看過那部電影,而且在西雅圖的日子裡,大半時間呆在圖書館裡,所以沒怎麼體會到西雅圖的浪漫。不過我很喜歡那兒咖啡館的氣氛。
西雅圖的咖啡很有名。我在美國買過一件襯衫,上面有三個圖案,第一個圖案就是一杯咖啡,據說美國人一看就知道是西雅圖買的。雖說我愛喝咖啡,但對咖啡沒有研究,不知道西雅圖的咖啡有什麼獨到之處。但那兒的咖啡館確實與澳大利亞不一樣。它無處不有,而且常常會出現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說,書店裡一定會有咖啡角,座位還很講究,有一般的硬座椅,也有舒適的大沙發。顧客們可以買杯咖啡放在茶几上,到書架上找本最新的雜誌翻翻。我去過大學附近的一家大書店,裡面居然有一個能容五六十人的咖啡廳。不少學生買杯咖啡坐在那裡看書,做作業,也有學生在沙發上小憩。書店裡的咖啡館充滿了書卷氣,有一種進去了就不想出來的感覺。
如果說書店裡的咖啡店是文人們聚集的地方,超級市場的咖啡店便是家庭婦女們聊天的好場所。每次去買菜,都能在市場的角落裡看到熱氣騰騰的場面,尤其在天冷的時候。壁爐裡燒著的柴火劈啪著響,熟人朋友各端一杯咖啡,聊得熱火朝天。很多人到那兒並不為買東西,只為會會朋友,或是坐坐,消除一下疲勞。西雅圖的人說他們一天不上咖啡館,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我在西雅圖接觸的人不多,總的印象是那裡的人很熱情很直率。有一天,我正趕路時,一位中年婦女叫住了我:「請問,你的鞋是在哪兒買的?」我一下沒有反應過來。她圍著我轉了兩圈,連連說:「這正是我要找的鞋,這正是我要找的鞋。」原來她看上了我的鞋。「對不起,我是在澳大利亞買的」。「是嗎?」她顯然很失望。「澳─大─利─亞,太遠了。」走了幾步後還回頭望了我(準確地說,是望了我的鞋)一眼。
我在綠湖邊的一戶美國人家裡住了兩個星期,房東及房東太太均已退休多年了。他們的家很大,有三套房間可以出租。因為離大學近,他們接待的通常是大學老師或訪問學者。他們接待過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人,而我是他們接待的第一個華人。
老兩口的精力十分充沛,一天到晚手腳不停,比我還忙。他們的社會活動很多,除了教堂的活動以外,還有兩項大的活動:種菜和跳舞。在他們的居民區裡,有一塊公用的土地。政府把這片土地劃成小塊,免費讓居民們種菜。房東夫婦每隔一兩天就會到菜地幹幾個小時的活兒,然後帶回來一大堆菜和一大堆消息:什麼瓜已開了花,什麼菜再有一個星期就可以吃了,諸如此類。我是自己開夥,但沒少吃地裡的菜。美國的瓜特別多,形狀也很特別。我吃了不少,可惜都沒有記住名字。吃得最開心的是剛剛掰下來的玉米棒,放在鍋裡蒸上三兩分鐘就行了。那股清香,真沒治。
週末的舞會兩口子是從不缺席的。到這一天,房東太太便要刻意打扮一番。換掉長褲,穿上裙子。據他們介紹,舞會是一個國際性的舞蹈團體舉辦的,這個團體定期組織舞會,並教授各國的民間舞蹈,他們已經學過泰國和日本舞了。不管他們去到哪個國家,都可以找到這個組織的分會,都可以去參加舞會。
房東太太退休前是某個大專的地理老師,愛好旅遊,幾乎每年都要和一群搞地理的同行們出國一遊。她去過中國,也到過澳大利亞。她曾給我放過她在澳大利亞拍的幻燈片,絕大多數拍的是岩石。
老太太已經七十五歲了,但對生活充滿著激情。她告訴我幾年前她學會了寫詩,現在還常常練筆。談起學寫詩,她十分感激她的啟蒙老師。「我的老師很年輕,只有二十多歲。她教我們如何欣賞詩歌,並說如果自己會寫詩,就能更好地欣賞。她講了詩的基本規律,然後要我們練習。我交給她第一篇詩歌時,她當著同學們的面一把抱住了我,說,你的詩寫得太好了。那時我才知道,自己居然會寫詩。」
老太太結過三次婚,第一次是在婚後三十一年以後以離婚為結局的。第二次婚姻只有五年,可這五年對她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她遇上了她一生中所認識的男人中最好的一個。第二任丈夫是某地理雜誌的編輯,他倆算是同行。她給我講了他們相識時的一件趣事。一天,她給編輯寄出了第一份情書,自認為的那份情書寫得十分動人,她期待著一封同樣動人的回信。好不容易盼來了回音,打開一看,情書居然被退回來了,上面還用紅筆作了不少修改,包括拼寫錯誤。後來她才知道,她的編輯先生出於職業習慣,拿起情書就改,而且照規矩寄還作者,真叫她哭笑不得。「那五年實在是太幸福了。雖然大多數的時候我們分居兩地,但我們的心每分每秒都在一起。」聽到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如此動情,我真是感動。可惜那位編輯在一次醫療事故中喪生。
「我五年前又結了婚,我覺得每結一次婚都象重新活了一次。」老人講得不錯,老倆口比年輕夫婦還親熱。我在的時候,他們正在裝修房子,正在計劃今後的生活。
兩個星期以後,華盛頓大學的一位教授邀請我住在她家,我便離開了兩位老人。教授的丈夫曾是一位有名的日本漢學家,十來年前因病逝世,留下一個女兒。女兒在哈佛大學畢業後,參加工作離開了家。
教授在學術界很有名氣。在一般人的眼裡,這種事業成功的人多是書呆子,教授卻不是。她是一個非常有生活情趣的人:愛好音樂,學過鋼琴,家裡擺了不少畫有五線譜的各種裝飾品。門口擺著畫有五線譜的擦鞋墊,門上掛著五線譜狀的風鈴。餐廳的桌上擺著四個墊碗的銅製品:一架鋼琴,一把小提琴,兩塊五線譜模型,一圓一方。客廳沙發墊上的圖案是五線譜,玻璃杯上的圖案也是五線譜的。總而言之,她的世界充滿了音樂。
教授還愛花草,家裡擺滿了奇花異草。誰都知道蘭花難種,可她就種得好。我去的時候,兩盆蘭花競相盛開,有一枝上居然有十一朵花。住久了,就知道教授的花為什麼種得好了,她是以研究學術的精神來研究花,書買了一大遝兒,並認真地實踐。有一次,我陪她去買花兒,售貨員無法問答她的問題,找來花店的技術人員,仍無法作答,那位技術人員很驚訝教授對花的知識之豐富。每當夜深人靜,教授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後,就會去澆澆水,伺候伺候她的花。
雖說教授到美國已經幾十年了,但基本還是保持著華人的傳統習慣。週末有空時,會邀請學生或朋友去飲茶,順便到唐人街買一些中國食品。做菜也是教授的一大嗜好,她給我看過自己訂制的一本菜譜,只有巴掌大,每一頁都用塑膠紙包好了,以防做菜時翻看弄髒。每每在朋友那兒吃到可口的新款菜,就會記下來,回家實踐。我做的湖南口味的剁辣椒,酸辣包菜得到她的賞識,這兩道菜的做法榮幸地上了她的私家菜譜。
在教授家住了四個星期,向教授學到了不少東西:學問,做人,還有對生活的熱愛。
西雅圖是一座美麗的城市,景美,人亦美。
注:本文寫于1998年,曾在悉尼的《東華日報》上發表,有刪改。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客居小唱的圖書 |
 |
客居小唱 作者:湘月 出版社: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06-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76 |
中文書 |
$ 176 |
現代散文 |
$ 180 |
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客居小唱
作者近三十年客居異國、小住他鄉的生活故事,一本完全不同以往的深度旅遊記事文學。
◎作者筆下娓娓道出的歐遊記事,讓讀者彷彿跨越時空,走進充滿藝術氣息的歐洲。
◎小住巴黎半年,從品嘗乳牛的「甲狀腺」等生活瑣事寫到幽默的乞討者等社會百態。
◎以「客居者」的角色分享異國的人文、社會、語言等差異所帶來的各種文化衝擊。
◎深入介紹赫爾辛基、聖彼得堡、蘇黎世、南歐和北歐的行程,以及當地特色。
這不是Long stay的田園調查,也不是走馬看花的遊記。作者通過入住公寓式旅館的小住方式,在欣賞異國風光的同時,也面對柴米油鹽、關注衣食住行。到超市買食材自己做飯,像個本地人一樣坐在咖啡館裡欣賞來來往往的人群,走街串巷體驗民風民情,創造機會與當地人交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一本真正帶領讀者進入當地人文與生活的旅遊記事。
怎麽會和法國總統家相鄰?「總統的小米飯」滋味如何?
逛聖彼得廣場撞見羅馬教皇是怎麼一回事?
電影《羅馬假日》的情景又是什麼樣的體驗?
拜訪丹麥安徒生的故居,沿途都是童話中的五彩小房子,
真的讓人有進入了安徒生筆下世界的感覺嗎?
《客居小唱》記載了一個客居者而非旅遊者的故事,其中固然包含奇山異水帶來的興奮和驚喜,名勝古跡和各種藝術形式所給予的激動和震撼,但更多的是作者身為客居者的見聞與思想。是在異國他鄉與友人或路人的各種交流──文化衝撞、語言尷尬、有趣的邂逅等等,而得到的一次又一次的感動和啟迪……
在佛羅倫薩參觀博物館的導遊說:「美的是佛羅倫薩。」指「很多人說羅馬美,我不以為然,美的是佛羅倫薩。」我當時很驚訝,因為她說的不是佛羅倫薩比羅馬更美。
一個晚上的小住,可能引起你對某件事情的深思;
一個陌生人的隻言片語,可能讓你終身受益。
章節試閱
「雞同鴨講」的尷尬與愉悅
聽過不少對法國人的批評,其中之一是他們多不會說英語,即使會說的也只和你說法語云云。我覺得此說有失公允,上別人家做客,只能客隨主便,入鄉隨俗。再說交流的手段不只是語言,其實「雞同鴨講」也有它特別有趣的地方,既尷尬又開心。
1996年第一天去巴黎坐地鐵時,進了地鐵站就糊塗了,不知東南西北。看到一個長得像華人的姑娘,便上前問路。她果然有四分之一的中國血統,會說一兩句英文,一兩句廣東話。可寒暄之後,就無法深入了。她拿著地圖嘰裡呱啦說了半天,我一個字也聽不懂。猜想她是說要轉車,可我...
聽過不少對法國人的批評,其中之一是他們多不會說英語,即使會說的也只和你說法語云云。我覺得此說有失公允,上別人家做客,只能客隨主便,入鄉隨俗。再說交流的手段不只是語言,其實「雞同鴨講」也有它特別有趣的地方,既尷尬又開心。
1996年第一天去巴黎坐地鐵時,進了地鐵站就糊塗了,不知東南西北。看到一個長得像華人的姑娘,便上前問路。她果然有四分之一的中國血統,會說一兩句英文,一兩句廣東話。可寒暄之後,就無法深入了。她拿著地圖嘰裡呱啦說了半天,我一個字也聽不懂。猜想她是說要轉車,可我...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序言
《客居小唱》記載的是作者近三十年來客居異國或小住他鄉的故事。我1987年離開中國到澳洲求學,後定居墨爾本,其間有過不少出國的機會,尤其是我和先生都退休以後。我本人去得最多的城市是巴黎,前後五次,最長一次呆了半年。本書所謂客居,指的是小住中國和澳洲之外的國家。
本文集分上下兩篇,上篇記載的是2001年7月到12月客居巴黎貴婦街半年的經歷,凡不在這個時間段裡發生的故事文中會有說明。下篇介紹的是1991年起在其它不同城市小住的花絮。集子裡的文章體裁不一,有2018年以來根據當年的日記整理而成的隨想劄記,也有2018年...
《客居小唱》記載的是作者近三十年來客居異國或小住他鄉的故事。我1987年離開中國到澳洲求學,後定居墨爾本,其間有過不少出國的機會,尤其是我和先生都退休以後。我本人去得最多的城市是巴黎,前後五次,最長一次呆了半年。本書所謂客居,指的是小住中國和澳洲之外的國家。
本文集分上下兩篇,上篇記載的是2001年7月到12月客居巴黎貴婦街半年的經歷,凡不在這個時間段裡發生的故事文中會有說明。下篇介紹的是1991年起在其它不同城市小住的花絮。集子裡的文章體裁不一,有2018年以來根據當年的日記整理而成的隨想劄記,也有2018年...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言
上篇
客居巴黎貴婦街
與法國總統家相鄰
辦法國臨時居留卡
職場趣事
得發誓需付費的圖書館
我的法語老師
方正端莊的沙發罩
巴黎的早市
嘗試法國菜
乳牛的「甲狀腺」
法國餐前酒Kir
和乳酪結緣
傳統名菜「納瓦里諾」
吃飽了不想家
巴黎人的衣著
那年流行粉紅色
聰明的乞討者
街頭藝術家
一張特殊的郵票
盧森堡公園
巴黎的狗及其公墓
走進莫內的花園
駿馬博物館
跳蚤市場
八個「模特兒」妻子
小澤征爾神奇的手
精神貴族
「雞同鴨講」的尷尬與愉悅
拜訪巴黎警所
走街串巷
在巴黎遇到的華人
巴黎人的浪...
上篇
客居巴黎貴婦街
與法國總統家相鄰
辦法國臨時居留卡
職場趣事
得發誓需付費的圖書館
我的法語老師
方正端莊的沙發罩
巴黎的早市
嘗試法國菜
乳牛的「甲狀腺」
法國餐前酒Kir
和乳酪結緣
傳統名菜「納瓦里諾」
吃飽了不想家
巴黎人的衣著
那年流行粉紅色
聰明的乞討者
街頭藝術家
一張特殊的郵票
盧森堡公園
巴黎的狗及其公墓
走進莫內的花園
駿馬博物館
跳蚤市場
八個「模特兒」妻子
小澤征爾神奇的手
精神貴族
「雞同鴨講」的尷尬與愉悅
拜訪巴黎警所
走街串巷
在巴黎遇到的華人
巴黎人的浪...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