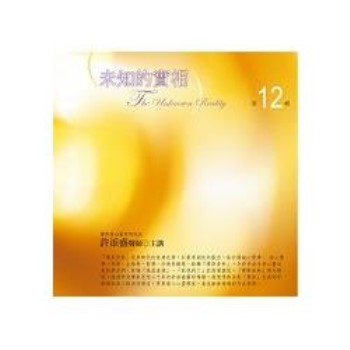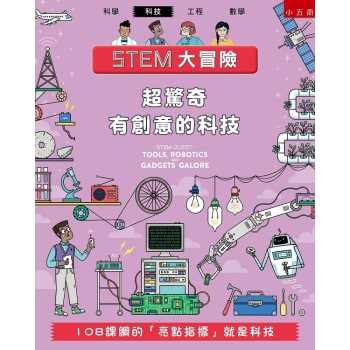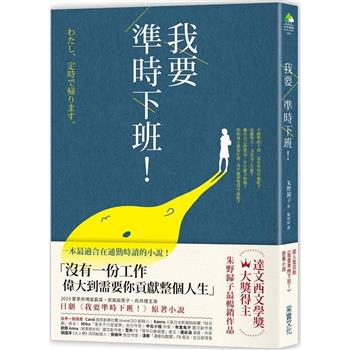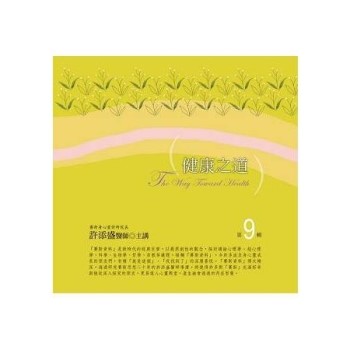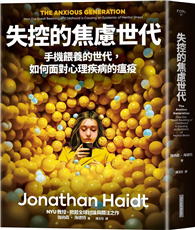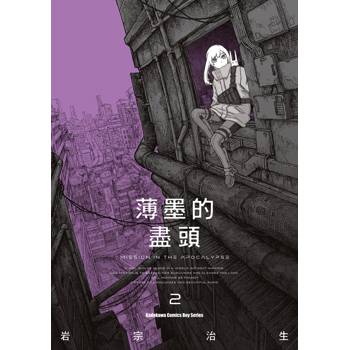金花巷到外婆橋
金花巷,因巷內的金花聖母小廟而得名。
這是我的出生地,由坐藤製的娃娃車,到趴在地上牙牙學語,繼而獨自步行上學,我的第一段人生旅程,就在這條位於西貢第一郡阮文森街(法屬時代叫羅腰街)金珠戲院左鄰的巷子渡過。
如果每一條長巷都是一條小河,那麼金花巷於我,好比一條夾岸開滿金盞花,入夜有很多童夢星辰點綴其間的回憶小河。
幼年最愛坐門檻,雙手捧腮,仰望天空發呆,巷子是L字型,所以天空映入我的眼簾也呈L形,緩緩移動的雲朵,彷彿從一個L型模具擠壓出來,有著法文Lenteur(緩慢)的L,相對車水馬龍的囂鬧大街,長巷是一個慢半拍的小宇宙,跟不貼時代的脈動,卻留住很多魂牽夢縈的故事。
每戶門前都有一條淺淺的明渠,把各家門口串連成一條直線,每逢大雨天,明渠水流變急,我常冒雨把摺好的紙船放逐到流水,再躲回屋簷下目送紙船一路踉蹌溢出視線外。我還會給紙船搭載一個小紙人,由他來扮演浪跡天涯的冒險家船長。
夜裡,依偎母親身邊,帶著對紙船的牽掛,我呼呼進入夢鄉。
大詩人泰戈爾的《紙船》可用來形容我童年的細膩感受:「夜來了,我的臉埋在手臂裡/夢見我的船在子夜星光下緩緩地浮泛前去/睡仙坐在船上,臂彎挽著滿載著夢的竹籃子。」
金花巷何止有星光,我家還給全巷街坊見識什麼是熒光燈電器!
祖母說,父母結婚時,在東方匯理銀行任職的父執袁世伯,送來一支熒光白電管,父親找來電器師傅安裝,當燈管一亮,全巷有些騷動,好奇街坊都跑來我家門外張望,因大家用的是鎢絲燈泡,昏黃而微弱,一旦見到日光燈,眼睛也都跟著發亮,並且嘖嘖稱羨。
每條巷子通常都會有一名很難相處的惡鄰居,金花巷四號的越南鄰居正是這類人,他是退休衙差,作威作福慣了,善良坊眾背後叫他老虎公。
二戰時的金花巷並非家家戶戶有電力供應,老虎公憑著當過衙差的特權,給自己家弄了一個電錶,全巷僅他一家可自街外引進電力,左鄰右里只好求他准予搭電,老虎公論燈泡數量來算緊每一分錢,窮戶付不起錢就全屋只用一個25火燈泡,燈泡再微弱,總勝過點油燈。
巷內每戶人家的燈泡都套上一個峴殼形狀的玻璃燈罩,用鏈子繫在天花板,可調校燈罩的高低,不夠亮就把燈罩往下拉近一點。老實說25火燈泡有等於無,一枚硬幣掉到地上,休想找得回。
刻薄成性的老虎公收了電費還要限制用電,晚上11時他出門巡視,誰家屋內仍亮燈,他就在誰的門外大聲咳嗽!所以每晚五音鐘報時響過11下,金花巷就如童話裡中了魔法的城堡,一瞬間家家戶戶沉睡無聲。
為了打破老虎公的電力壟斷,家父發動坊眾聯署請願信,先求大業主黃榮遠堂授權,再由家父拜託他的法國銀行同事菲利普,把有關函件轉呈其在電力局任高職的父親,希望當局為巷內各家各戶安裝電錶,想不到沒幾個星期就馬到功成,從此電力直接傳送各家各戶,誰家要裝多少個燈泡都不再有問題,人人額手稱慶,如同在黑暗枷鎖之中解放出來。
家父何止給金花巷帶來光明,他還給全巷的人帶來自來水。在今天來說,這兩樣東西太微不足道,但在那個生活維艱的舊年代,獲得電力和自來水,乃生活的「大躍進」,所以家父算不算「偉大雷鋒」?
未有自來水之前,坊眾日常用水須靠兩個公共水龍頭,每天祖母姑姐母親要排隊挑水提水,老虎公是太上皇,無需排隊,他每天優先把自家儲水缸裝滿,把門口兩株萬年青灌飽,才開放水龍頭給大家輪候使用。
父親為此再次串聯街坊向黃榮遠堂投訴,問題又迎刃而解,殖民當局派人來給巷內各個住戶安裝自來水管及獨立水錶,從而結束老虎公對水源之獨霸。那時大業主只顧收租,常忘記改善租客居所的設施。
我有一位鄰居,他今天在台灣很出名,自由僑聲久不久就有他的畫展報導,其大名叫林壽山,赴台升學之前,住在巷內15號。幼年每逢黃昏,洗好了澡的我就溜進他家的「廊廳」,看他揮毫練畫,他是廣肇母校何瀨熊老師的高足,自幼勤習書畫,其在嘉隆街舉辦的第一次個展,開幕那晚,我家全體總動員,搭的士前往捧場呢!
巷口的金花廟,香火不弱,善信都說金花聖母很靈,其實這是老虎公的宣傳伎倆,說穿了,金花廟不過是老虎公的私人斂財工具。善信不但捐香油,還獻上首飾金鏈作供品,變相養肥該衙差老虎。
某天,巷內人人交頭接耳,似有事發生,而老虎公則暴跳如雷,原來金花聖母的玻璃神龕被打破,塑像身上的金鏈不翼而飛!究竟是誰那麼斗膽竟然老虎頭上釘虱乸?可能為金鏈失竊而生氣過度,老虎公過沒多久就兩腳一伸見金花菩薩去了,舉殯之日全巷街坊都要送殯,父親還戴著帽子前往,預防老虎公家眷強迫每個執紼人須在額頭綁上白布條。
大家還記得「欄尾」之名稱否?故居的屋後有一座露天柴房,即為我家的欄尾,後來才知,欄尾的前世今生,其實就是一條戶戶相連的屎坑巷。不過我家的屎坑巷不臭,還鳥語花香呢,四季盛開的紙花常翻牆闖進我家的欄尾搔首弄姿。可惜欄尾經常有毛茸茸大老鼠出沒,更有喜歡擾人清夢的老虎貓,喵喵喵叫個不停,使得欄尾在夜深時分顯得有點詭異!
我出世那年,金花巷尚未有排糞下水道,人們如廁須使用馬桶,辦法是登上一座下置小木桶,高約兩三梯級的水泥小台。深夜會有倒夜香大叔拉著掛有小油燈的木頭車,沿著「屎坑巷」給各家各戶清理馬桶。祖母說倒夜香大叔是開罪不得的,他若跟你賭氣,把馬桶放歪,糞便掉到馬桶外,一屋子就會瀰漫「巴黎之夜」的香氣。
殖民時期有一名華人孖薦專責市府的倒夜香事務,他叫譚焯軒,外號是「夜香孖薦」,工作雖不高尚,但其民生貢獻,值得褒揚。譚先生跟另一位叫香玉堂的人,合稱國民黨孖寶元老,二人對公益出錢出力,不落人後。香玉堂是香達記搓香莊東主,外號「滿頭香粉」,跟「夜香孖薦」均是以「香」馳名,兩人不啻「越南楚香帥」,可媲美香港鄭少秋。
法國人告別越南之前,做了一件大好事,就是完成西貢嘉定的排污系統鋪設,從此馬桶及倒夜香均走進歷史,《夜來香》更成絕響矣(作曲人黎錦光因陶醉午夜的「窗外芬芳」,而譜出《夜來香》這首經典曲,夜來香與夜香,只差一個來字,意境卻有天淵之別)。
若非一牆之隔,我家天井跟潮州街菠蘿巷是相連的,不算高的磚牆,是擋不住鄰巷傳來的雞鳴犬吠,呼爹叫娘之日常嘈雜。
我常憑聲音去想象牆另一頭的世界,有好幾次鄰巷的三姑六婆發生口角,罵戰由上午直落下午,同屋的大哥哥攀上木凳再豎起腳跟去看牆外的熱鬧,年幼的我只能滿足於「隔牆有耳」的八卦。
雷雨夜的天井也很聒噪,雨點打在玻璃窗,彷似毛躁漢子在發洩內心的澎湃情緒,令人憶起粵語片那些很白燕、很黃曼梨、很余麗珍的行雷閃電,風雨交加的苦情鏡頭。
無雨之夜,隔牆的中華學校及高大榕樹,就是我家天井夜空的兩大構圖元素。一彎峨眉月會在烏雲消散後前來湊興,像玩單杠的頑皮孩子把自己倒掛在中華學校的人字屋簷角,而巍峨的校舍有幾分像傳說中的廣寒宮,大榕樹在月明之夜就是我所幻想的大桂樹,唯獨不見嫦娥及吳剛。
若逢望月,精神飽滿的月亮會利用高大濃密的樹影,跟地面寂寞的我玩起捉迷藏,此時此刻,月亮與我家天井距離最近,我想如果家中有一座小天台,只消登上天台就可觸摸月亮的臉蛋。母親每晚總是忙著給人縫製大襟衫及洋裙子,她一邊工作一邊哼著周璇的《月兒彎彎照九州》《明月千里寄相思》,把安靜的天井襯托得恍似蓋上一張銀色的綢緞——夜,以我家最溫柔!
中華學校的越文晚班辦得很成功,學生以在職人士居多(任教博愛和遠東的阮金鳳老師年輕時曾在該校兼課)。當夜校的瑯瑯書聲傳來,我雖未入學,還是懂得翻開「牛羊草花,樹鳥門窗」幼兒讀本要母親或三姑姐帶領一起唸。遲睡的晚上,我還聽到該校傳來陣陣口琴聲,把長夜襯托得格外空寂,如今思之,頗有《杏花疏影裡,吹笛到天明》之低徊。
後來長大,才知童年所聽到的夜半琴音,是來自該校莫老師和他的兩個兒子,父子三人於散學後就開始練口琴。舊時的男生常在褲子後袋插一件東西,要不是梳子,就是口琴,那時玩結他的人不多,大家一窩蜂醉心口琴。莫老師是一位籃球健將,他太太姓呂,畢業廣州中山大學,乃富家千金小姐,聽說兩人拍拖遭女方家長反對,為了追求自由戀愛,於是雙雙私奔來越,執教鞭為生。莫老師熱衷政治,兩子分別叫莫托夫和莫里尼,跟蘇聯的莫洛托夫、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是同名。
假如大街是一條滾滾而流的大江,那麼踡縮在都市心臟的長巷,該是一條午寐的小河。如上文說的,長巷的節奏永遠慢半拍,在這裡有點避秦的味道,老唐山留下來的風俗習慣,在這裡獲得了良好沉澱。
年終歲晚,巷子最忙碌,家家戶戶大掃除,跟著就是送灶君,然後把臘鴨臘腸跟通勝一塊高高掛起來(故坊間說掛臘鴨是指上吊)。端午節來了,每家都在戶外繫上一束菖蒲來辟邪,過節當天就煮湯給孩子沖涼,唱龍舟歌的大叔亦挨家逐戶來湊興,大叔雙手舞動小龍舟,用濃重鄉音唱出善禱善頌的歌謠,為的是向屋主討個吉利紅包。
輪到乞巧節,巷內妹子就為「七姐盤」的牛郎織女擺設忙個不亦樂乎。中元節晚上大家焚燒金山銀山,許多摩拳擦掌的孩子圍上來,當主人家撒幣,大家一哄而上,火光把每張興奮的小臉蛋照得通紅。中秋節的金花巷,儼如一條流動的熱鬧燈河,用空奶罐和線轆製成的滾動燈籠最搶佔風頭,得得得的響聲像開機關槍,向四方八面掃射節日的歡樂子彈。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南城瑣夢的圖書 |
 |
南城瑣夢 作者:郭乃雄 出版社: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01-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南城瑣夢
在回憶裡重現昔年的越南,茶香氤氳間,看這些年的人世變換
◎作者在新聞領域及報導文學中耕耘多年,練就入微的觀察及細膩的文筆,字裡行間織成無數畫面,猶如往日重現。
◎慵懶的午後,寂靜的深夜,一杯茶、一本書,帶你看一段人世風光。
◎書末以全彩印刷呈現珍藏多年的歷史照片,給予讀者更加直觀的感受。
郭乃雄成長於越戰年代,大眾傳播系出身,1978年以難民身分定居法國,在歐洲從事新聞工作歷30寒暑。學問廣博,閱歷豐富,以十數年心血,用文字打撈沉澱於記憶深潭的神祕箱子,掀開裡面藏著鮮為人知的眾多祕辛,是懷舊,也是笑看一個時代。
瑣夢如窗,往事似酒。
每一趟的回憶,就是每一季的深秋。
每一次的穿越,就是每一晚的無寐。
循著《南城舊夢》的足跡,《南城瑣夢》今天翻山涉水而至了!
14篇散文小品,記述往年在越南生活的點點滴滴。
往事在午夜低喃裡歷歷在目,猶如夢迴當年。
作者簡介:
郭乃雄
成長於越戰年代,大眾傳播系出身,1978年以難民身份定居法國,在歐洲從事新聞工作歷30寒暑。退休後致力報導文學,2016年出版過《南城舊夢》,2020續推出《南城瑣夢》《南城驚夢》,目的讓舊夢系列的紙船繼續在回憶大海上漂航。較諸舊作,新書內容更加豐富,耗盡作者十數年心血,一點一滴地匯聚,也像百家被子一針一線去做補遺,保證讀者前所未讀,前所未聞,前所未知。在此,由衷感謝與我結伴同行的創作夥伴,他或她,均為舊夢系列書的半個孕育者。懷舊,就是流浪!青春,就是回憶!揮別往事,只需一秒鐘,若完全忘記,那就得耗費一輩子了。
章節試閱
金花巷到外婆橋
金花巷,因巷內的金花聖母小廟而得名。
這是我的出生地,由坐藤製的娃娃車,到趴在地上牙牙學語,繼而獨自步行上學,我的第一段人生旅程,就在這條位於西貢第一郡阮文森街(法屬時代叫羅腰街)金珠戲院左鄰的巷子渡過。
如果每一條長巷都是一條小河,那麼金花巷於我,好比一條夾岸開滿金盞花,入夜有很多童夢星辰點綴其間的回憶小河。
幼年最愛坐門檻,雙手捧腮,仰望天空發呆,巷子是L字型,所以天空映入我的眼簾也呈L形,緩緩移動的雲朵,彷彿從一個L型模具擠壓出來,有著法文Lenteur(緩慢)的L,相對車水馬龍...
金花巷,因巷內的金花聖母小廟而得名。
這是我的出生地,由坐藤製的娃娃車,到趴在地上牙牙學語,繼而獨自步行上學,我的第一段人生旅程,就在這條位於西貢第一郡阮文森街(法屬時代叫羅腰街)金珠戲院左鄰的巷子渡過。
如果每一條長巷都是一條小河,那麼金花巷於我,好比一條夾岸開滿金盞花,入夜有很多童夢星辰點綴其間的回憶小河。
幼年最愛坐門檻,雙手捧腮,仰望天空發呆,巷子是L字型,所以天空映入我的眼簾也呈L形,緩緩移動的雲朵,彷彿從一個L型模具擠壓出來,有著法文Lenteur(緩慢)的L,相對車水馬龍...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寒日蕭蕭上瑣窗,梧桐應恨夜來霜
酒闌更喜團茶苦,夢斷偏宜瑞腦香
瑣夢如窗,往事似酒。每一趟的回憶,就是每一季的深秋。每一次的穿越,就是每一晚的無寐。
循著《南城舊夢》的足跡,《南城瑣夢》今天翻山涉水而至了!
如果舊夢是秋日的醉人香醇,瑣夢又會是什麼呢?那是夜闌人靜苦而回甘的一壺龍鳳團茶!灌澆的,是心底那株老去的梧桐,搖落的,是夜來髮梢的霜白,還有一絲絲瑞腦的芬芳。
回憶,一定離不開舊日的美食,只因那時我們既傻氣又年輕。
化身一張無形的漁網,《南城瑣夢》在透明如鏡的歲月海洋,打撈所有吃的回憶,包...
酒闌更喜團茶苦,夢斷偏宜瑞腦香
瑣夢如窗,往事似酒。每一趟的回憶,就是每一季的深秋。每一次的穿越,就是每一晚的無寐。
循著《南城舊夢》的足跡,《南城瑣夢》今天翻山涉水而至了!
如果舊夢是秋日的醉人香醇,瑣夢又會是什麼呢?那是夜闌人靜苦而回甘的一壺龍鳳團茶!灌澆的,是心底那株老去的梧桐,搖落的,是夜來髮梢的霜白,還有一絲絲瑞腦的芬芳。
回憶,一定離不開舊日的美食,只因那時我們既傻氣又年輕。
化身一張無形的漁網,《南城瑣夢》在透明如鏡的歲月海洋,打撈所有吃的回憶,包...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
金花巷到外婆橋
洋場金粉番衣街
春風化雨華教淚
買辦名人祕聞錄
滿城盡帶黃金甲
餐搵餐食餐餐有
湄河美食風情畫
茶樓粉麵頰留香
牛丸牛火君子好
麵包糕餅黑咖啡
扇傘時尚文藝情
公仔書與小說迷
球王棋仙鬥雞經
戲夢人生笑風月
金花巷到外婆橋
洋場金粉番衣街
春風化雨華教淚
買辦名人祕聞錄
滿城盡帶黃金甲
餐搵餐食餐餐有
湄河美食風情畫
茶樓粉麵頰留香
牛丸牛火君子好
麵包糕餅黑咖啡
扇傘時尚文藝情
公仔書與小說迷
球王棋仙鬥雞經
戲夢人生笑風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