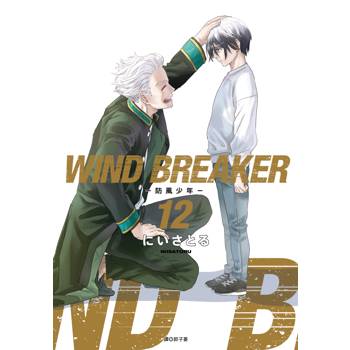久, 可以是時間;
久, 可以是空間。
可以是停步、注視,
看向內心,理解生命。
久,音比較纏綿,筆畫少,不常當錯別字,卻也不容易寫得漂亮。
外表純粹一些,情意比較綿長,不算出色受矚目,但獨特。這是我自己。
有人閱讀我的書,是從國中高中,一直到現在已為人父母。這是一種久。
看我的散文,要細,要靜,也需一種久,而我的書寫,時長,日也久。
因為久,時空都拉緩拉長拉立體了,常與變,業與懺,因與果,消逝與新生,也才能看得真,悟得清。
而我的入世法則一向就是同情與理解。這需要久,久久,久久。
本書特色
1.石德華歷時三年的散文新作。歷經三年的沉澱,歷經親人告別與新生命的誕生。散文作家石德華以她特有的溫暖筆觸,寫下她對於久的體悟。她說:書寫文章要久,體驗人生也要久,而品味她的文章,擁有同樣的理解與感觸,更需要久,久久,久久久久。
2.本書每篇篇末,皆開設石德華文學課,以她獨到的筆觸,闡述書寫散文的靈感泉與下筆技巧,提供給需要散文寫作的讀者另一扇繆思之門。
|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看我,久久久久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看我,久久久久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石德華 (1955~ )
湖南新寧人,出生於臺灣苗栗,1961年舉家遷居彰化,現居住臺中。A型,天蠍座。持續創作中。
曾獲第二屆梁實秋文學獎散文首獎、第三屆中央日報文學獎小說獎第三名、第三屆梁實秋文學獎散文第三名、第二屆台灣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
著有:校園勵志散文《校外有藍天》、《典藏青春與愛》、《青春捕手》、《新好女孩新好男孩》;生活散文《很溫柔的一些事》、《靜靜的深海》、《懂得》、《時光千噚》、《約今生》、《火車經過星河邊》;小說《愛情角》;新新古典小說《西廂記》、《長生殿》。
石德華 (1955~ )
湖南新寧人,出生於臺灣苗栗,1961年舉家遷居彰化,現居住臺中。A型,天蠍座。持續創作中。
曾獲第二屆梁實秋文學獎散文首獎、第三屆中央日報文學獎小說獎第三名、第三屆梁實秋文學獎散文第三名、第二屆台灣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
著有:校園勵志散文《校外有藍天》、《典藏青春與愛》、《青春捕手》、《新好女孩新好男孩》;生活散文《很溫柔的一些事》、《靜靜的深海》、《懂得》、《時光千噚》、《約今生》、《火車經過星河邊》;小說《愛情角》;新新古典小說《西廂記》、《長生殿》。
目錄
Chapter01 看我
掩不住我的情意 012
杯裡的擁抱 018
人生若只如初見 024
這種經驗不知你有沒有過? 032
CAN HELP 039
不說 046
我的摯友艾瑞克和魯卡斯 054
我弟 060
基本咖 066
我的遺書練習曲 070
我發現 074
收藏 081
跨度 092
我的除夕初一到十五 098
富貴寶 103
【石德華文學課】看我‧散文就是我 108
Chapter02 凝視
一直,是因為有方向 110
日光是日光,月色是月色 120
他在她的城市寫歌 126
同在時間的一個微點 132
就是愛媽祖 137
說話 147
在座 153
鳶尾草教我的一些事 162
天臺上 170
現在,就是最好的時刻 179
遍食人間煙火 187
【石德華文學課】凝視‧真正的看見 192
Chapter03 流眄
滄溟一戰收,心路史家論 194
孤拔元帥與小遊客 207
中華路七十三巷 226
【石德華文學課】流眄‧他鄉的愛 238
Chapter04 我看
手寫的從前 240
左外野 245
我能力所及,我管轄 250
喜歡和月亮 256
停步,注視 262
致愛情 268
說再見 275
明白了 281
在雲道咖啡館讀詩 288
天孤星 294
【石德華文學課】我看‧自己的戀 319
掩不住我的情意 012
杯裡的擁抱 018
人生若只如初見 024
這種經驗不知你有沒有過? 032
CAN HELP 039
不說 046
我的摯友艾瑞克和魯卡斯 054
我弟 060
基本咖 066
我的遺書練習曲 070
我發現 074
收藏 081
跨度 092
我的除夕初一到十五 098
富貴寶 103
【石德華文學課】看我‧散文就是我 108
Chapter02 凝視
一直,是因為有方向 110
日光是日光,月色是月色 120
他在她的城市寫歌 126
同在時間的一個微點 132
就是愛媽祖 137
說話 147
在座 153
鳶尾草教我的一些事 162
天臺上 170
現在,就是最好的時刻 179
遍食人間煙火 187
【石德華文學課】凝視‧真正的看見 192
Chapter03 流眄
滄溟一戰收,心路史家論 194
孤拔元帥與小遊客 207
中華路七十三巷 226
【石德華文學課】流眄‧他鄉的愛 238
Chapter04 我看
手寫的從前 240
左外野 245
我能力所及,我管轄 250
喜歡和月亮 256
停步,注視 262
致愛情 268
說再見 275
明白了 281
在雲道咖啡館讀詩 288
天孤星 294
【石德華文學課】我看‧自己的戀 319
序
作者序
久
1
久,音比較纏綿,筆畫少,不常當錯別字,卻也不容易寫得漂亮。
外表純粹一些,情意比較綿長,不算出色受矚目,但獨特。這是我自己。
2
有人閱讀我的書,是從國中高中,一直到現在已為人父母。這是一種久。
自我了解,需要時間,需要功力。
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溝通,其實也是難事。
這是個需要利與攀的世間,計利與攀緣是功用性的,數算性的,而我個人,一向只能專注做好自己的事,沒能力給利與拉抬,除非你能看我久一點,才能知道我的無用之用。
而人總是很馬虎、主觀的評斷別人。但你如果看得不久,便無法深細;無法深細,便無法真正了解一個人;無法真正了解一個人,就是辜負。久,才能讓這一切不致於太過遺憾?
往來匆匆,擦肩而過,從不駐足留步,此生的意義會是什麼呢?駐足、注視,彼此有了聯結,新的意義便產生了,有人甚且記憶交集,彼此成為生命中的獨一無二。駐足、注視、交集、互動,愛與責任,馴服與了解,人生的意義原來在此。
而我的入世法則一向就是同情與理解。這需要久,久久,久久。
看我的散文,要細,要靜,也需一種久,至於我的書寫,時長,日也久。
因為久,時空都拉緩拉長拉立體了,常與變,業與懺,因與果,消逝與新生,也才能看得真,悟得清。
3
他原本就美在那,等我們去將他收擷進自己的生命裡。旅行,就是這樣。
澎湖是我一去再去的地方,這兩年我也常有南臺灣的輕旅行,發現友伴及自己都不約而同在由衷輕呼:臺灣真美。沒來得及留下文字的,幸好有留影,生命總是不知短長,美的確定倒是不必遲延,尤其親見二○二○年全球疫情下的臺灣。於是在書中影像收進「臺灣之美」,圖與文並不完全相符,只為留下。
書稿交給出版社之前,我給人間福報副刊編輯覺涵法師一則Line:
「有人連著兩本書都感謝同一個人嗎?」
覺涵法師的催稿很厲害,即便他沒動靜,透過虛空你也知道他在等待,於是,偷懶散逸一下下就好,很快又自動坐直身子,電腦前一字一字Key過流光,我真的沒有新鮮詞,合十說的仍是這一句:「法師,謝謝你,沒你沒福報,我絕對寫不成書。」
也將這些年常有的一種心情,一併融入拌勻吧!用書中的一句話以達,那就是:
「行走,回家,仰頭,心中無比寧靜而飽滿,感受時光穿越過我,我突然很想很想,謝天。」
4
散文是我的斷代史,一本本,我的不回頭,我的彎弧跨度,我沉穩的悲傷,我無匹的壯遊,那,這本呢?
這本書呈現我從隔岸所觀照的日常,和它清澈倒映水面的入世信念。信念,有堅持,有抗拒。
我成也如此,敗也如此,始終護守著世間最有價值的久久久久:
意志力。專注力。誠信。善良。
久
1
久,音比較纏綿,筆畫少,不常當錯別字,卻也不容易寫得漂亮。
外表純粹一些,情意比較綿長,不算出色受矚目,但獨特。這是我自己。
2
有人閱讀我的書,是從國中高中,一直到現在已為人父母。這是一種久。
自我了解,需要時間,需要功力。
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溝通,其實也是難事。
這是個需要利與攀的世間,計利與攀緣是功用性的,數算性的,而我個人,一向只能專注做好自己的事,沒能力給利與拉抬,除非你能看我久一點,才能知道我的無用之用。
而人總是很馬虎、主觀的評斷別人。但你如果看得不久,便無法深細;無法深細,便無法真正了解一個人;無法真正了解一個人,就是辜負。久,才能讓這一切不致於太過遺憾?
往來匆匆,擦肩而過,從不駐足留步,此生的意義會是什麼呢?駐足、注視,彼此有了聯結,新的意義便產生了,有人甚且記憶交集,彼此成為生命中的獨一無二。駐足、注視、交集、互動,愛與責任,馴服與了解,人生的意義原來在此。
而我的入世法則一向就是同情與理解。這需要久,久久,久久。
看我的散文,要細,要靜,也需一種久,至於我的書寫,時長,日也久。
因為久,時空都拉緩拉長拉立體了,常與變,業與懺,因與果,消逝與新生,也才能看得真,悟得清。
3
他原本就美在那,等我們去將他收擷進自己的生命裡。旅行,就是這樣。
澎湖是我一去再去的地方,這兩年我也常有南臺灣的輕旅行,發現友伴及自己都不約而同在由衷輕呼:臺灣真美。沒來得及留下文字的,幸好有留影,生命總是不知短長,美的確定倒是不必遲延,尤其親見二○二○年全球疫情下的臺灣。於是在書中影像收進「臺灣之美」,圖與文並不完全相符,只為留下。
書稿交給出版社之前,我給人間福報副刊編輯覺涵法師一則Line:
「有人連著兩本書都感謝同一個人嗎?」
覺涵法師的催稿很厲害,即便他沒動靜,透過虛空你也知道他在等待,於是,偷懶散逸一下下就好,很快又自動坐直身子,電腦前一字一字Key過流光,我真的沒有新鮮詞,合十說的仍是這一句:「法師,謝謝你,沒你沒福報,我絕對寫不成書。」
也將這些年常有的一種心情,一併融入拌勻吧!用書中的一句話以達,那就是:
「行走,回家,仰頭,心中無比寧靜而飽滿,感受時光穿越過我,我突然很想很想,謝天。」
4
散文是我的斷代史,一本本,我的不回頭,我的彎弧跨度,我沉穩的悲傷,我無匹的壯遊,那,這本呢?
這本書呈現我從隔岸所觀照的日常,和它清澈倒映水面的入世信念。信念,有堅持,有抗拒。
我成也如此,敗也如此,始終護守著世間最有價值的久久久久:
意志力。專注力。誠信。善良。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