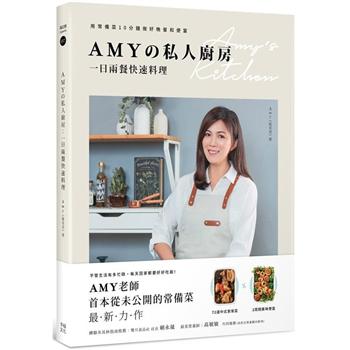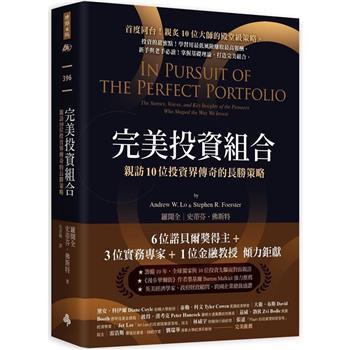嚴峫死死盯著那輛全黑色悍馬H2在包圍中遠去,牙咬得那麼緊,以至於生生咬出了血。直到最後一輛車消失在山谷重重的霧靄中,他才發著抖埋下頭,把臉埋在冰涼的掌心,額頭抵著粗礪的沙土碎石,卻全然沒有感覺。
他真的已經透支了,肝腸寸斷的劇痛淹沒了一切,肉體上的傷痛和流血都傳遞不到麻痺的神經末梢。
不知過了多久,身後傳來腳步聲,有人衝上來連拖帶拉地把他從灌木後扶了起來,二話不說立刻往遠處山林裡拽。嚴峫喘息著一看,只見來人體型十分瘦,頭戴鋼盔護目鏡、全身迷彩服,從頭髮到腳跟包裹得嚴嚴實實,但意外的是身上沒有背槍。
倉促中嚴峫只感覺來人十分眼熟,但根本看不清是誰。這時候他已經連問話的力氣都沒有了:「你……」
對方警惕掃視周圍,做了個噤聲的動作,一打手勢:「跑!」
就那短短一個字,嚴峫瞬間呆住了。
然而這時根本沒有任何猶豫的時間,車隊雖然走了,但誰也不知道黑桃K是否在原地留下了人等待狙擊手現身,或者乾脆殺個回馬槍。嚴峫踉踉蹌蹌隨對方穿過空地,一頭撲進山林,視野兩邊參天大樹漸漸密集,不知道撥開多少荊棘樹叢後,嚴峫的視線越來越花,前方所有景物都出現了明顯的重影,連那道穿迷彩服的背影都分裂成了兩三個。
「……呼呼……呼……」
他聽不見風聲和鳥鳴,只有自己的喘息重重鼓蕩耳膜,每邁出一步都感覺心臟被無形的利爪攥住,強行扭曲、緊縮,再扭曲、再緊縮……
撲通!
嚴峫在毫無知覺的情況下一腳踩空,他自己都沒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麼,整個人重重滾進了樹溝裡!
山林中的樹溝布滿碎石土坑,嚴峫只覺天旋地轉,下一秒額頭撞上了尖銳的東西,溫熱一下湧了出來,紅色的液體刷拉蓋住了視線。
是血。
他躺在地上,手腳痙攣,全身抽搐麻痺。那個穿迷彩服的立刻跟著趔趄地跳下溝來,似乎壓抑著低聲罵了句什麼,但嚴峫聽不清。
他的耳朵也被血蒙住了,連自己的喘息都彷彿隔著深水,朦朧又不清楚。
真狼狽,他心中突然掠過這麼一個念頭。
怎麼會這麼狼狽?比流浪狗還不如。
嚴峫咬緊牙關,搖搖晃晃從地上支起身。他額角到側頰劃出了一道長長的血痕,鮮血順著鋒利的眉角流下眼梢,隨著動作一滴滴掉在手背上,旋即被更多透明鹹澀的液體沖開。
下一刻,大股腥甜從氣管直衝喉頭,他「哇」地噴出了滿口血沫!
「!!」來人撲上來失聲道:「嚴隊!」
「……」嚴峫想說什麼,但眼前迅速發黑,不知不覺已經軟倒在了地面上。
他感覺自己彷彿墜入了冰冷的海水,眼睜睜望著世界旋轉上升,迅速遠去。迷茫、絞痛和絕望都化作虛無,伴隨著那個頭也不回的背影,消失在了漆黑的深海。
「……江……停……」他無聲地念道。
那刻骨銘心的兩個字帶走了他的最後一絲意識。嚴峫緩緩閉上眼睛,沉入了暗不見底的深淵。
**
越野車在前後護衛中開出山路,突然車載對講機響了,阿杰立刻抬手接通耳麥裡的頻道:「喂,說。」
不知通話那邊說了什麼,阿杰一愕,緊接著臉色沉下來:「我明白了。」
他按斷通訊,探身俯到黑桃K耳邊,藉著車輛行駛的轟鳴輕聲說了幾句,少頃黑桃K睜開眼睛「噢?」了一聲:「招子說只有一個人?」
「對,身材不高很瘦,像個女人。『招子』怕狙擊手還在,不敢太靠近,但確定那女人行動並不敏捷,身上也沒有帶任何狙擊槍一類的武器,扶起那姓嚴的就退回叢林了。」
黑桃K微微頷首。
阿杰皺眉道:「大哥,我們會不會被空城計給忽悠了?」
黑桃K默然不語,似乎也看不出喜怒。阿杰跟他很久了,知道這模樣基本就是要大開殺戒的表示,一時不由心下發緊,右手略微抬了起來,隨時準備打手勢下令車隊回頭。
然而足足等了一分多鐘,卻見黑桃K呼了口氣,笑著慢慢地重複道:「……空城計……」
他彷彿感覺非常有意思,突然他轉身問:「江停?」
江停沒有反應,他好像睡著了,光潔的眉心微微蹙著,似乎在睡夢中還很心事重重。
然而黑桃K卻知道他不可能睡著,阿杰也能從呼吸頻率、眼睫顫動和肌肉繃緊程度等最細微的差別中,看出他還清醒著這麼一個事實。
只是醒著也很不舒服罷了。
他這種體質,落水、槍殺、劇烈情緒波動,能撐到現在還沒作出病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下次見面時,你跟他就是生死仇敵了。」黑桃K含笑看著他,溫聲問道,「如果他帶警察來抓你,我就幫你殺了他,好嗎?」
許久江停才略微挑起眼皮,密密實實的眼睫之下流露出一絲微光,隨即又合上了,在幾道銳利的視線中低聲道:「……好,那你可千萬別忘了。」
黑桃K微笑回答:「不會忘,我明白。」
山路兩側樹林青黃,正是當午。
車尾後騰起的塵煙遮蔽了灰白天光,很快沿途遠去,消失在了蒼茫大山的盡頭。
**
「……血壓偏低,有輕微腦震盪,生命體徵穩定……」
「做個檢查看看有沒有顱內血腫,護士把他臉上血擦擦……」
「嚴哥!我們嚴哥到底是怎麼回事?!他怎麼樣了?!」
「嚴哥你快醒醒,嚴哥你醒醒啊!」
……
似乎有無數人簇擁著他往前奔跑,錯落的腳步和激動的咆哮圍繞周圍,此起彼伏。漸漸地那些喧囂都遠去了,他好像來到一片安靜的空間裡,眼前亮起了柔和的白光。
我這是怎麼了?嚴峫迷迷糊糊地想。
我在哪裡?發生了什麼?我是誰?
窸窸窣窣的動靜就像漲潮一般,從四面八方漸漸湧現而來,旋即變成了雷鳴般的掌聲。白光化作燦爛的太陽,走廊盡頭瑰麗斑斕的玻璃門轟然開啟,大理石臺階下是一大片茵茵草坪;白玫瑰花鋪成的地毯兩側,無數熟悉的面孔笑容滿面,一邊紛紛起身一邊歡呼鼓掌。
呂局,魏副局,余隊,方隊,黃興,苟利……秦川也穿著黑西服白襯衫,打著漂亮的領結坐在馬翔和高盼青中間,笑著向他吹了個戲謔的口哨。
嚴峫站住了,望著大家,不知怎麼突然有些靦腆。
「快去啊嚴隊,愣著幹什麼!」韓小梅笑倒在楊媚懷裡,雙手比成喇叭大聲喊道。
「這小子高興傻了嗎?」魏副局一個勁笑罵招手,「還不快過去?」
順著他所指的方向,嚴峫往前看去。玫瑰花瓣從臺階下一路向前延伸,碧玉般的草坪盡頭,嚴父嚴母分別站立在花毯左右兩側,曾翠翠女士還特意穿戴了她壓箱底的好首飾,高興得彷彿年輕了二十歲。
而在嚴家父母中間,一道熟悉的身影穿著禮服,緩緩回過頭,向他露出了柔軟的笑意。
那是江停。
彷彿被無形的力量推著後背,嚴峫一步步走上前。他腳下踩著雲海般新鮮芬芳的花毯,耳朵裡盡是稱賀道喜的聲音,腦海中一時清醒又一時恍惚;那麼長的草坪轉眼就到了盡頭,嚴峫停下腳步,只見江停的笑容越來越深,眼底閃爍著鑽石般璀璨的光亮。
他們就這麼面對面站著,嚴母笑著問:「拿出來啊,你的戒指呢?」
嚴父也問:「對呀兒子,你的戒指呢?」
嚴峫訥訥站著,只聽臺下大家都在催促:「戒指在哪裡?快拿出來呀!」
「快呀,還在等什麼?」
「戒指呢?你的戒指呢?」
……
江停眼珠明亮,面容白皙,嘴唇是飽滿健康的緋紅色。他看起來永遠都像二十出頭最好的年紀,又有些不經人事的羞澀和含蓄,問:「你的戒指呢?」
「……戒指在這裡。」嚴峫聽見自己的聲音說,「我替你戴上。」
咔擦──
錚亮手銬卡住了江停的雙腕,鐵鍊虛虛懸在半空。
「……」江停似乎有些不懂,疑惑地看了看,抬頭問:「嚴峫,這是什麼?」
嚴峫張了張口,沒發出聲音。
歡呼消失了,鼓掌消失了,成排婚禮賓客陡然失去了蹤影。玫瑰花瓣凋謝枯萎,草坪由翠綠變作灰敗,遠處蒼茫層巒疊嶂,山林間吹來淒厲彷彿哭號般的北風。
就像在無數個噩夢組成的迷宮中穿梭,他們又回到了那片山谷。
江停眼底的笑意漸漸消失,變作一片徹骨冰冷,然後他輕輕一掙就將手銬化作齏粉,就像已經發生過的那樣,舉槍對準了嚴峫的眉心。
「我愛你嚴峫。」他冷冷道。
「但你是警我是匪,等再見面時,你我就是生死仇敵了。」
嚴峫怔怔站在那,不能動也不能喊,甚至連轉開目光的能力也沒有。他就這麼眼睜睜看著江停食指用力,然後扣下了扳機──
砰!
病床上,嚴峫身體猝然抽搐,爆發出劇烈的嗆咳!
「大夫!大夫!」
「他醒了!他醒了,快!!」
主治大夫帶著護士快步衝進病房,只見嚴峫已經急促喘息著坐起身,用力閉上眼睛,復又睜開。他眼眶中滿是血絲,額角到側頰那道長長的劃口已經被包紮起來了,精悍的上半身滿是累累的瘀血和外傷;他就像一頭剛衝出囚籠的負傷野獸,滿身凶悍未消,一把推開護士,翻身下床,沙啞地問:「我在哪裡?」
「嚴哥你冷靜點,沒事了!沒事了!」馬翔高盼青等幾個人一疊聲把他往病床上按,七嘴八舌安慰,「你已經回建寧了,還不快躺下!」
「我們都在呢!沒事的嚴哥!醫生說你有點腦震盪暫時不能起!」
「你嚇著護士了,哎呀別別別!小心他那個注射針頭!」
……
嚴峫如夢初醒,目光從周遭每一個兄弟焦急的臉上掃過,瞳孔劇烈發顫。
建寧初冬的陽光越過病房玻璃,將白牆映得亮亮堂堂。
「……呂局呢?」他嗓音嘶啞地蹦出著幾個字來,「呂局……他在哪裡?」
馬翔有些遲疑,刑偵支隊幾個兄弟迅速交換了一個為難的目光。
高盼青掩飾地咳了聲:「呂局他……他現在有點事,待會省廳可能會有些人過來,有些情況吧可能要,那個要稍微解釋清楚……」
嚴峫聽不出這話裡隱約的暗示,他頭痛欲裂,腦子彷彿一鍋煮開了的粥。這時突然他眼角餘光瞥見病房門口掠過一道身影,個頭高挑削瘦,穿著那件熟悉的黑色大衣,眨眼間就過去了。
……江停?
那是江停?!
嚴峫想都沒想,猛然起身推開正準備給他量血壓的醫生,在驚呼聲中搖搖晃晃奔出病房門:「等等!喂,等等!」
那背影毫不停頓,大步流星地向遠處走。
「你給我站住!」嚴峫幾乎是踉蹌著奔上前,一把抓住那人肩膀,「這到底是怎麼──」
嚴峫猝然一僵。
楊媚裹著江停最常穿的那件大衣,手拎鉑金包腳踩高跟鞋,蒼白的臉上未施脂粉,從眼角到鼻翼閃爍著不明顯的淚跡,緊抿唇線面無表情地盯著他。
馬翔他們追出病房,也都紛紛愣在了走廊上。
周圍病患家屬路過,都帶著怪異的神情,擦肩時不住打量他們。推著藥車的護士經過,隔老遠還好奇地頻頻回頭。
「……」嚴峫喉結猛地一滑:「……是你?」
楊媚不動聲色說:「是我。」然後在他灼灼的瞪視中向後微微一偏身。
嚴峫的視線越過她,只見走廊盡頭,三個身著深藍警服的省公安廳人員出現在了電梯門口,正神情嚴肅地向這邊走來。
「我們省公安廳辦公室負責對這次事件進行調查,關於恭州前禁毒支隊長江停,你必須給我們最真實最詳細的訊息。現在我們可以確定,你的問題很大,市公安局的問題也很大!這些問題需要我們一層層抽絲剝繭,絕不容許任何欺騙和隱瞞!……」
三名負責人坐在病床前,每個人手裡都拿著筆記本和錄音設備。為首的是個副主任,自稱姓趙,嚴峫以前辦案的時候遠遠見過一眼,似乎是專門搞風紀督查的。
嚴峫面無表情地靠著病床頭,右手上還扎著針頭在注射,只聽趙副主任冷冷道:「雖然我們已經掌握了你所有的違紀證據,其實不再用問你任何東西了,但經各位領導研究,決定看在你好歹當了這麼多年警察的分上,給你最後一次自我挽救的機會,看表現決定你是否可以獲得組織的寬大處理!……」
「呂局呢?」突然嚴峫打斷了他激情澎湃的演講。
趙副主任的審訊技巧果然為負,明顯愣了下,才皺起眉頭:「我說了,你們市公安局也有問題,現在不是你發問的時候。」
嚴峫說:「我要見呂局。」
「你想見呂局幹什麼?搞串聯,還是對口供?不行!」
嚴峫淡淡一哂:「那我要見劉廳。」
趙主任的臉登時風雲突變,那個拿筆記型電腦的負責人欲言又止,伸手攔了一下,想勸但沒勸住,只聽他「砰」地重重一拍床頭櫃。
「嚴副支隊!」趙主任怒道,「你一直是組織眼裡桀驁不馴的頑固分子,到現在還想負隅頑抗嗎?!我可不管你有什麼背景,有什麼來頭,我們這次過來是給你最後活命的機會!你不主動把握這個機會的話,就別怪組織不客氣了!」
另兩個人坐不住了:「老趙,哎,老趙快坐下!」
「話不是這麼問的,好好說好好說……」
趙副主任大怒指著嚴峫的鼻子:「一會要見這個一會要見那個,你以為你是誰?在所有問題搞清楚之前,你最好給我認清自己的身份!你──」
噗呲!
嚴峫突然拔出注射針頭,在血星飛濺中,劈手將床頭櫃上所有東西甩到了地上,巨響讓所有人一震!
「我是什麼身份?我家去年光省裡定點扶貧出了一個億!我貪汙腐敗了還是偷稅漏稅了,你他媽什麼都沒搞清楚就把我當犯人審!」
趙副主任一呆,霎時病房死寂,只聽嚴峫歇斯底里的怒吼響徹耳鼓:「老子要見呂局!呂局不見見劉廳!劉廳也不見老子就去省委!他媽的,老子到底犯了什麼罪,去省委說清楚!!」
砰!
注射瓶被嚴峫一把奪下來狠砸在地,碎玻璃片葡萄糖滿室迸濺,所有人都僵住了。
半小時後。
同一家醫院,同一棟住院樓,病房樓上。
「就是你看到的這樣。」穿著淡藍色病房服的呂局坐在床頭,放下大茶缸,緩緩道,「第二個原因,他承認了自己就是紅心Q。」
趙副主任逕自氣沖沖回省廳告狀,另兩個負責人跟省廳和市局兩方面協調好之後,也滿臉複雜地跟呂局告辭走了。空曠寬敞的高幹病房裡只有呂局和嚴峫兩個人,房門緊閉著,透過一小塊玻璃窗,可以看見高盼青馬翔等人憂心忡忡守在門外的身影。
霧霾蒙住了白日,空氣中飄浮著消毒水味,連肺裡都灌滿了這嗆人的味道。
「我立刻告辭從你家離開,這時候差不多是晚上九點,外面雨已經下得非常大了。我急急忙忙出了社區,正準備立刻打車回市局彙報這個情況,卻沒想到江停一直跟在後面,在短暫的對峙後突然一刀向我刺來。我受傷倒地,失去了意識,等醒來已經被送進了醫院。整個過程差不多就是這樣,更多細節因為還在調查的原因,就不能再一一告訴你了。」
呂局扶了扶老花鏡,正色望向嚴峫。
後者一言不發。
「他還是喜歡你的,嚴峫。他之所以沒在你家動手,而是選擇跟蹤到社區外偏僻處再行凶,應該是想盡力撇清你在這件事當中的干係。如果不是為了救你,要抓秦川,導致他在我面前露了面,估計他還會隱姓埋名地在你身邊多待兩年。」呂局感慨地搖頭道,「事已至此,可見是天意啊。」
剛才對趙副主任驚心動魄的爆發,就像篝火熄滅前的迴光返照,呼然爆起然後就消失了,只餘滿地狼藉灰燼。
嚴峫沉默著,伸手想摸菸,但摸了個空。
呂局倒從人家來探望他帶的禮品盒中抽出一包雲菸,連火拋給了他:「喏,將就著抽吧。」
喀嚓輕響,嚴峫就著淡藍色的火苗點著了菸,尼古丁的芬芳迅速滲透了每一寸神經。他英俊硬朗的臉在煙霧中模糊不清,許久終於看不出意味地一笑:「──天意。」
然後他抬眼問:「天意讓您派楊媚帶著個紅外線發射器,跑去元龍峽救我的?」
呂局瞅著他哼笑起來:「你小子倒懷疑上我了?──老實說吧,楊媚那事我根本就不知道,不過她自己倒跟調查組交代了個底朝天。江停離開前帶上她,是怕留她在建寧,將來對警方說出更多不利的東西。但在永康村發現你被金杰等人圍捕之後,江停背著『梅花A』吳吞的人,把楊媚支使了出去,讓她有機會的話想辦法救你。」
「他作為紅心Q為吳吞辦事,後來走投無路投靠黑桃K,這些都是真的。但不論如何都不想殺你這點也是真的。」呂局擺擺手,說,「人心幽微、複雜叵測,同一件事從不同的角度來看,會呈現出各種矛盾的實情。總之你這小子能活下來,真是福大命大了!」
真是這樣?
嚴峫瞇起眼睛,目光深處隱約浮現出銳利的懷疑。
呂局不用看就知道他在想什麼,但懶得跟他多囉嗦:「別僥倖了,要是我知道江停和黑桃K在哪,我能不通知省委省廳,派大批特警武警去滅了這個大毒梟?我一個公安局長,有可能派一個編外女線人跑去深山野嶺,執行難度那麼高危險性那麼大的任務?嚴峫,我看你這一跤是把基本的邏輯都給摔忘了!」
的確,如果江停是跟呂局串通好的,那他身後應該跟著大批刑警,而絕不該僅僅只有楊媚一個。
嚴峫夾著菸的手停頓在半空,一時不知該說什麼。
「我明白你的想法,嚴峫。」呂局大概也覺得自己過於嚴厲了,略微緩和口氣道,「但江停這個人的本性是這樣,你得學會接受現實。」
香菸迷住了嚴峫的視線,不久前江停的話再次從耳邊響起:「這條征程漫長艱難而無止境,一旦踏上就難以回頭……能身披國旗走到生命盡頭的人畢竟是少數,更多的人中途就離開了,走散了,或者迷路踏進岔道,再也無法並肩戰鬥……」
「嚴峫,」那天江停在車裡看著他,眼眶中似乎帶著不明顯的微光,輕輕說,「你必須學會接受。」
嚴峫慢慢抽著菸,此刻在病房中,他終於明白了江停眼底那複雜而又不動聲色的光芒是什麼。
那是憐憫。
不是同情他剛剛經歷了秦川的背叛,而是憐憫他一個三十多歲男人,卻還抱著這樣致命的天真。
「我明白了,」嚴峫終於嘶啞地道,摁熄菸頭站起身,「您安心養傷吧,我會配合省廳那幾個傻……那幾個『調查組』的。」
呂局點點頭,為終於勸服他而鬆了口氣。
「江停的問題沒說清楚之前,你暫時被排除在市局工作之外──別多心,這也是正常程序。嚴格照規定來的話你應該被暫時拘留,但你母親……」呂局捂著嘴咳了一聲,「畢竟愛子心切,於是就……暫時走了個特批……讓你停職在家了。」
呂局這話可算相當含蓄,但嚴峫能想像出曾翠翠女士手提金箍棒大鬧天宮的場景。幾年前這明明是他最心煩最唯恐避之不及的,現在卻突然從心底裡油然萌生出一絲感激和溫暖。
生了我這麼一個既不省心也不孝順的兒子,他們其實是不幸的吧──他突然想道。
嚴峫壓下傷感,最後向呂局點點頭,轉身要往病房外走。就在掉頭那瞬間,香菸的白霧被散開,露出他曾經英俊逼人又桀驁不馴的側臉,只見眼梢下不知何時已多了幾道細細的紋路,像是歲月穿透肉體,在靈魂深處沉澱出的累累傷痕。
「……嚴峫。」呂局突然從背後道。
嚴峫站住了。
「楊媚說她離得遠,只看見恭州支隊長齊思浩死了,但沒看清是被誰槍殺的。」呂局沉沉的聲音傳來,「──你看清了嗎?」
嚴峫一動不動,彷彿連呼吸的起伏都沒有。
「……可能是江停吧。」不知過了多久,終於他被砂紙磨礪過的聲音響了起來,說,「當時太快了,其實我也……」
頓了頓他又低聲道:「應該是吧。」
呂局沉默著點了點頭,嚴峫推開門,彷彿逃避什麼似的,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破雲(5)(限)(完)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17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破雲(5)(限)(完)
三年前,緝毒行動中,
江停判斷失誤,發生連環爆炸。
三年後,江停奇蹟般從植物人狀態下醒來……
英魂不得安息,他必須從地獄重返人間!
傾其所有來還原血腥離奇的真相!
作者簡介:
淮上
超人氣網路作家,擅長磅礴大氣的場景描寫,喜歡嘗試不同的題材,以耽美、愛情、都市、奇幻等題材原創網路小說聞名。
已出版品:《銀河帝國之刃》、《青龍圖騰》、《提燈映桃花》。
章節試閱
嚴峫死死盯著那輛全黑色悍馬H2在包圍中遠去,牙咬得那麼緊,以至於生生咬出了血。直到最後一輛車消失在山谷重重的霧靄中,他才發著抖埋下頭,把臉埋在冰涼的掌心,額頭抵著粗礪的沙土碎石,卻全然沒有感覺。
他真的已經透支了,肝腸寸斷的劇痛淹沒了一切,肉體上的傷痛和流血都傳遞不到麻痺的神經末梢。
不知過了多久,身後傳來腳步聲,有人衝上來連拖帶拉地把他從灌木後扶了起來,二話不說立刻往遠處山林裡拽。嚴峫喘息著一看,只見來人體型十分瘦,頭戴鋼盔護目鏡、全身迷彩服,從頭髮到腳跟包裹得嚴嚴實實,但意外的是身上沒有背槍。
倉...
他真的已經透支了,肝腸寸斷的劇痛淹沒了一切,肉體上的傷痛和流血都傳遞不到麻痺的神經末梢。
不知過了多久,身後傳來腳步聲,有人衝上來連拖帶拉地把他從灌木後扶了起來,二話不說立刻往遠處山林裡拽。嚴峫喘息著一看,只見來人體型十分瘦,頭戴鋼盔護目鏡、全身迷彩服,從頭髮到腳跟包裹得嚴嚴實實,但意外的是身上沒有背槍。
倉...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