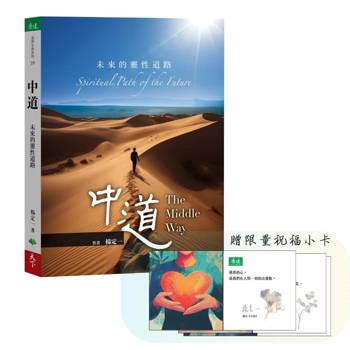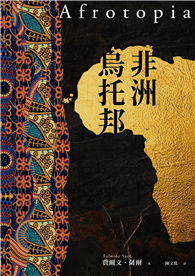修真界千來以來,英豪輩出,而如今能列在「仙君譜」上的, 只有十個人,南宮長英是其中之一。
從前,墨燃並不以為然,他曾經用一根小指頭就碾碎了儒風七十二城,他只覺得這仙城裡窩藏著數以百計的廢物膿包,刀還未架到脖子上就開始喊疼,劍還沒劈下去就開始求饒。
正如上輩子葉忘昔臨死前所說的,煌煌儒風七十城,竟無一個是男兒。
在墨燃眼裡,儒風門是一盤散沙,而聚攏了這一盤散沙的南宮長英,又能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
血跡斑駁,百年基業在瞬間被後來者夷為平地,到處都是死屍,烏鴉啄著死人的肚腸。當年的踏仙帝君拾級而上,他臉上沒有任何表情,推開了先賢堂的大門──
他披著及地的黑色斗篷,穿過掛著儒風歷代掌門、長老肖像畫的長廊,最終停在了先賢堂的盡頭。
踏仙君仰起臉,斗篷加身,帽兜之下,瞧不清他整一張臉,只能看到他蒼白的下巴,弧度凌厲囂張,微微抬起,用審奪的姿態,打量著那尊比真人更高的雕像。
那是尊白玉靈石所雕的塑像,雕的是一位寬袍廣袖的年輕仙君,憑虛御風,持弓而立,匠人工筆遒勁,巧奪天工,用鰈晶石鑲嵌眼珠,浣晶砂塗抹衣冠,泛著血腥味的晨曦從雕像後的鏤花天窗灑落,令他瞧上去就像沐浸著九天神光的謫仙。
踏仙君帽兜下的那半張臉,忽然展露了個笑容,露出森森白齒,甜蜜酒窩。
他整理衣冠,長作一揖,而後抬起那張清俊的臉龐,笑盈盈地說:「久仰啦,南宮仙長。」
雕像自然不會說話,只有那雙黑色晶石流曳著光澤,像是在凝視著來人。
踏仙君也當真是無聊極了,沒人理睬他,他也依舊能自得其樂地做戲良久:「晚輩墨微雨,今日有幸拜會,南宮仙長當真好神氣啊。」
他嘻嘻哈哈,熱熱鬧鬧地一個人講了很久,活人對著雕像發神經。
「我見過了你的玄玄玄玄……」他掰著手指,然後嘆了口氣, 「算不清了,誰知道是你的第幾代姪子,見過了你的不知道第幾代外甥,你座下的不知道第幾代徒弟。」
然後他粲然一笑:「不過如今他們都成了我的刀下鬼啦,所以仙長您若還未投胎,大約也已經見過他們了。」
「可惜沒有瞧見您的玄玄玄玄玄孫子。那傢伙在城破之前就逃啦,我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多少有些遺憾。」
他又開開心心,皮裡陽秋地與那雕像親暱至極地聊了一會兒天,然後道:「對了,我聽說南宮仙長當年也是一代人傑,眾望所歸,走到哪裡都有人誓死效忠追隨,甚至還有擁簇仙長稱帝的。」
墨燃笑咪咪道:「那豈不就和我今日一樣威風?所以我來這趟,前頭說的都是廢話,我只是有個疑問──不知南宮仙長當年為何拒而不登基呢?」
他頓了頓,又往前走了幾步,這時候他的視線落在了南宮長英雕塑後面立著的警言碑上,其實這個碑那麼大,他一早就瞧見了,只是一直刻意略過。
石碑是南宮長英九十六歲那年,用劍鑿刻下的,當初樸實無華,但後來又被子嗣添了金粉熒彩,如今瞧來倒是熠熠生輝,字字千金。
墨燃盯著看了一會兒,笑道:「哦,我明白了。『貪怨誑殺淫盜掠,是我儒風君子七不可為?』仙長真是好風骨。」
他負手而立,繼續道:「可是仙長皓白一世,清譽加身,又對後世諄諄教誨,至死方休,但我很好奇,仙長有沒有料想過有朝一日,儒風門會變成今天這個局面?」
他說到這裡,抿了抿唇,似乎在想一個合適的措辭來形容,而後他想到了,於是他撫掌笑道:「一窩碩鼠?」
他說完,哈哈笑了起來,笑容痛快又恣意,純澈又邪獰,久久迴盪在空寂肅穆的先賢堂,聲如裂帛,像要撕碎那一張張微微隨風擺動的畫軸,撕碎歷代儒風門英傑的肖像……
那笑聲最後停泊擱淺在了南宮長英冰冷的雕塑前,戛然而止。
墨燃不再笑了,他收斂了笑容,面上緩緩凝起一層冰。
他漆黑的眼睛盯著對面吳帶當風的前朝先賢,盯著當年那個與他一樣,同樣可以號令天下,踏盡諸仙的人。
好像時空在此交會,兩個時代的第一仙君在歲月的洪流裡對峙著。
最後,墨燃輕聲說:「南宮長英,你的儒風門是一潭髒水,我不信你會乾淨。」
他驀地揮袖轉身,大步走出先賢堂,忽然起了一陣狂風,吹落了斗篷的帽兜,終於露出踏仙帝君那張近趨瘋狂的臉。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二哈和他的白貓師尊(6)(限)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96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二哈和他的白貓師尊(6)(限)
紅海棠,黃海棠,一朝風吹多悠揚。
小童相和在遠方,令人牽掛爹和娘。
作者簡介:
肉包不吃肉
知名網路小說作家。
章節試閱
修真界千來以來,英豪輩出,而如今能列在「仙君譜」上的, 只有十個人,南宮長英是其中之一。
從前,墨燃並不以為然,他曾經用一根小指頭就碾碎了儒風七十二城,他只覺得這仙城裡窩藏著數以百計的廢物膿包,刀還未架到脖子上就開始喊疼,劍還沒劈下去就開始求饒。
正如上輩子葉忘昔臨死前所說的,煌煌儒風七十城,竟無一個是男兒。
在墨燃眼裡,儒風門是一盤散沙,而聚攏了這一盤散沙的南宮長英,又能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
血跡斑駁,百年基業在瞬間被後來者夷為平地,到處都是死屍,烏鴉啄著死人的肚腸。當年的踏仙帝君拾級而上,他臉上...
從前,墨燃並不以為然,他曾經用一根小指頭就碾碎了儒風七十二城,他只覺得這仙城裡窩藏著數以百計的廢物膿包,刀還未架到脖子上就開始喊疼,劍還沒劈下去就開始求饒。
正如上輩子葉忘昔臨死前所說的,煌煌儒風七十城,竟無一個是男兒。
在墨燃眼裡,儒風門是一盤散沙,而聚攏了這一盤散沙的南宮長英,又能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
血跡斑駁,百年基業在瞬間被後來者夷為平地,到處都是死屍,烏鴉啄著死人的肚腸。當年的踏仙帝君拾級而上,他臉上...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