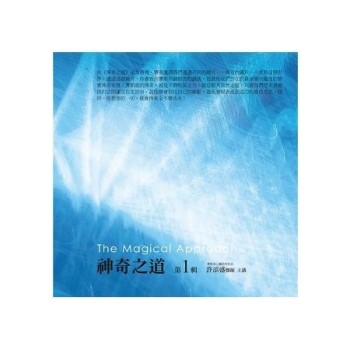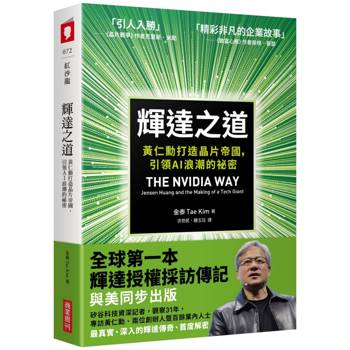她如火鳳凰一般,突破生命火海的重重桎梏,傳遞永不放棄的正能量!
◎翻山越嶺、穿越邊防、怒海浮沉,一部逃出鐵幕追尋生命自由的真實紀錄!
◎從孑然一身的出逃難民到擁有幸福家庭的新時代女性,撐過絕路,也鼓舞眾人。
◎一部個人史,也是那個世代華人海外奮鬥的縮影與寫照,足堪鑑往知來!
從中國文革到香港創業、在西雅圖成為藝術家和作家,鐵幕女性終於大放異彩!
一個生長在極權封閉國家的女子,從小接受洗腦的教育,對外面世界毫無認識,思想純潔又單純,卻又為了什麼失去了升學成長的機會?
與世無爭的她遭受連翻打擊,被迫下鄉務農,為了自由拚死一搏,投奔怒海,失敗了四次最終獲得成功。
身無分文,無依無靠,來到香港打拚的她,好不容易有個立足之地,卻又為兒女移民美國,重新適應新國度。
當她好不容易上大學完成朝思暮想的求學夢,卻又惡疾纏身得了肺癌,再度為生命掙扎奮鬥。
在這個瘋狂年代裡,她就像飛出火海的鳳凰,發出正能量,以自身的故事鼓勵眾人,在絕路中千萬不要放棄,尋找重生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