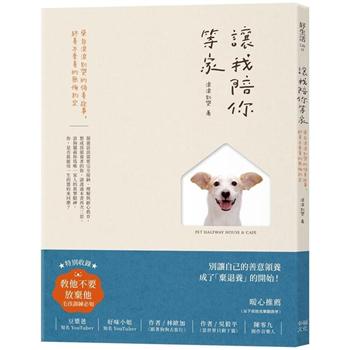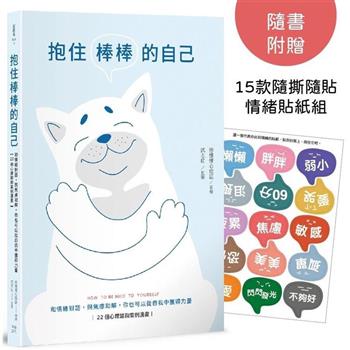總序
音樂家傳記新視野
傳記文學在整個文學及人類文化,占有相當的分量與地位。世界各民族起初以口語傳承民族、部族或原始社會英雄人物的事蹟;有了文字以後,就用筆記載偉大人物的傳記。
傳記因此被認為是歷史學的重要佐證,學界視其為歷史學的分支,極重要的史料。
傳記類書籍在我的藏書裡占了相當的分量,將近1,000本。這些傳記的範圍很廣,包括歷史人物(其實那一個不是歷史人物)、間諜、探險家、發明家、詩人、畫家、建築家等等。其中音樂家傳記就占了三分之二。
我有一個很大的毛病,那就是對某個特定人物感興趣時,除了蒐集在學術上受肯定的傳記以外,凡是在書店(幾乎是在國外)看到有關他們的傳記,或從書上讀到另有附人物圖像的好傳記,就會如在田野挖地瓜般,想盡辦法蒐購。結果是,書架上有關馬勒、莫札特的書就各超過100本。馬勒的研究在這幾年成為風氣,除了米契爾(D. Mitchel)及法國人拉•朗格(La Grange)以外,也有一些新近的研究,被挖掘出來的資料越來越多。
音樂家傳記與其他領域傳記最大的不同點,可能是與一般傑出人物的生涯不同。我們從很多傳記上的記載得悉,不少人物屬大器晚成型,如發明家愛迪生兒童時期的智能發展就比較慢;但音樂家與著名數理學者一樣,很早就展現驚人的天才。
依照學者的研究,音樂家的各種特殊技藝、才能,及數理學者驚人的計算能力,最容易被發現。通常一個人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受教育及實務工作,從中自覺所長,並集中精力投注於此,才能磨練出才華及成就;但是音樂及數理方面的才華,有些是與生俱來的,如上帝的恩寵,頭頂光環,因此很容易被發掘。
幾乎可以斷言,歷史上留名的大作曲家或演奏家,都有過一段神童時期。有些特異才華無法維持太久,過了幾年這種能力就消失。
在東方長幼有序、注重本分倫理的威權之下,天才很難得以發揮,沒有人栽培天才,就沒有天才生存的空間。但在西方有個特別的文化現象,即不管什麼年代都有「期待天才出現」的強烈願望,這可能與西方「等待救世主來臨」的宗教觀有關,西方各國肯定天才,對天才多方栽培的例子不勝枚舉。
有人認為天才不但要是神童,而且創作力必須維持到年邁時期甚至逝世為止;另外一個條件是作品多,而且要對當時及後世有影響才算數。
這樣的條件,令許多夭折的天才只能屈居為才子,無法封為天才。許多人認為天才都是英年早逝,但有些天才很長壽,可見天才夭折的說法,在科學昌明的廿世紀及即將來臨的廿一世紀,是近於妄斷的說法。
音樂家傳記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傳;另外是由親友知已或學者所寫的傳記。十九世紀浪漫時期的特徵之一,就是對超現實的強烈慾望,或因想像所產生的幻想的現實,及由於對現實的不滿,而產生的超現實兩種不同的極端,因而產生了「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至上主義。在這種風潮下,自傳及一般傳記中的許多史實,不是將特定人物的幻想,或對人物的期許寫得如事實般,不然就是把紀實寫成神奇的超現實世界。例如莫札特死後不久,早期的傳記往往過分美化莫札特或將他太太康絲坦彩描述為稀世惡妻;貝多芬被捧為神聖不可觸及的樂聖、李斯特是情聖、舒伯特是窮途潦倒、永遠的失戀者。更可怕的是,將邁人廿一世紀的今天,這種陳腔濫調的傳記,還是充斥市面,不少樂迷都被誤導。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各國對古樂器的復原工作不遺餘力,利用各種資料、圖片、博物館收藏品及新科技,而有長足的進步,得以重現這些古音。同時因副本或印刷器材的發達,原譜不必靠手抄,使古樂譜的研究有突破性的成果, 加上文獻學的發達,以及各種週邊旁述,不同年代的演奏形式、技法漸漸地被分析出來。因此目前要聽所謂純正的巴洛克時期所使用的樂器、原譜、奏法、詮釋,及重現湮沒多年的古樂,已不再是夢想。同樣地,音樂史上的作曲家如巴哈、莫札特、貝多芬的面目,已經相當準確地重現,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人員,不再只是苦心研究的學者,還包括許多業餘研究的經濟、社會、文化、醫事專業人員,從事精密的考證工作;著名音樂家的健康、遺傳病、死因、經濟收人、人際關係等,都有豐富的史料被發掘出來。因此第二次大戰後所出版的音樂家傳記,與十九世紀浪漫筆調下的描繪相距很遠。
十九世紀傳記中描述的音樂家愛情故事極端被美化,而當時極流行的書簡更是助長了這些故事。十九世紀名人所留下的書簡,有些是吐露內心的真話,有些卻是刻意寫給旁人看的,若要以之作為史料,史學者、傳記作者都要小心取捨。
優良傳記的標準是什麼?見人見智,很難有定論,但一定要忠於史實,不能私自塑造合乎自己理想的人物形象,不能偏頗或限於狹隘的觀點,要考慮時代性及政治、經濟、社會等廣泛的文化現象,但也要有自己的史觀。
讀了優良的傳記後,重新聆聽這些音樂家的作品,會增加多層面的體會與瞭解。雖然音樂以音響觸發聽者的想像力,有些是普遍的理念,有些是作曲者強烈主觀所訴求的情感,與作曲家的個性及所追求的目標有密切關係。因此我鼓勵真正喜歡音樂的年輕人,只要有時間,多閱讀傳記。馬勒、莫札特、巴哈的傳記或研究書籍,我各有一百多本,但我還是繼續在買,看起來雖是重複,但每一本都有他們研究的成果,即使是同一件事,也有不同的獨特見解。當然,當作工具書的葛羅夫(Grove)音樂大辭典,都是由樂界的權威人士所執筆,比差勁的傳記可靠,但優良的傳記更富於情感、更有深人的見解,當作工具書也很可靠。
由於喜歡讀傳記,不知不覺中對這些音樂家最後的居所有所知悉。因此旅遊時,我都會去憑弔這些音樂家的墓地或他們曾經居住過的居所。看到這些文物器具,會讓你像突然走入「時間隧道」般,回到幾百年前的景象,與這些作曲家的心靈交流。那種感觸與感動難以言喻。
旅遊時,我除了參觀美術館、音樂博物館、上劇院、看音樂廳、拍攝大教堂及管風琴外,音樂家的史蹟或墓園都列人行程,會對這些地方產生興趣或好奇,大半是讀了傳記而引發的。
讀好的音樂家傳記,如聽好音樂,對人的一生、才華、成就,可以做烏瞰式的觀察,對同時代人造成衝擊,對後代產生影響,並可以培養人們閱讀歷史的技巧;而且有些文章如文學作品般巧妙雋永,讀來回味無窮。
這套由Omnibus出版的音樂家傳記系列,英文原版我幾乎都有,因為內容比聞名的葛羅夫音樂大辭典更深人,對每一個音樂家所處時代,有清楚的定位,應用最新研究資料,附加適宜的註解及推薦相關書籍,幾乎可以當作工具書,其中有些作者是樂界的權威人士。對音樂家及其作品想要有更深人瞭解或欣賞的有心人,這是一套良好的讀物。
資深樂評人
曹永坤
音樂的印象主義
當我年輕時,第一次聽到德布西(Achille-Claude Debussy, 1862-1918)的音樂,就不知不覺的喜歡上了。以後,接觸越多他的作品,對他的喜愛就與日俱增,甚至因此引發對繪畫的印象主義及文學的象徵主義的興趣。
德布西不僅是歐洲鋼琴音樂史上的奇葩,更打破了德意志浪漫主義雄霸歐洲樂壇近一世紀的局面,使法國音樂重新在國際舞台上揚眉吐氣,也為現代音樂墊下了第一塊基石。
德布西出身於並不富裕的家庭,所幸他的音樂天才未被忽視,深具慧眼的音樂老師福洛維爾(Maute de Fleurvil1e)夫人竭盡所能的教導他,使他得以在十一歲時考入巴黎音樂院。本書對他的求學情形有很生動的描述,例如教學嚴苛、專門以培養「巨匠音樂家」為目標的鋼琴教授馬蒙泰(A. Marmomentel)評論他「並不愛好鋼琴,不過他愛好音樂。」德布西幾乎從不規規矩矩的練習和聲習題,老是加一些奇異的和弦,所以「嚴厲的批評與憤怒的鉛筆眉批不斷落在這位學生的頭上和音樂簿上,」儘管如此,這位杜蘭(Emile Durand)教授還是說:「當然,它根本完全不正統,然而,也的確非常有創意。」德布西後來加入吉羅(Ernest Guiraud)的作曲班,這位恩師不但鼓勵他鍥而不捨的爭取羅馬大獎,也在他後來險遭退學時極力庇護他。
德布西曾經像當時的許多法國作曲家一樣,成為一位「華格納的摧崇者,嚴重到忘卻了基本的禮節,」在這個「拜魯特老鬼才」的陰影下,德布西掙扎了許久,終於在碰到薩替(E. Satie)後,找到了另一個自我。另外,他也受了印象畫派莫內、塞尚等人創作理念的影饗,並綜合了象微主義手法,而創作出《牧神的午後前奏曲》(1894)的傑作,擠入當時一流的法國作曲家行列。
即使像德布西這樣的天才,在創作的過程中,還是充滿著徬徨、情緒化與自我懷疑,甚至有「近乎精神崩演的恐懼感」,像譜寫「貝利亞與梅麗桑」,前後歷時十年,一而再,再而三地修訂、重寫,終於在1902年成就了這部印象主義的抒情劇,這部歌劇在各地的演出,都受到熱烈的歡迎。但是成名並沒有帶給德布西經濟上的保障,那些不欣賞他的人仍毫不留情的詆毀他,加上他的緋聞,及後來對妻子的遺棄,都對他產生不利的影饗。然後,他隱居起來,繼續他永無休一止的創作。
大自然對德布西永遠有著無可比擬的吸引力,他甚至聲稱「我把神秘的大自然當做我的宗教」,於是他聆聽、觀察大海的聲音、地平線的曲度、樹葉裏的風聲、鳥嗚等等。他的樂曲中處處可見使用與大自然有關的標題:「春」、「海」、「月光」、「雨之庭園」、「倒影」、「西風所見」、「霧」、「落葉」……等。不過他對標題音樂的看法和白遼士及李斯特大異其趣,從他最偉大的傑作之一《前奏曲集》(二卷)中,將標題用小字附在樂曲終了處,當可窺知一二。
德布西從四十六歲開始與癌症博鬥,但病魔並沒有摧毀他,上述的《前奏曲集》、管弦樂《意象》等都在生病的期間完成,他甚至還完成蕭邦全集的編輯工作。他在病入膏盲時仍表示:「我下決心要忽略我的身體狀況,要回到工作上,而不再受這無比霸道的疾病所奴役。 ……如果我注定很快要消失於人世,那麼我希望自已至少嘗試著克盡職責。」
讀荷密斯(Holmes)寫的這本德布西傳記,我們看到了上個世紀交替期一位偉大作曲家的心路歷程,分享了他的喜怒哀樂,以及如何開創出一片前所未有的音樂天地,建立了音樂的印象主義。
柏林自由大學音樂博士
國立藝術學院專任副教授
顏綠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