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無論是在中國與台灣,幾乎沒有不認識魯迅筆下的孔乙己,也還算熟悉阿Q「兒子打老子」的「精神式勝利法」(《狂人日記》)。可是,我也認為在台灣的絕大多數人,即便高中時都曾讀過魯迅的《孔乙己》,大抵都會懵懵懂懂,一知半解,囫圇吞棗。進入大學後,走理工與醫學的大多扔開國語課本,就此分道揚鑣,老死不相往來。即便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對於魯迅的認識僅止於是民國時期的文學家,而且透過陳西瀅、梁實秋、蘇雪林作品中所呈現的魯迅形象還是高度負面。魯迅被斥之為刻毒不寬容、陰險尖刻的紹興師爺外,還「不尊重底層人民,而是抱著一種藐視的心理來訓斥」(顧曉軍2015:11)。魯迅的心理人格「心胸過於仄隘,把自己世界縮小得無以復加,竟致弄得有無處可去之苦」(蘇雪林1979)。更甚者,在《李敖有話說》的談話性節目中,李敖言之鑿鑿地指出魯迅對提拔他的陳獨秀(創辦中國共產黨),在其政治受難時不僅不能夠如胡適努力營救,還要撰文諷刺將其比喻為吃了滿嘴馬糞的焦大(紅樓夢),儼然是「過河拆橋,落井下石」,李敖帶風向的問道:「大家不覺得魯迅這個人的所謂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這個風骨,有點問題嗎?」(房向東2014:3-4)。
陳芳明(1992)在《魯迅在台灣》一文中(中島利郎編2000),深刻的剖析了為何魯迅在台灣人文學界長期缺席的三個因素,第一、1947年的228事件,使台灣知識分子從此保持沉默。第二、1948年許壽棠在台北遭到暗殺,使得介紹魯迅作品的最大力量從此斷絕(臺靜農、黎烈文分別留在台大中文系、外文系執教、終身不談魯迅)。第三、1949年國民黨逃到台灣,展開積極的反共政策,從此出現長達了40年的反魯迅傳統(國民黨官方的三位御用文人:陳西瀅、梁實秋、蘇雪林;還有台灣反共的另一批打手:鄭學稼與劉心皇)。所以,即使陳芳明的研究結論之一是「從台灣文學發展的實施來看,魯迅對台灣作家的影響是否有那麼巨大,誠令人懷疑。」但是陳芳明對於未來台灣的魯迅研究抱持高度的期待,他在文末中寫道:
相對於中共文藝政策下魯迅的神話,國民黨顯然是過於貶低魯迅的文化地位。身為台灣的作家,如果要正確認識魯迅作品,就必須有能力擺脫國、共兩黨文藝政策的影響。國共兩黨為魯迅附加上去的面具,使後人很難看見魯迅的真貌。魯迅的文學成就,並沒有像中共學者所說的那樣高超,也沒有像國民黨學者所說那樣低俗。魯迅文學,是非常具有人性的;而人性有其堅強的一面,也有其軟弱的一面,這才是台灣作家接觸魯迅作品時所應探討的課題。(陳芳明《魯迅在台灣》,引自中島利郎編(2000)《台灣新文學與魯迅》,第31頁)
這篇文章出版近三十年後,台灣各界大抵仍然不待見魯迅的作品與思想。房向東(2014:1)點名了台灣有「魯迅遺風,是魯迅的傳人」的「幾個男女」(牧惠、柏楊、龍應台、李敖),不說是少的屈指可數(五個指頭以內),「幾個男女」中的李敖還違反歷史事實地惡意曲解魯迅。再反觀中國大陸,2007年大陸在民間與官方都致力於「去魯迅化」,但是理由全然不同,民間想將魯迅拉下「神壇」,因為大陸在文革期間只能讀兩種著作,一是毛語錄,二是魯迅選集,前者給後者戴上了九頂高帽子,分別是:「旗手、主將、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骨頭最硬、民族英雄、馬克思主義者、唯物論者」(顧曉軍2015:103),還是睚眥必報,「一個都不寬恕」的「刀筆吏」與「紹興師爺」;另一頭,中共官方也想「忘卻」魯迅在百年前的《吶喊》,並致力於「一直在試探儒家取代馬克思主義,成為新的官方意識形態的可能性」(陳純2020:17)。在民間與官方的「不謀而合」下,魯迅的文章也因其已經不符合時代需求,必須走出大陸的小學、中學與高中的語文課本。所以,當代在魯迅研究上,兩岸終於不謀而合的給他冷處理,走出眾人的視野。
這兩年來仔細詳讀《魯迅全集》(2005)後,我發現魯迅既非尼采式「張個性、揚精神」的超人,更非「心胸過於仄隘,把自己世界縮小得無以復加,竟致弄得有無處可去之苦」(蘇雪林1979)。從《魯迅全集》的小說、雜文、書信與日記中,處處可見希望拆毀封建社會的鐵屋子,檢視愛情、婚姻、兩性平等、語言改革、教育改革、尤其是兒童教育,要救救孩子。顯然是為了要「救救孩子」的急切之情與對於舊社會的惡習慣的滿腔憤懣,所以魯迅總是愛罵人。雖然我不是畫家陳丹青(2011),實無法從畫像上大先生的八字鬍中看出美來;可是從長期研究的關懷倫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中放開眼看,《魯迅全集》(2005)中竟然充斥著滿滿的愛與關懷的悲憫與同理心,從中我看到的不只是文學家魯迅,而是有方法與行動的思想家魯迅。就如同《非攻》中摩頂放踵地墨子般(《魯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編》),魯迅幾度大病之餘,浮起的就是「要趕快做」。臨死前仍然忙碌奔走、收集並出版《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1936),因為魯迅從凱綏珂勒惠支(Kathe Kollwitz 1867-1945)的作品中,深切感受「伊以深廣的慈母之愛,為一切被侮辱和被損害者悲哀,抗議,憤怒,鬥爭;所取的題材大抵是困苦,飢餓,流離,死亡,然而也有呼號,掙扎,聯合和奮起。」(《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序目》,《魯迅全集》第六卷,第487-488頁)
所以,此專書將名為「魯迅與關懷倫理學十六堂課」,比照一學期上課16週,規劃為十六堂課,梳理出為何筆者會主張民國時期文人魯迅竟然會與西方關懷倫學扯上關係,兩方是如何跨越約半世紀的差距而前後呼應,同聲一氣。說起來,百年前魯迅所提倡的愛情與婚姻觀與西方極端個人主義,並不雷同。反觀西方自1980年代以降,女性主義內部也開始反省個人主義所倡導的價值的片面性,從而拉開了女性主義的另一波思想風潮,也是關懷倫理學的時代背景。從關懷倫理學的發展來看,魯迅對於如何在新社會中發展愛情、婚姻與教育的關切,也正是關懷倫理學者所關切的重估家庭價值與教育的重要議題。兩方都察覺西方講究個人主義的偏頗,也紛紛以「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架勢,抵抗想要「復古」的父權傳統與舊社會保守封閉的群體主義。同時在魯迅與關懷倫理學「無情未必真豪傑」的有情中,兩方都強調從最切身的差等之愛起手,魯迅要「以幼兒為本位發展進步的智識,道德,品格,思想」,擺脫中國人以家長為尊的「差序格局」與其「宗法制度」,才能免於被「擠」出世界的大恐懼,更要能和世界上的種種人民「協同生長」。西方關懷倫理學者更進一步發揚照顧者思考中的實踐,本於孕育近身關係的「差等之愛」來建構渾然不同於父權傳統下的倫理學,並且憑著關懷倫理學的「不同的聲音」,橫眉冷對傳統法政哲學中所強調的不涉及人身利益的一視同仁的原則性、抽象性與普遍性。
在時空穿越中,魯迅與西方關懷倫理學之所以能夠遙相呼應,起到關鍵橋樑作用的是被卡繆譽為「我們時代中唯一偉大的精神」─西蒙韋伊(Simone Weil)(1909-1943)。雖然魯迅與韋伊互不相識,卻有著高度的雷同性:兩人在性格上都反對「名人效應」外,對知識名流的種種勢利態度相當反感並且敬而遠之;兩人都看到勞苦大眾眼中的茫然與麻木,從而對這些被欺壓與受損害的廣大群眾懷有深刻的同情外,還更願意身體力行地成為其中的一員(韋伊積極參與工人罷工運動、進工廠、去農場、赴西班牙參軍)。同時,兩人都以積極的方法來推動改革社會種種積弊,堪為二戰期間,東、西輝映的「骨頭最硬」的「這樣的一種戰士」。
筆者以為:既然關懷倫理學的精神豐碑源自於西蒙韋伊,那麼在精神氣質上如此相近的魯迅,也會是關懷倫理學的重要思想資源,成為協力抵抗父權傳統中根深蒂固的男性支配的推手與助力。所以,比起眼觀三世的遠庖廚者以恩義為尚、由親而疏的「差等」(partiality),魯迅與關懷倫理學都是以自然之愛為本,要盡義務的「差等之愛」。雖然兩者同樣使用「差等」語詞,其實概念已經經歷「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產生質變,不可共量。所以,如同魯迅所言,父母們學著應該怎麼愛孩子,照顧朋友,體貼人類,如果還有時間與力量,就為世界的協同生長盡一點點力量,以上都不僅僅是好聽的「無物之陣」的空話,而是要走出「象牙之塔」,要去實行,從自己最切身的人開始,對於孩子「應該健全的產生,盡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魯迅全集》第一卷,第141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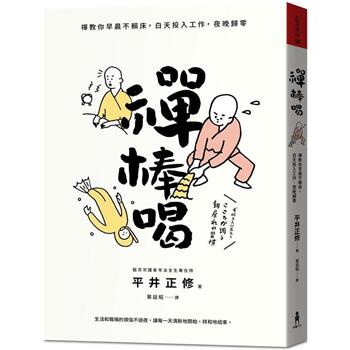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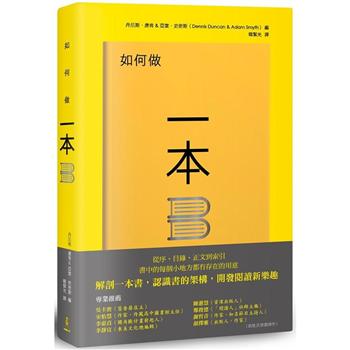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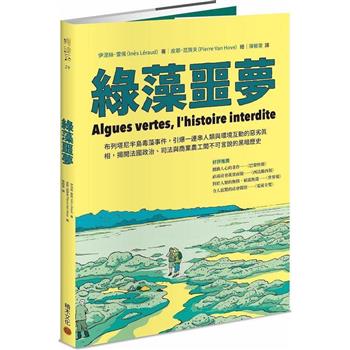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失智症照護指南[經典暢銷增訂版] 失智症照護指南[經典暢銷增訂版]](https://cdn.kingstone.com.tw/book/images/product/20141/2014150562736/2014150562736m.jpg?Q=e3fc9)



![114年公幼教保員專業科目關鍵突破[教師甄試] 114年公幼教保員專業科目關鍵突破[教師甄試]](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18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