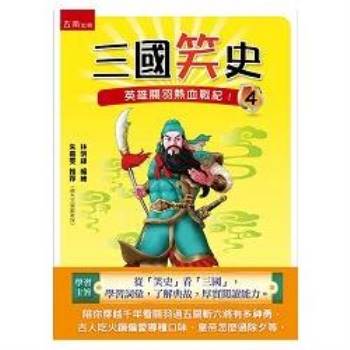序
陳小瀅
1996 年,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舉辦了一次「中國古代人與神」文物展覽。聽說有些展品是不久前才在四川「三星堆」出土的,而且展出的人像和過去古代中國的展品不同—相貌很特別,有巨大的眼睛,可又不恐怖,人像之外的其他展品也都自然活潑。
當時去看展覽的人真是人山人海,但又是排着英國式的整齊長隊,慢慢地走去買票。我和丈夫也去看展覽,除了被這壯觀的隊伍震撼,更為祖國輝煌的民族文化感到無限自豪。之後,我們認識了這次展覽的中方策展人—陳烈先生。他是中國國家文物局選派來英國的,對中國的古代文化了如指掌,口若懸河,讓我們十分佩服。
有一天,一位朋友帶陳烈來我們家,把我們夫婦介紹給他。我們真是受寵若驚!特別的興奮和高興。朋友告訴陳烈,我的丈夫秦乃瑞是位漢學家,去過中國多次。關於我,朋友介紹我的父親就是陳西瀅,過去寫《西瀅閒話》的,母親是小說家凌叔華,他們都是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國文學界的名人。
以後陳烈常來我家聊天。他問我是不是在北京長大的,我告訴他說我小時候在北京,但時間很短,因為日軍侵華後,我多半在武漢和四川樂山。他於是問我在北京住在何處,我說我家當年在北京史家胡同有一所房子。他聽了大吃一驚,問是多少號,我告訴他說是五十四號,他說他家也是五十四號呀!
我在1944 年冬季想從軍,告訴父親我的想法: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為國家犧牲是光榮的,人生自古誰無死…… 父親回信說,他很吃驚,但我年紀太小,才十四歲,去從軍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我長到十八歲了,他贊成我從軍,為祖國打仗。他告訴我,在英國所有年輕人都在十八歲從軍,包括英國皇室的成員,國王的女兒,還有首相的兒子。這是他在二戰時和我的通信,大約有一百幾十封。
我的父親十五歲時經過長輩的動員,自費去英國留學,幫了他大忙的是表叔吳稚暉先生。父親在英國近十年,從中學到大學,直到得到博士學位,他都是個窮學生。但因為好學而且聰明,他對英國的政治和文學有了極大的興趣和了解,得到當年英國學術界名人的資助。他和傅斯年為H.G.Wells(赫伯特.喬治.威爾斯)博士的《世界通史》一書寫過有關東亞、中國的章節。
父親回國後,蔡元培先生聘他為北京大學英文系教授。父親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如胡適、徐志摩等人先後創辦了《現代評論》和《新月》雜誌,那是近一百年前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期。這些宣傳推廣白話文的學者們,年輕大膽。後來他們與魯迅先生發文的《語絲》等刊物有筆戰的情況,在當年的很多國家,政論不一致的雜誌很多,甚至有些評論家在報刊雜誌上彼此罵得不堪,但在生活中還是談得來的朋友。
我父親回國時才二十四歲,後與比他大十幾歲的魯迅先生發生了筆戰,我覺得是一件有意思的事。魯迅先生是留學日本而且是學醫的,我父親是留英學政治和文學的,他們回國後都對當時的情形看不順眼,很多時候寫文章都是出於愛國之心;而他們一位成為民族的英雄,另一位卻變成了「小丑」……
後來父親停止寫「閒話」,結婚後離開了北平。1928 年,父親被聘為國立武漢大學的第二任文學院院長,承擔教學和行政工作。1937 年中日正式開戰,武漢大學於1938 年遷到四川樂山。到了1943 年,當時的政府希望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抗日情形多一些了
解,遴選幾位資深教授去美國和英國,向當地人民宣傳中國抗日的意義。
我父親是其中之一,被派去英國,但由於當時中英之間無法直接交通,只有先到美國,再從美國飛去英國。
那時是二戰歐洲戰場激烈的時期,1943 年底英國還受到德國炸彈的威脅,倫敦遭到德國V1 和V2 導彈的襲擊,十分可怕。但父親還是想辦法飛去英國,與他在英國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並活了下來。
陳烈先生也要寫到我的母親凌叔華,我聽說她的名字現在中國文化界幾乎人人知曉,因為她是很有名氣的短篇小說作家,而且還是資深的畫家。
我記得小時候總是希望得到母親的寵愛,在武大珞珈山,我說「我是姆媽的小走狗」,而當父親和母親吵架時,我總是叫嚷「爹爹不對,姆媽對」,可是母親對我始終是比較冷漠的。
我對母親真是不很了解,我們家可以說是「父慈母冷」。母親對我和父親都比較冷漠,而那時期我的小鄰居、小夥伴都是有兄弟姊妹的,而我母親卻說她不想再生小孩了,因為生孩子痛苦,小孩也是個負擔。
母親是在清朝官宦人家出生的,我的外祖父凌福彭曾任直隸布政使、天津知府和順天府尹,後來在袁世凱手下也做過事。外祖父很有才幹,而且對書畫很有興趣,對新生事物如白話文也不拒絕。外祖父有五位夫人,母親是第三位夫人所生,她們姊妹三人,沒有兄弟。
大家庭裏的太太們為了爭寵而爭風吃醋,兄弟姊妹們為了父親的寵愛而爭鬥,大約是我們母親從小的生長過程中看得最多的事。而由於她的性格比較強勢,對於繪畫和文學又有得天獨厚的稟賦,比其他姊妹兄弟都強,受到了外祖父的注意和寵愛,聘請北京最好的畫家和學者來啟蒙她、教導她。
母親在家中受到特別的重視,使得她的個性更強了。一般女性在那個時代都是很早就嫁人了,但母親卻能進入有名的中學和大學讀書。當時白話文剛開始興起,母親就發表了白話文寫作的短篇小說,受到特別關注。
那時讀書的女子並不很多,尤其是能寫作、發表文章的女性實在很少,像林徽因、冰心、蘇雪林、丁玲等,都受到社會的關注。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社會風氣有所開放,我想我父母的婚姻也不是意外了。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社會還是講「門當戶對」的。我聽母親說過,當他們婚後去無錫拜望她的公婆,就受到了極大的刺激。因為母親家是奴僕成群的,她有自己的小姐書房,而我父親家就是一棟極小的房子,公公婆婆連個像樣的僕人都沒有。那時候,在江南新進
門的媳婦應該為公婆端茶、端飯,站在公婆身後伺候;客人來賀喜時,新媳婦也要為客人端茶水,我母親告訴我說,她只好裝病,不出來見人。母親可能覺得,她的婚姻是徹底失敗了。從那時起,她對父親可能就有看法了。
我小時候在珞珈山時,母親總說女人不應該結婚。當我淘氣的時候,母親就說我不像凌家人,只像陳家人,好像陳家人成了「二等公民」似的。母親後來的婚姻狀況、和朋友相處的情況,都和她的家庭背景有關。
母親覺得應該和最有名望的人士來往,和最有才能、最有勢力的人士來往。所以她和朱利安.貝爾的所謂愛情,也和貝爾身後英國文藝界特別有名的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the bloomsbury group)有關—這是我的猜想。
現在,母親和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的通信都在大英圖書館公開了,而伍爾芙又是貝爾的姨母,更是英國非常知名的作家;貝爾的父母也是英國文藝界的主流人物。當然,現在看來這是件有益的事,是當年中國作家與西方作家開始交流的重要事件。
我母親的書畫創作受到好評,但她從來沒有教過我書法、繪畫,還有讀書。這也不能怪她,因為我出生在戰爭年代,一出生就趕上「九一八」日本入侵,之後1937 年抗日戰爭正式爆發,戰火遍野,大家都在逃難、躲警報。後來武漢大學又西遷到四川,母親那一代人可以說開始是有過好日子的,而我們生在1930 年後的人,卻都是受到戰爭影響的。
陳烈先生說他要寫我父母二人的傳記,我很歡迎。因為中國文學界比較少有關於作家夫婦二人的傳記。陳烈知道我父母二人性格完全不同,而我自己在國外生活了近五十年,對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的情況不太了解,因此我把父母的書信和日記等資料交給陳烈,請他客觀地將二人的性格、經歷寫出來,想來這是二十年前就約定的事了。
我覺得,別人寫我父母的傳記比我自己寫會更加客觀,所以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通過《雙佳樓往事》,了解這一對上個世紀有些名氣的夫婦的故事,是件可喜的好事。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技術型高中易點通數學B總複習講義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06 |
升學考試 |
$ 324 |
社會學 |
$ 324 |
Parenting & Education |
$ 342 |
中文書 |
$ 342 |
升學考試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技術型高中易點通數學B總複習講義
#108新課綱#各版本適用
本書特色
1.重點整理:歸納重要觀念與公式,濃縮各版本精華,使學生快速掌握應考要點。
並在每個重點後標示出統測考過的年度,讓學生更清楚瞭解各個重點在大考中出現的頻率。
2.大家來找碴:馬上練習找出常犯的計算錯誤,強化基本觀念。
使學生輕鬆掌握該章節重點,培養正確的解題觀念與能力。
3.例題類題:整理出各節重要題型,並依難易度區分為基礎題型和進階題型。
每一組例題類題皆有標示主題,更貼心提示其難易度與重要性。
※「進階題型」教師可依班級學生程度斟酌選授,讓程度優異的學生能進行深度演練,滿足所有學生的需求。
4.歷屆試題:囊括最新歷屆試題,掌握最新考題趨勢與重點。
本書另附課後練習本,搭配例題精心編寫實力檢測、自我評量,學生可立即自我檢測以強化觀念,增進解題之熟練度。
「★」表示進階題型,提供程度優異的學生練習,活化思考力。
作者簡介:
陳列,筆名陳烈,北京人。畢業於南開大學歷史系文博專業,任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兼任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客座教授。在職期間,主辦或參與各式對外展覽近百,足跡遍除非洲外各大洲。工作之餘喜編著,成果有《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法書選集》《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劄》《小莽蒼蒼齋輯藏紅樓夢相關資料》《田家英與小莽蒼蒼齋》。業餘愛好:旅行、收藏、圍棋、橋牌。
作者序
序
陳小瀅
1996 年,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舉辦了一次「中國古代人與神」文物展覽。聽說有些展品是不久前才在四川「三星堆」出土的,而且展出的人像和過去古代中國的展品不同—相貌很特別,有巨大的眼睛,可又不恐怖,人像之外的其他展品也都自然活潑。
當時去看展覽的人真是人山人海,但又是排着英國式的整齊長隊,慢慢地走去買票。我和丈夫也去看展覽,除了被這壯觀的隊伍震撼,更為祖國輝煌的民族文化感到無限自豪。之後,我們認識了這次展覽的中方策展人—陳烈先生。他是中國國家文物局選派來英國的,對中國的古代文化了如指掌,口若懸河...
陳小瀅
1996 年,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舉辦了一次「中國古代人與神」文物展覽。聽說有些展品是不久前才在四川「三星堆」出土的,而且展出的人像和過去古代中國的展品不同—相貌很特別,有巨大的眼睛,可又不恐怖,人像之外的其他展品也都自然活潑。
當時去看展覽的人真是人山人海,但又是排着英國式的整齊長隊,慢慢地走去買票。我和丈夫也去看展覽,除了被這壯觀的隊伍震撼,更為祖國輝煌的民族文化感到無限自豪。之後,我們認識了這次展覽的中方策展人—陳烈先生。他是中國國家文物局選派來英國的,對中國的古代文化了如指掌,口若懸河...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單元1坐標系與函數圖形
1-1直角坐標系
1-2函數
單元2一元二次方程式與不等式
2-1一元二次方程式
2-3一元二次不等式
單元3式的運算
3-1多項式的四則運算
3-2餘式與因式定理
3-3分式與根式的運算
單元4直線方程式與線性規劃
4-1直線的斜率與方程式
4-2兩直線關係
4-3線性規劃
單元5三角函數
5-1有向角及其度量
5-2三角函數的定義
5-3任意角的三角函數
單元6三角函數的應用
6-1三角函數的圖形
6-2正弦定理與餘弦定理
6-3三角測量
單元7平面向量
7-1向量的意義及其運算
7-2向量的內積與夾角
單元8圓
8-1圓的方程式
8-2圓與直線的關係
...
1-1直角坐標系
1-2函數
單元2一元二次方程式與不等式
2-1一元二次方程式
2-3一元二次不等式
單元3式的運算
3-1多項式的四則運算
3-2餘式與因式定理
3-3分式與根式的運算
單元4直線方程式與線性規劃
4-1直線的斜率與方程式
4-2兩直線關係
4-3線性規劃
單元5三角函數
5-1有向角及其度量
5-2三角函數的定義
5-3任意角的三角函數
單元6三角函數的應用
6-1三角函數的圖形
6-2正弦定理與餘弦定理
6-3三角測量
單元7平面向量
7-1向量的意義及其運算
7-2向量的內積與夾角
單元8圓
8-1圓的方程式
8-2圓與直線的關係
...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