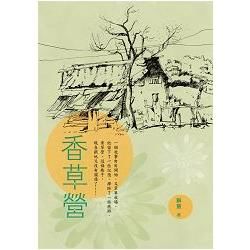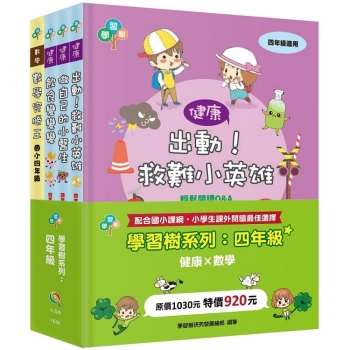一個故事匆匆開始,又草草收場,
他留下了一些記憶,掃除了一些痕跡,
香草營,這條巷子,現在跟他又沒有關係了……
他留下了一些記憶,掃除了一些痕跡,
香草營,這條巷子,現在跟他又沒有關係了……
這部短篇小說集收錄了蘇童的三篇小說:〈香草營〉以一個婚外情的故事作為依託,巧妙地演繹了兩個不同身分男人之間的內心交戰。〈拾嬰記〉講述一個棄嬰在城鄉之間不斷被轉手的過程,這一趟旅行,實是對世道人心的一次檢驗。〈茨菰〉經由少年「我」的視角,記錄了鄉下姑娘彩袖在知青的慫恿與協助之下,逃婚進城後的種種遭遇。
本書特色
這部作品裡,沒有一個是所謂高尚的人,但也沒有大奸大惡之徒。書中的這些人物,無論光鮮的還是失意的,都是些平凡的俗世中人。他們為著各自的目的在社會上活動,保持著人性、人情最原始的狀態。作品讀來深刻寫實,彷彿在身邊發生,但也像一個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