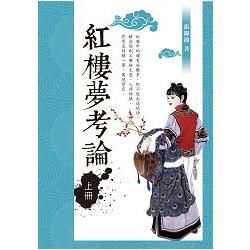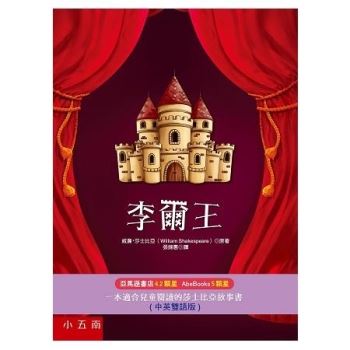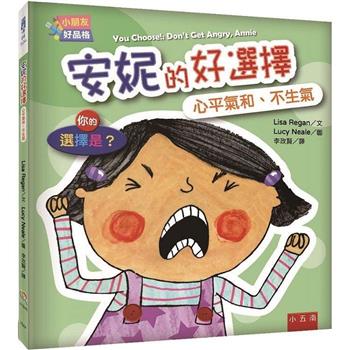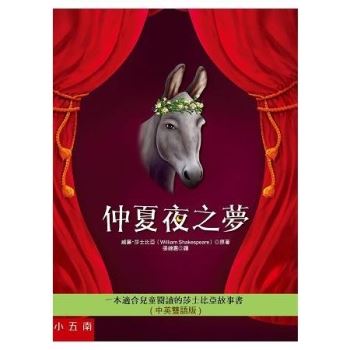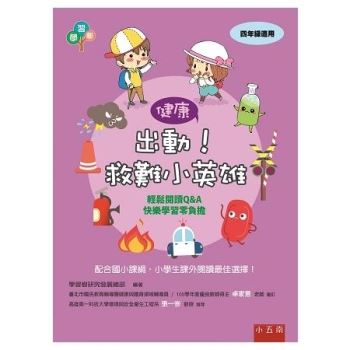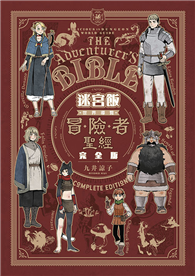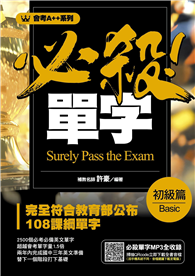《紅樓夢》作者考
一 小引
《紅樓夢》的作者是誰?是曹雪芹,可又不時有人提出質疑。《北方論叢》1979年第1期發表的戴不凡先生的〈揭開《紅樓夢》作者之謎〉,就是一篇具有代表性的質疑文章。「謎」底是:「曹雪芹是在石兄《風月寶鑑》舊稿基礎上巧手新裁改作成書的。」
認為曹雪芹只是《紅樓夢》的改寫者而不是原作者,這說法雖則並非始於戴不凡先生,乃是歷史上的一種意見;然而戴不凡先生從多方面作了考證、論述,提出了有關的新見,這對於我們進一步研究《紅樓夢》的作者問題頗具啟發。這是個沒有真正解決而又值得探討的問題。因為,從胡適於1921年發表了〈《紅樓夢》考證〉,認定《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以後,很少再有異議,也就沒有人再去作過專題研究予以進一步證實;但胡適的這個論斷,卻是避開歷史上的不同意見而僅憑所需的一條證據作出的。所以,戴不凡先生重新提出《紅樓夢》的作者問題來進行討論,我認為是有意義的。不待說,這類學術上的問題,經由各抒己見,互相爭鳴,更容易得出比較正確的結論。因此,我不揣謭陋,也把自己的看法寫出來,以就正於戴不凡先生和廣大的《紅樓夢》愛好者。
二 乾隆年間的看法
戴不凡先生說:「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一手創作的祖師爺,就是『新紅學』的祖師爺胡適。」可是,我所接觸的證據卻不是這樣;早在乾隆年間,就有不少人認為《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袁枚的《隨園詩話》卷二中有一段敘述:
康熙間,曹練亭(練當作楝)為江寧織造,每出,擁八騶,必攜書一本,觀玩不輟。人問:「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見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與江寧太守陳鵬年不相中,及陳獲罪,乃密疏薦陳。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
袁枚是乾隆進士,曾任江寧等地知縣,與曹雪芹同時代人,他說「雪芹撰《紅樓夢》一書」,總不會是無中生有。倘說袁枚把曹楝亭(曹寅)與曹雪芹的祖孫關係說成父子關係,顯見兩家並不是世交,因此他說「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可靠性有值得懷疑之處,那就不妨再看一首永忠的詩。此詩見於他的《延芬室稿》稿本第十五冊,題目就是:〈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弔雪芹三絕句(姓曹)〉。詩上有弘旿眉批曰:「此三章詩極妙。第《紅樓夢》非傳世小說,余聞之久矣,而終不欲一見,恐其中有礙語也。」詩云:
傳神文筆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淚流。可恨同時不相識,幾回掩卷哭曹侯。
顰顰寶玉兩情痴,兒女閨房語笑私。三寸柔毫能寫盡,欲呼才鬼一中之。
都來心底復心頭,辛苦才人用意搜。混沌一時七竅鑿,爭教天不賦窮愁。
倘若曹雪芹不是《紅樓夢》的作者,永忠讀《紅樓夢》後何以作詩弔曹雪芹?詩裡說曹雪芹是「傳神文筆」、「用意搜」、「能寫盡」、「爭教天不賦窮愁」,口氣也都不是指改寫而是指創作。墨香是曹雪芹的好友敦誠的幼叔,弘旿是乾隆的堂兄弟、永忠的堂叔父,永忠就是那被雍正謀奪了儲位權的胤禵之孫,曹府又是在康熙諸王子的奪嫡鬥爭中因受牽連而被抄家的。墨香借給永忠《紅樓夢》,弘旿在永忠的詩上加眉批;因此永忠認為《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實際上也就反映了墨香、弘旿的共同看法。此詩寫於乾隆三十三年,距曹雪芹之死,按「壬午」說為六年,按「癸未」說為五年,諒來他們總不是串通起來造謠生事吧!倘說這仍只是一種分析和推測,詩裡並沒有《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的字樣,因而不足為據,只能作為旁證,那就不妨再看明義的〈題紅樓夢〉小序:
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蓋其先人為江寧織府;其所謂大觀園者,即今隨園故址。惜其書未傳,世鮮知者,余見其鈔本焉(見《綠煙瑣窗集》抄本)。
明義是永忠的從兄永珊的外甥,與永忠、墨香、敦誠、敦敏均有交往;墨香是明義的堂姊夫,與曹雪芹關係較密切的明琳可能是明義的堂兄弟。因此,明義說「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該不是向壁虛構吧!而我以為,假若把明義的這篇序和上面引的永忠的詩相並觀,更可以看出永忠心目中的《紅樓夢》作者確實是曹雪芹。
此外,沈赤然在他的《五硯齋詩鈔》卷十三中有四篇題《紅》七律,詩作於乾隆六十年(1795),此時高鶚輩續書才刊行三年,而詩題也是「曹雪芹《紅樓夢》題詞四首」。許兆桂在給女作家吳蘭徵的《絳蘅秋》所作的序言裡也確言:《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為故尚衣(按指曹寅為織造)後」。西清在《樺葉述聞》中說得更明確:「《紅樓夢》始出,家置一編,皆曰此曹雪芹書,而雪芹何許人,不盡知也。雪芹名霑,漢軍也。」這些證據,都可說明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因此,並不能說這是胡適的發明。
那麼,乾隆年間有沒有人認為曹雪芹只是《紅樓夢》的改寫者呢?有。以下就是戴不凡先生所引用的裕瑞的看法;在這個問題上,裕瑞的看法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會兒說:
聞舊有《風月寶鑑》一書,又名《石頭記》,不知何人之筆。曹雪芹得之,乃以近時之人情諺語夾寫而潤色之,藉以抒其寄託。以是書所傳述者,與其家之事蹟略同,因借題發揮,將此部改至五次,愈出愈奇。……聞其所謂寶玉者,尚係指其叔輩某人,非自己寫照也。(《棗窗閒筆》)
這顯然是指曹雪芹只是這部小說的改寫者。可在同一部書裡,一會兒又說:
《紅樓夢》一書,曹雪芹雖有志於作百二十回,書未告成即逝矣。諸家所藏抄本八十回書,及八十回書後之目錄,率大同小異者,蓋因雪芹改《風月寶鑑》數次,始成此書,抄家各於其所改前後第幾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諸稿未能劃一耳。
殊不知雪芹原因托寫其家事,感慨不勝,嘔心始成此書,原非局外旁觀人也。若局外人徒以他人甘苦澆己塊壘,泛泛之言,必不懇切逼真如其書者。
這又顯然是說《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而且只能是曹雪芹。《紅樓夢》的作者究竟是誰,裕瑞自己也不甚了了,因而戴不凡先生說《棗窗閒筆》裡的「記載可徵」,足資證明曹雪芹只是《紅樓夢》「這部小說的改作者」,還是有值得推敲的地方。或許戴不凡先生會說:要充分重視裕瑞的「聞」,因為此人「去雪芹生平未遠,很可能和曹家有點親戚關係」;焉知這不是「小道消息」!在此,我們只想指出一個事實:裕瑞和曹家的關係較之明義和曹家的關係是隔了一層。明義約生於乾隆五年左右,曹雪芹死時他已二十三歲上下;而裕瑞生於乾隆三十六年,曹雪芹死後八、九年他才出生。明義姓富察,是承恩公富文之侄、都統富清之子;而根據《玉牒宗室譜》稿本,得知裕瑞之母是「富察氏承恩公富文之女」、都統富清之侄女,二人是舅甥關係。《棗窗閒筆》裡說:「雪芹二字,想係其字與號耳,其名不得知。……聞前輩姻戚有與之交好者。」裕瑞這裡所說的與曹雪芹「交好」的「前輩姻戚」,顯然是指明義家族。順帶說一句,如此又增加了明義所說的「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云云的可靠性。總之,倘若明義等人從曹家得來的是第一手證據,那麼傳到裕瑞那裡已成為第二手。哪一邊的證據可靠些,是很清楚的。
實際上,只要對裕瑞的「聞舊有《風月寶鑑》一書」云云略加研究,便知他所標榜的這種「聞」與程偉元的〈紅樓夢序〉中一段話差別不大:此書「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書內記雪芹曹先生刪改數過」。因此,關鍵問題還在於如何理解《紅樓夢》第一回裡的以下這一段話:
(空空道人)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云: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
該如何正確理解這段話呢?這就有必要先看一看甲戌本的兩條重要眉批。一條是批在「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上:
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懷舊,故仍因之。
另一條是批在「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上:
若云雪芹披閱增刪,然後(則)開卷至此這一篇楔子又係誰撰,足見作者之筆狡猾之甚。後文如此處者不少。這正是作者用畫家煙雲模糊處,觀者萬不可被作者瞞弊(蔽)了去,方是巨眼。
照戴不凡先生的看法,書裡「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云云,乃是「棠村為舊稿《風月寶鑑》寫的序」。脂批「故仍因之」是「故仍用之」之誤,「用之」就是「把已故的棠溪(應為棠村)」寫的這段舊序「用」在這裡。而從這段舊序,可以看出「小說的寫作過程原來明分兩個階段:先是那個被稱為『石兄』、自稱為『石頭』的作者業已『編集在此』的一部『自敘』性質的小說,由後來易名為『情僧』的空空道人抄錄回來問世傳奇,他『改《石頭記》為《情僧錄》』;同時又被人題以《紅樓夢》、《風月寶鑑》等等不同書名。到了第二階段才是曹雪芹在石兄舊稿基礎上『披閱十載,增刪五次』,改寫成為《金陵十二釵》,即今天我們所說的《紅樓夢》」。這看法,我難以理解。若說這段話是「棠村寫的《風月寶鑑》舊序」,「序」上豈能道出此書以後的修改情況?假若果真如此,那麼,這篇「棠村寫的《風月寶鑑》舊序」究竟是「序言」呢,還是個預卜此書未來命運的「預言」?
照戴不凡先生的看法,脂批「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云云,這裡的「有」,指「藏有」,不是「著有」;雪芹「藏」的這部「石兄」的「舊稿《風月寶鑑》原為一部黃色小說」。雪芹的功績是在一個「改」字上。這看法,我也難以理解。假若果真如此,那麼,棠村是弟,雪芹是兄且是此書的收藏者,何以讓棠村作序而雪芹自己不作?「石兄」的「舊稿《風月寶鑑》」和空空道人「改《石頭記》為《情僧錄》」的那「舊稿」《石頭記》是什麼關係?「第一階段」,那「作者群」把「舊稿」《石頭記》一改而為《情僧錄》,再改而為《紅樓夢》,三改而為《風月寶鑑》(新稿?),這樣改來改去,是否也改動了內容;而雪芹是此書的收藏者,何以倒不參加這個「作者群」?「第二階段」,雪芹一動手,又何以要把那個「作者群」統統拒之於「悼紅軒」之外,獨自一人「披閱十載,增刪五次」?《金陵十二釵》與「舊稿」《石頭記》在思想傾向上有無不同?倘若沒有,雪芹的手「巧」在哪裡;倘若有,脂硯齋把《金陵十二釵》又改題為《石頭記》,「石兄」、「作者群」、曹雪芹何以皆大歡喜;脂硯齋又何以如此地薄曹雪芹而厚「石兄」?
照戴不凡先生的看法,脂批「若云雪芹披閱增刪」云云,所謂「後文如此處者不少」,「那是說後面還有不少章節是雪芹自撰;但是其他部分則是根據他人舊稿增刪改寫的」。因為「如果書前所列的『作者群』全是雪芹自布的『疑陣』,小說是由雪芹一手創作而成,那麼,脂硯齋在這裡就毋需說什麼『然則這一篇楔子又係誰撰』;他還要特地點明『後文如此處者不少』,就變成完全多餘的廢話了」。這看法,我又難以理解。假若果然如此,那麼,曹雪芹在「披閱十載,增刪五次」中的「增」,這「增」可以不可以稱為「自撰」?「根據他人舊稿增刪改寫」部分中的「增」,這「增」可不可以稱為「自撰」?「增」和「自撰」的界說是什麼?倘說「披閱十載,增刪五次」中的「大增」可以稱為「自撰」,那雪芹是直言不諱的,脂硯齋還要加這條批豈不是饒舌?倘說以不動「石兄舊稿」的筋骨為前提的「小增」筆墨謂之「增」,這種「據石兄舊稿增刪改寫的」部分能改變其「黃色小說」性質嗎?倘說上述的「自撰」部分與「增刪改寫」部分的合璧,便產生了如此偉大的古典小說,這實在教人無法置信。
照我的淺見,上引「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云云,乃是小說家言。這在中國的小說中尤其屢見不鮮。《兒女英雄傳評話》首回就曾自敘該書有過幾個不同的書名,而魯迅先生評云:「多立異名,搖曳見態,亦仍為《紅樓夢》家數也。」(《中國小說史略》)凡讀過魯迅先生《狂人日記》的人,都知道這篇小說有篇小序。假若誰依據那序中所述便以為這篇「日記」真是某君昆仲於病中所寫,魯迅只是這篇「日記」的修改者,我想,和者一定甚寡。
照我的淺見,上引「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云云,乃是說雪芹曾著有《風月寶鑑》一書,這部書的序言是他的弟弟棠村作的。現在棠村已死,由於「睹新懷舊」,所以仍用《風月寶鑑》這個書名。甲戌本「凡例」說:
是書題名極多:《紅樓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寶鑑》,是戒妄動風月之情;又曰《石頭記》,是自譬石頭所記之事也。此三名皆書中曾已點睛矣。如寶玉作夢,夢中有曲,名曰《紅樓夢十二支》,此則《紅樓夢》之點睛。又如賈瑞病,跛道人持一鏡來,上面即鏨「風月寶鑑」四字,此則《風月寶鑑》之點睛。又如道人親眼見石上大書一篇故事,則係石頭所記之往來,此則《石頭記》之點睛處。然此書又名曰《金陵十二釵》,審其名則必係金陵十二女子也。
也就是說,四個題名是從不同角度取的,指的是同一部書,並不是反映什麼「小說的寫作過程原來明分兩個階段」。無疑,「凡例」裡所說的《風月寶鑑》,指的就是《紅樓夢》,並不是棠村序本《風月寶鑑》。然而,我們卻由此可以看出棠村序本《風月寶鑑》與《紅樓夢》的關係:二者只有規模的不同和藝術性高低的差別,思想傾向是一致的;後者的創作可能曾以前者做基礎,但前者的原有情節入後者當是融入而不是雜陳。
照我的淺見,上引「若云雪芹披閱增刪」云云,「又係誰撰」是針對「披閱增刪」而言的。意思是說:假若說你曹雪芹只是個修改者,那麼,這麼長的一篇〈楔子〉又是誰寫的呀?弦外之音自明:你曹雪芹不只是此書的修改者,而且是此書的撰寫者。「後文如此處者不少」,絕不是指「後面還有不少章節是雪芹自撰」,而是說後面像這裡的「畫家煙雲模糊」筆墨還有很多。何以見得?後面凡遇此等筆墨,脂批不是寫著「欲瞞看官」,就是寫著「幾被瞞過」,或者寫著「亦作者欲瞞看官,又被批書人看去(出),呵呵」,足可證明。寫到這,我想補充說一點: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僅憑我們前面所引的袁枚的一段話,便斷言《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理由確實不充分。然而,就他的這項論斷本身來說,還是對的。判斷某個觀點是否正確,不應依據它是出自誰口,而應看它有沒有道理、符合不符合客觀事實,似不應把胡適說的話一概斥之為「胡說」,似不應把「胡適」派說成「胡(適)說」派。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紅樓夢考論(上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70 |
文學 |
$ 285 |
中文書 |
$ 285 |
中國古典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紅樓夢考論(上冊)
紅塵中的確有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
瞬息間則又樂極生悲,人非物換,
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皆空。
本書對小說文本的研討,辯證地運用還原批評和接受美學相結合的方法,且嘗試著將文本、文獻、文化作整合一體的研究。這在方法論上也是個可喜的創獲,令人耳目一新。
本書是作者自一九八二年以來從事《紅樓夢》研究的心血結晶,關於紅學考證與論述的又一部力作。上編三篇,考中含論,從不同角度考證了《紅樓夢》的著作權、曹雪芹的生卒年,以及小說的成書過程和大觀園的時間跨度等重要問題。中編十篇,論中含考,從不同層面研討了《紅樓夢》的思想意蘊、主題學、結構學、文化學、審美特徵等。下編五篇,就《紅樓夢》的道德觀念、人性觀念、審美觀念、社會觀念,分別與中國另五大古典小說作了比較研究,以見其對傳統思想和寫法的打破。
作者簡介:
張錦池,1937年2月生,江蘇靖江人。196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哈爾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學科領導人。著有《紅樓十二論》、《紅樓夢考論》、《中國四大古典小說論稿》、《西遊記考論》、《中國古典小說心解》、《漫說西遊》等多種,以及論文多篇,亦為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紅樓夢》新校本注釋者和注釋定稿者之一。
1986年中國人事部授予「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1991年獲中國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03年獲中國首屆國家級高校教學名師獎,2008年獲黑龍江省「龍江文化建設終身成就獎」。社會兼職有:中國紅樓夢學會副會長、《文學遺產》編委、《紅樓夢學刊》編委等。
TOP
章節試閱
《紅樓夢》作者考
一 小引
《紅樓夢》的作者是誰?是曹雪芹,可又不時有人提出質疑。《北方論叢》1979年第1期發表的戴不凡先生的〈揭開《紅樓夢》作者之謎〉,就是一篇具有代表性的質疑文章。「謎」底是:「曹雪芹是在石兄《風月寶鑑》舊稿基礎上巧手新裁改作成書的。」
認為曹雪芹只是《紅樓夢》的改寫者而不是原作者,這說法雖則並非始於戴不凡先生,乃是歷史上的一種意見;然而戴不凡先生從多方面作了考證、論述,提出了有關的新見,這對於我們進一步研究《紅樓夢》的作者問題頗具啟發。這是個沒有真正解決而又值得探討的問題。因為...
一 小引
《紅樓夢》的作者是誰?是曹雪芹,可又不時有人提出質疑。《北方論叢》1979年第1期發表的戴不凡先生的〈揭開《紅樓夢》作者之謎〉,就是一篇具有代表性的質疑文章。「謎」底是:「曹雪芹是在石兄《風月寶鑑》舊稿基礎上巧手新裁改作成書的。」
認為曹雪芹只是《紅樓夢》的改寫者而不是原作者,這說法雖則並非始於戴不凡先生,乃是歷史上的一種意見;然而戴不凡先生從多方面作了考證、論述,提出了有關的新見,這對於我們進一步研究《紅樓夢》的作者問題頗具啟發。這是個沒有真正解決而又值得探討的問題。因為...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紅學的新貢獻 馮其庸
錦池先生的大著《紅樓夢考論》即將問世了,要我寫幾句話作為序言,我當然無可推辭。
我認識錦池先生是在1975年,至今已二十三年了。1977年我們又一起校注以庚辰本為底本的新版《紅樓夢》,十來位各地來的專家聚集在一起,從《紅樓夢》的抄本到文句的注釋,一一從頭討論,這樣大約有兩年左右。這兩年左右,實在是一次寶貴的難得的聚會,現在回憶起來還令人神往。這次聚會的成果,又經過後來反覆訂正修改,就是1982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新校注本《紅樓夢》。
從1977年聚會至今的二十多年來,當年與會的諸公都...
錦池先生的大著《紅樓夢考論》即將問世了,要我寫幾句話作為序言,我當然無可推辭。
我認識錦池先生是在1975年,至今已二十三年了。1977年我們又一起校注以庚辰本為底本的新版《紅樓夢》,十來位各地來的專家聚集在一起,從《紅樓夢》的抄本到文句的注釋,一一從頭討論,這樣大約有兩年左右。這兩年左右,實在是一次寶貴的難得的聚會,現在回憶起來還令人神往。這次聚會的成果,又經過後來反覆訂正修改,就是1982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新校注本《紅樓夢》。
從1977年聚會至今的二十多年來,當年與會的諸公都...
»看全部
TOP
目錄
紅學的新貢獻——《紅樓夢考論》序 馮其庸
前言
上編
《紅樓夢》作者考
一 小引
二 乾隆年間的看法
三 脂硯齋們的說法
四 如何理解書中的「矛盾現象」
曹雪芹生年考
一 引言
二 評胡適的前後三種說法
三 評周汝昌的「雍正甲辰」說
四 評李玄伯的「康熙乙未」說
五 說曹雪芹生於康熙戊戌年
六 說曹雪芹的卒年問題
巧姐的人生歷程及大觀園的時間跨度考
一 小引
二 巧姐與大姐:說《紅樓夢》創作過程中的一些問題
三 巧姐與香菱:說巧姐被賣時的年齡與大觀園的時間跨度
四 巧姐與二丫頭...
前言
上編
《紅樓夢》作者考
一 小引
二 乾隆年間的看法
三 脂硯齋們的說法
四 如何理解書中的「矛盾現象」
曹雪芹生年考
一 引言
二 評胡適的前後三種說法
三 評周汝昌的「雍正甲辰」說
四 評李玄伯的「康熙乙未」說
五 說曹雪芹生於康熙戊戌年
六 說曹雪芹的卒年問題
巧姐的人生歷程及大觀園的時間跨度考
一 小引
二 巧姐與大姐:說《紅樓夢》創作過程中的一些問題
三 巧姐與香菱:說巧姐被賣時的年齡與大觀園的時間跨度
四 巧姐與二丫頭...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張錦池
- 出版社: 龍視界 出版日期:2015-09-12 ISBN/ISSN:978986562020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58頁 開數:14.8*21 cm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中國古典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