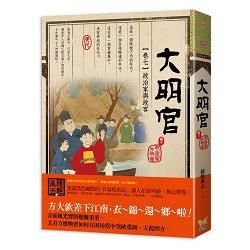在方大知縣的勤懇治理下,
宛平縣的縣務蒸蒸日上。
待他任滿的時候,恰又遇到劉棉花攜劉府小娘子回京。
憑藉現有政績,
實現升職、加薪、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的巔峰的道路!
可偏偏事情卻不是方應物所想的那麼容易,
先有隔壁縣同僚眼紅背後使壞,
後又捲入科舉舞弊謠言的漩渦當中,
待他好不容易脫身,
正想著接下來將換到哪個官位之時,
一道詔書下來徹底打懵了他!
他竟被安上了下江南去督收錢糧、清理田土的工作!
說得好聽是欽差御使,
可說白了,就是幫朝廷討債去了,
天下沒有再比這個還要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了!
在京城已經闖出名號的方小青天,
接下來要面對的,
將是由士紳、地方官以及欽差太監所組成的龐大挑戰……
本書特色
起點中文網歷史分類榜第一,累積三百萬點擊,五十萬推薦!
充滿黑色幽默的「官場現形記」,讓人拍案叫絕,無法釋卷!
趣味橫生、妙語如珠,讓成化年間明代科舉、政治、官場形象一一呈現眼前。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大明官 卷七 政治家與政客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大明官 卷七 政治家與政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