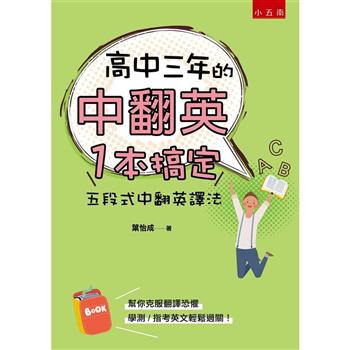第十一章
一晃眼就到了正月十四,余舒大清早就從紀家出門,前天去找賀郎中取藥時被趙慧叮囑要她今日早點過去,他們要提前一天給她過生日。
紀星璇昨日擲夠了六爻八象,「起卦」這頭一步學會了,余舒接著又教她六爻的「裝卦」,不過只說了其中納甲和世應兩個步驟,沒講解卦宮和用神這兩步,這次余舒不讓她擲銅板了,教了個半吊子,就讓紀星璇回去裝上兩百卦,變著法地給她找事幹,騰出幾日空閒。
余舒老遠就瞧見余修站在趙慧家門口等她,喊他一聲,那小孩兒就興沖沖地跑過來,看見余舒比看見誰都高興。
「姐,吃早飯了嗎?」
「沒吶,家裡有飯嗎?」
「嗯!慧姨讓廚子給妳熬了紅豆子甜粥,還煮了一鍋雞蛋,等妳回來吃呢。」
余舒被余修拉回家,先到後院去見趙慧,堂屋裡,賀芳芝正在給趙慧把早脈,看兩個孩子走進來,便笑著讓他們過來坐下。
因為趙慧不便挪動,一家人就把飯桌挪到屋裡吃早飯,余舒在趙慧期待的目光下,硬是喝下兩碗粥,吞了三顆雞蛋。
大安朝民間有一個說法,男孩兒生日不曉得,但未嫁人的女兒過生日一定要喝甜豆粥,象徵日後婚姻美滿,那子時半夜煮的雞蛋則象徵著多子多福,吃得越多越好。
早飯後,趙慧把賀芳芝和余修攆出去,讓芸豆從屋裡抱了一身新衣服出來,將余舒拉到身邊比劃,較深一點的藍色布料很襯余舒並不太白的膚色。
余舒很喜歡趙慧這種待她像親女兒一樣的態度,嘴裡甜甜地喊了一聲「謝謝乾娘」,便抱著新衣進屋去換了,她那天在忘機樓量的衣裳還沒有做好,今天出門穿的是過年趙慧給她做的新衣,只少套了一件夾襖。
換好新衣,趙慧又在余舒頭上添了一支點翠的白玉簪子,說是賀郎中送的。
「這樣多好,越來越有姑娘家的樣子,過明日就是十六歲的大姑娘了。」趙慧愛憐地攏了攏余舒的耳鬢,十分心疼這個命運波折的孩子,每每看到她就好像看到自己當年,無依無靠只能自己努力地過活。
以前是她日子過得苦,不能為她多做什麼,現在一切都好了,作為一個長輩,該能盡的心她都想盡到。
快到中午的時候,裴敬也來了,只不過兩手空空,讓趙慧笑話:「義兄今日怎麼小氣起來,孩子過生兒你什麼都沒拿,就帶了一張嘴來嗎?」
裴敬哈哈一笑,「誰說我沒帶禮,這不是麼。」說著他從後腰上抽出一樣東西遞給余舒,「拿著,可別說舅舅對妳不好,為這份禮我可是費了一番力。」
遞到余舒手上的,卻是一根用紅皮子裹的細長馬鞭,瞧得余舒一頭霧水,賀芳芝夫婦也不解其意。還是余修聰明,一拍巴掌站起來,興奮道:「您是要送姐姐一匹馬?!」
裴敬伸手摸摸他腦袋,笑道:「可不是麼。」
余舒早惦記著要買馬騎,年前就向裴敬打聽過這買馬的事,裴敬就留了心,剛好碰到門路,前幾日聽說了余舒過生,就趁機當成禮物。
幾人一聽,頓時傻眼,是因裴敬這便宜舅舅當的,比親爹都大方。
「我們泰亨商會底下管著幾個走馬的販子,前幾日才送了一批好馬進京,我搶先去挑了挑,給妳選了一匹性情溫和的母馬,剛有三歲大,本來今早上是想帶過來,因牠鬧了肚子只好作罷,過兩日妳再去牽牠。」
這禮太厚,余舒簡直不好意思受,能送到京城來賣的馬,想也知道不便宜,尤其是能配對的母馬,沒個二三百兩就摸馬屁股去吧。
趙慧和賀芳芝雖同樣覺得這禮過重,但不好插嘴,裴敬是個人精,看出他們心思,便對余舒道:「怎麼妳不想領舅舅的情?傻孩子,沒看出來這是舅舅在巴結妳呢,等回頭大衍放榜,妳這個年紀的大算師,多少人爭著搶著要,舅舅到時候就是想巴結也巴結不上了,這不趁早嘛。」
余舒一聽這話,立馬就笑了,她豈不知裴敬為人,他這話就算是真的,這話裡的情分也不是假的,她再扭扭捏捏地推拒,倒顯得不夠坦蕩。「謝謝舅舅!」
「哈哈,這就對了。」
趙慧看他們你情我願的,便沒插嘴,余修最是高興,坐到裴敬身邊一個勁兒地詢問那匹馬的事。
芸豆去廚房看了一圈回來,告訴說是飯菜準備好了,賀芳芝看看外面日頭,詢問余舒:「怎麼還不見曹掌櫃的來?沒說錯日子吧?」
趙慧為了給余舒過個熱鬧的生兒,就想多請一些人,奈何安陵裡沒幾個熟人,算來算去就那幾個,請了裴敬,又交待余舒邀請「曹子辛」。
「和他說是今天。」余舒站起來,看看外面:「你們先到客廳去坐,我出去瞧瞧。」
初九那天交完帳後,余舒好幾日都沒見到薛睿的人,忘機樓明天就要正式開張了,薛睿昨天下午才在酒樓露了一面,匆匆地來,交待了林福幾件事就又匆匆地走,余舒就來得及和他說上兩句話,一句打招呼,一句就是說她十四這天在趙慧家做生日請他來,薛睿當時是應了會到場。可是這會兒都快該吃午飯,還沒見到人影。
余舒在大門外等了一會兒,就見一道馬影從街頭跑過來,停在門前下馬的,是平常駕馬車的老崔,氣喘吁吁地喊了余舒一聲,先禮道:「姑娘,問姑娘生日好。」
余舒看他一個人跑來,就猜到薛睿是有事不能來了,果然,老崔喘了兩口氣接著道:「大少爺讓小的來帶話,他今天過不來了,讓姑娘不必等他。」
余舒有些失望,卻沒表現出來,「我知道了,老崔進來坐吧,飯菜都擺好了,同我們一起熱鬧熱鬧。」
「姑娘好意,我這還有別的事急。」老崔遲疑了一下,又左右看看無人,往前湊了湊,輕聲對她道:「實話告訴姑娘說,少爺今日實在是脫不開身,九皇子前日回京了,今天早上奉了貴妃娘娘的諭出宮來府上見親,一家老小都接著呢。」
這內情讓余舒聽得一愣,九皇子,是哪個?
「還有,大少爺交待姑娘明日及早到忘機樓去,能早不能遲,小的這就走了,您進去吧。」
老崔帶了話,便急忙走了,余舒一個人在門口站了會兒,想來想去,覺得這九皇子應該就是薛家那位貴妃娘娘的兒子了。
「姐,曹大哥來了嗎?」
余修的喊聲在背後響起,余舒停下思緒,轉過身向院子裡走:「沒有,剛才老崔來送話,他今天來不了了。」
◎
余舒在趙慧家待到下午才走,趙慧有意留她吃晚飯,被余舒找由頭婉拒了,趙慧怕她回去晚了,就沒有挽留,包了幾顆雞蛋,一盒月餅又給灌了一壺米酒,讓她帶回去給翠姨娘。
余修送余舒出門,到街口停下,從懷裡掏出一只小袋子,扭捏了一下,遞與她。「給。」
「喲,你也給我備了禮物?」余舒笑著接過去,摸那袋子裡頭似裝著一些條狀物,解開來看,誰想到會是五六根打磨好的炭筆。看粗細像是柳枝燒的,難得的是沒裂開一根,還細心地磨尖了筆頭,筆身上還套了一個精緻小巧的布筆套,以防握筆時手指沾上黑。
「呀,你做的?」
看到余舒臉上驚喜,余修靦腆道:「開始燒了很多都不好,就找了賀叔幫忙,那筆套子是請芸豆給縫的,我知道妳不愛用毛筆,寫字又慢,偶爾用用這個倒沒什麼,姐,妳晚上別總學到很晚,早點睡,賀叔說熬夜對身子不好。」
聽這一席話,余舒老懷大慰,差點掉下眼淚,只覺得手裡這輕輕的一袋子炭筆頭,是今天收到最好的一份禮物了,有十匹馬她都不換。忍不住伸手摟了摟余修,余舒道:「好弟弟,你送這禮物姐姐很喜歡,會好好用的。」
余修被她當街抱住,不好意思地擰了擰身體,彆扭道:「妳還是盡快把毛筆使好才是正經,這個寫的字哪能見人。」
余舒嘻嘻一笑,拍拍他肩膀鬆開他,口諾道:「明日我就買了字帖練字去。」
姐弟倆又膩歪了一會兒,才道別,余修等到余舒人在街角不見,轉身回去。
余舒卻在下一條街換了個方向,趁著天亮往城南走去,沿途路過街市,進了幾家店鋪,手上大包小包越來越多,等到了回興街,已經手提不下。
熟門熟路地進了小巷,在巷尾緊鎖的一間院門前停下,四下無人,余舒騰出一隻手從脖子上摘了鑰匙,將門打開,「吱呀」一聲推門進去,反手將門帶上,落了門閂。
久未住人的小院裡透著一股冷清氣息,余舒進大屋將大包小包都放下,被灰嗆了兩口,手在鼻子前揮了揮,皺皺眉頭,明天景塵就要回來了,她得先將這裡收拾乾淨才行。
余舒退到屋門口,環顧四周的蜘蛛網和土灰,挽起了袖子,插在腰上,輕呵了一口氣,幹勁十足!
◎
正月十五,元宵佳節,也是忘機樓開張的好日子。
早起紀府就有跡象,園子裡的燈籠全換了一批,新一簇的大紅色,說不出的喜慶,就連余舒住的小院外頭都被人掛了兩只應景。
余舒留下話就出了門,她今天事多,先是忘機樓正午開門,不知要忙到什麼時候,晚上還要接余修去陪翠姨娘過節,若有空閒,她想再到回興街上去看看,說不定景塵是今晚還是明早會回來。
駉馬街上今日人來人往,附近幾條街上的茶館店鋪像是約好了一樣都在今天開了門,安陵城裡三元(注:農曆初一。)晝夜不禁宵、不禁販、不禁聲,城南的小商小販都流動到了城北,攤子架子一個個在路邊支起來,各式各樣的彩燈掛出,又有捏湯圓子賣吹糖人的,這會兒還不見怎麼喧譁,但想入夜點了燈會更熱鬧。
余舒特意從忘機樓前門經過,不意外看到樓外那典雅氣派的門臉上多了一塊紅綢搭的橫長匾牌,橫空結彩,花團錦簇,招了許多路人側目,只是大門未開。繞到後門進去,竟是亂糟糟的,原本空蕩蕩的後院裡到處擺放著雜物,林福正指揮著貴六和幾個臨時雇來幫工的夥計上下抬放,看到余舒,紛紛放下手中的活問好。
余舒示意他們繼續幹,轉身進了樓後的廚房,秀青正帶著兩個廚子在準備今天要用到的點心,一橫兩丈長的灶臺上架著七八個蒸籠,熱氣騰騰地冒著白煙。再到前樓,桌椅板凳都規整,櫃檯後面上了十五六罈老酒,小蝶小晴正在樓梯上貼彩紙,離地七尺高,頭頂上縱橫懸掛了近百只彩燈,全是方孔形狀的宮造,余舒知道上面黑黑小字都是謎題,這是今天開張的一個噱頭,凡摘燈能解謎者皆可免一桌的酒菜錢,薛睿這一招使得厲害,不可謂不是大手筆。
樓前樓後都在為中午開張做最後的準備,大家都忙得團團轉,算來只有余舒一個閒人。
余舒看沒她什麼事幹,就上了二樓,昨天去趙慧家過生辰將金寶留給了余修,怕今天人多牠亂跑。
她剛拿了帳本在書桌前坐下,小晴就來敲門,說是熱水燒好了請她沐浴更衣,又稱昨天下午裁縫將製好的新衣送了來。
「姑娘昨天沒來,衣裳到放到隔壁屋去了,奴婢給您拿過來看看,針線縫得可仔細了。」
余舒一聽來了神,就讓她送到這屋裡,小晴去去抱了一摞整齊疊好的衣物,放在榻上余舒一件件抖開來看,竟比那天畫兒上的還要精緻如意,不禁喜歡。
便讓小晴使人送熱水上來,她待洗一洗再更換了衣物。
◎
余舒洗好了澡坐在雅房裡,穿著乾乾淨淨的白裡衫,披著一件棉襖坐在花梨矮腳妝鏡前,臉蛋被熱水蒸得粉紅,不知是否她這幾日服用藥丸的好處,臉上病黃褪去,皮膚光滑了許多。
旁人挪不開手,小晴就去樓後頭請了琴師白氏給她梳頭。
「姑娘想要怎麼打扮?」白氏人長得就秀靜,說話更是溫聲細語的。
余舒心想著待會兒要穿胡服,就說:「梳個簡便的,爽利的樣式,不要那麼多髻髻角角。」
白氏領會,又看妝臺上沒幾件簪頭的東西,就拿梳子箅著她剛剛擦乾的頭髮,道:「那就綁個朝天髻,我拿絲帶給姑娘纏個髮箍,並一根白玉簪子,不用戴什麼銀紅疊翠,就很好看。」
余舒不懂這些,就隨意地說好,等到頭髮束好才道漂亮,她五官並不精緻,勝在長了個標準的鵝蛋臉,真效了那些名門閨秀去雲鬢花釵反倒沒有樣子,似這樣大大方方露出額頭和整張臉來,眉目清晰,反而俊秀。
再換上胡服短靴,窄腰平肩,往鏡子前一站,那人就更精神了,手腳修長,比女子多三分挺拔,五官明朗,比男兒勝三分姿態。
小晴捧著茶盞站在一旁,看著余舒,微微紅了臉,那白氏也不好意思多盯著余舒瞧,又沾黛粉稍微修了修她的眉形,便告退下去了。
這時候,有人在門外說話:「姑娘收拾好了嗎,公子爺來了,請您下樓去見他。」
余舒正在手上擦蛇油膏,聽到薛睿來了,便應一聲:「這就下去。」
◎
「大哥,你來了。」
樓下小廳,薛睿在聽林福回報事宜,聞聲轉頭,見那門扉處陽光灑進,余舒一身乾淨俐落地走進來,上穿著墨綠雜染織錦的窄袖束胸長翻領,板板正正地垂到膝下,露出一條木蘭色的纖細褲腿,筆直地緊紮在小皮靴裡,背在光裡,修長挺拔的身段一覽無遺,青絲成束,面含皎光,掃眉若異,活脫脫似從前朝壁畫上走下來的胡虜貴女。
縱薛睿至今見過形形色色之女子,這一時眼裡也不由地被她晃了下眼睛。
余舒倒是沒注意到薛睿眼中異樣,走過去還在他面前站了站,整了整領子讚道:「你找那兩個裁縫手藝真是好極了,這衣裳我穿著很合身。」
薛睿笑笑回過神,端起了茶杯掩飾心中那一絲騷動,道:「合意就好,下次再找她們來。早上吃飯了嗎?」
余舒茶座另一旁的太師椅上坐下,道:「嗯,來時路上就吃了。」
薛睿道:「我讓他們備菜,待會兒妳再吃點,等到中午廚房一忙照應不來。」
余舒說好,薛睿看了看她,又道:「昨日我沒能如約去赴妳的生日宴,妳可有不高興?」
余舒笑道:「哪有那麼小氣,你又不是故意不來。」
薛睿點點頭,道:「想必老崔和妳說了,九皇子歸京,昨日出宮到我們府上,我不便離開。」
余舒正對這九皇子有些好奇,聽他主動提起,看上去並無避諱,就順勢問道:「這九皇子離京在外很久嗎?怎麼我在京中都沒有耳聞過他的事。」
薛睿倒了杯茶遞給她,道:「妳不知也不怪,九皇子乃是貴妃娘娘所出,實為我表弟,因他兒時身體孱弱,常招鬼神之困,就被送到山中道派聖地清修,每三年才回京一次,不常露面所以少為人提起。」
「哦,原來如此。」
聽了這九皇子的事,余舒不禁地想起景塵來,同樣都是為了保命被送到道門中,這九皇子猶能三年回來一次見見親人,可是景塵卻一待就是十八年,好不容易下一次山,回京路上又波折重重,險丟性命。就不知道這九皇子和景塵是不是同在一個道派?
「公子爺,飯菜備好了。」
余舒剛聯想到點什麼,就被門外說話聲打斷,收起思緒,跟著薛睿到隔壁去用飯。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萬事如易(第二卷):善惡昜知,是非難說(2)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99 |
二手中文書 |
$ 205 |
中文書 |
$ 205 |
言情小說 |
$ 221 |
穿越文 |
$ 221 |
小說/文學 |
$ 234 |
華文羅曼史 |
$ 234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萬事如易(第二卷):善惡昜知,是非難說(2)
《新唐遺玉》作者三月果歷時三年完成的長篇大作!
奇門遁甲這類學問在此時代竟有如此大用?
且看小女子余舒如何運用精算師頭腦配合易學,谷底翻身、出人頭地!
上輩子,她昧著良心賺錢;
這一世,她要活得乾淨自在!
「我乃雲華易子同昔年麓月公主之子。」
先前景塵對余舒剖白的身世,在司天監張貼尋人榜文後,
那些想藉此撈得好處的人,開始暗中算計──
紀星璇工於心計,和祖父紀懷山共謀,構陷余舒。
基於種種緣由,再者加害景塵之人的身分亦尚未可知,
余舒有口難言,只能受酷刑折磨。
雖幸而有薛睿及時出現,設法解救,
可這紀家,難道當她是好欺負的嗎!
憑著尋回的擋厄石,再加上手握大衍試盜題一事的內情,
紀家那對祖孫可要小心了,
她余舒,絕對會狠狠討回這筆帳的!
本書另收錄未公開番外<紀星璇篇>。
作者簡介:
三月果
暱稱果子,性別女,年齡不詳,身高不明,體重不定,說話沒有打字快,患有嚴重拖延症。家有一隻愛貓,現為鏟屎官一名。歡迎關注本人新浪微博——三月果熟了。
TOP
章節試閱
第十一章
一晃眼就到了正月十四,余舒大清早就從紀家出門,前天去找賀郎中取藥時被趙慧叮囑要她今日早點過去,他們要提前一天給她過生日。
紀星璇昨日擲夠了六爻八象,「起卦」這頭一步學會了,余舒接著又教她六爻的「裝卦」,不過只說了其中納甲和世應兩個步驟,沒講解卦宮和用神這兩步,這次余舒不讓她擲銅板了,教了個半吊子,就讓紀星璇回去裝上兩百卦,變著法地給她找事幹,騰出幾日空閒。
余舒老遠就瞧見余修站在趙慧家門口等她,喊他一聲,那小孩兒就興沖沖地跑過來,看見余舒比看見誰都高興。
「姐,吃早飯了嗎?」
「沒吶,...
一晃眼就到了正月十四,余舒大清早就從紀家出門,前天去找賀郎中取藥時被趙慧叮囑要她今日早點過去,他們要提前一天給她過生日。
紀星璇昨日擲夠了六爻八象,「起卦」這頭一步學會了,余舒接著又教她六爻的「裝卦」,不過只說了其中納甲和世應兩個步驟,沒講解卦宮和用神這兩步,這次余舒不讓她擲銅板了,教了個半吊子,就讓紀星璇回去裝上兩百卦,變著法地給她找事幹,騰出幾日空閒。
余舒老遠就瞧見余修站在趙慧家門口等她,喊他一聲,那小孩兒就興沖沖地跑過來,看見余舒比看見誰都高興。
「姐,吃早飯了嗎?」
「沒吶,...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三月果
- 出版社: 知翎文化 出版日期:2015-10-08 ISBN/ISSN:978986562546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68頁 開數:14.8cmx21cm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