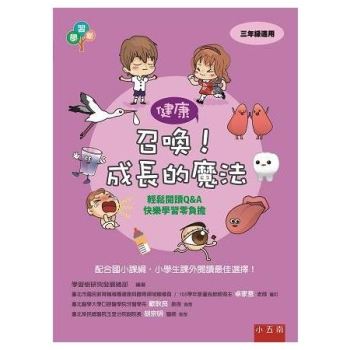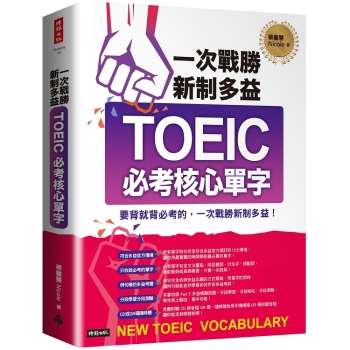生了孩兒之後的周少瑾,生活過得越來越順,
丈夫程池官運亨通,婆婆郭老夫人對她益發疼愛,
身邊的姊妹們,日子也過得很是滋潤,
怎麼看,都沒有什麼事值得她擔心。
可少瑾沒有忘記前世曾經發生過的事。
程家,最終走入了被滿門抄斬的悲慘命運。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這樣詩書耕讀之家,
被皇家如此嫌惡,甚至殘忍下手呢?
少瑾已細細將前世她所知道的事全都告訴了程池。
有了程池的謀畫與調查,
就算是面對朝廷上的人事鬥爭,
爭皇位的腥風血雨,
這一世的程家,肯定能避過禍事,安全度過滅頂之災!
本書另附四篇實體書番外。
本書特色
《九重紫》作者吱吱全新重生宅鬥代表作!
鴛鴦交頸,花好月圓
少瑾和程池,成親了!
他的小姑娘像艘漂泊良久的小舟,終於停靠在了他的港灣。
他又怎麼會如此的幸運。
茫茫塵世間,她重生,都要遇到他。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金陵春 卷十(完)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05 |
小說 |
$ 205 |
古代小說 |
$ 205 |
言情小說 |
$ 221 |
古代小說 |
$ 234 |
中文書 |
$ 234 |
華文羅曼史 |
$ 252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金陵春 卷十(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