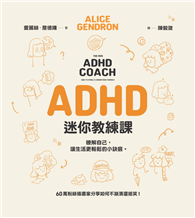《新唐遺玉》作者三月果歷時三年完成的長篇大作!
奇門遁甲這類學問在此時代竟有如此大用?
且看小女子余舒如何運用精算師頭腦配合易學,谷底翻身、出人頭地!
上輩子,她昧著良心賺錢;
這一世,她要活得乾淨自在!
奇門遁甲這類學問在此時代竟有如此大用?
且看小女子余舒如何運用精算師頭腦配合易學,谷底翻身、出人頭地!
上輩子,她昧著良心賺錢;
這一世,她要活得乾淨自在!
因著一場陰謀,余舒被迫下獄,
大提點尚未歸京,在無人搭救之下,
私刑吊拷等手段,皆被殘忍地施加其身。
然她余舒豈會有仇不報?
此番鬼門關前走一遭,對方沒能弄死她,
那麼待她好轉之時,就該是她還手的時刻了──
此逢新舊交替之際,一朝天子一朝臣,
顯赫一時的薛家滿門獲罪,
而歷經劫難的余舒,則成了第十一代大提點。
如今的她位極人臣,處於權力之巔,
可薛睿,卻也已是敵國大燕的異姓王爺。
兩軍交戰,烽煙四起,
分離多年,各自努力的兩人,又將如何重新走到一起?
本書收錄番外〈白冉的祕密〉及未公開番外〈大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