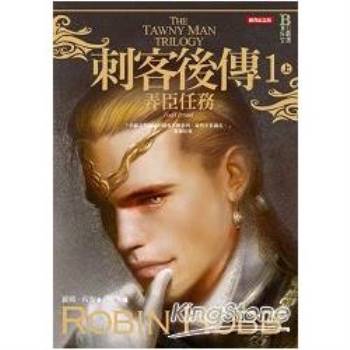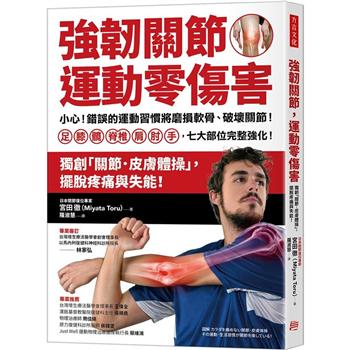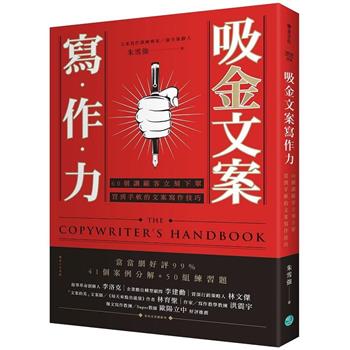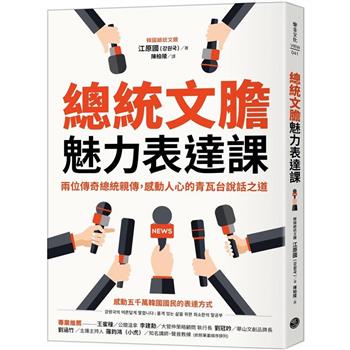慶瀚教授是我的同宗兄弟,也是中央大學不同科系的同事。慶瀚在法國讀博士,學的自然科學,同時又修了兩年的文學博士課程。讀他的文章,像是喝法國葡萄酒一般,充滿溫情和些許的浪漫。長慶兄是著名的小說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有一段金門軍中服務處的特殊經歷,小說的題材別出匠心……
本書是《東吳小記》的姐妹篇,收錄序跋小品四十多篇,每篇不過三千來字。來不可遏,去不可止,有時興頭一來,下筆千言,不能自休;有時文思枯竭,三天不能一字。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慶元序跋的圖書 |
 |
慶元序跋 作者:陳慶元 出版社:蘭臺網路出版商務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6-01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慶元序跋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陳慶元
福建省金門縣人。歷任福建師範大學古籍所所長、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協和學院院長;現任福建師範大學教授、閩學研究中心主任、《閩學研究》主編。先後被聘為山東大學、復旦大學、福州大學兼職教授、閩南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台灣東吳大學、中央大學客座教授、金門大學榮譽講座教授。兼任中國韻文學會副會長、中國古代散文學會副會長、福建省文學學會會長。近五年主要著作:
東吳手記(二〇一一)臺北:蘭臺出版社
鼇峰集(二〇一二)揚州:廣陵書社
徐熥年譜(二〇一四)揚州:廣陵書社
陶淵明集(二〇一四)南京:鳳凰出版集團
福建文學發展史(二〇一五)臺北:萬卷樓
石倉全集(二〇一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中古文學續稿(二〇一五)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學文獻:地域的觀照(二〇一五)北京:人民出版社
高山青澗水藍(二〇一五)福州:海峽書局
陳慶元
福建省金門縣人。歷任福建師範大學古籍所所長、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協和學院院長;現任福建師範大學教授、閩學研究中心主任、《閩學研究》主編。先後被聘為山東大學、復旦大學、福州大學兼職教授、閩南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台灣東吳大學、中央大學客座教授、金門大學榮譽講座教授。兼任中國韻文學會副會長、中國古代散文學會副會長、福建省文學學會會長。近五年主要著作:
東吳手記(二〇一一)臺北:蘭臺出版社
鼇峰集(二〇一二)揚州:廣陵書社
徐熥年譜(二〇一四)揚州:廣陵書社
陶淵明集(二〇一四)南京:鳳凰出版集團
福建文學發展史(二〇一五)臺北:萬卷樓
石倉全集(二〇一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中古文學續稿(二〇一五)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學文獻:地域的觀照(二〇一五)北京:人民出版社
高山青澗水藍(二〇一五)福州:海峽書局
目錄
009 小引
016 林怡《庾信研究》序
021 施祖毓《吳梅村歌詩編年箋釋》序
027 張帆《末代帝師陳寶琛評傳》序
034 粲然《季節盛大》序
040 苗健青、呂若涵《文采風流千年榜——歷代閩籍作家作品掠影》序
047 胡大雷《宮體詩研究》序
054 苗健青《閩中十子詩》序
060 劉建萍《詩人何振岱評傳》序
069 鴛鴦溪詩社《鴛鴦溪詩詞》序
075 湯江浩《北宋臨川王氏家族及文學考論》序
081 張帆、劉建萍《同光體閩派詩歌評析》序
090 李小榮《〈弘明集〉〈廣弘明集〉述論稿》序
099 王玫《建安文學接受史論》序
107 劉福鑄、王連弟《歷代媽祖詩詠輯注》序
115 徐安琪《唐五代北宋詞學思想史論》序
121 藍雲昌《風生閣詩詞》序
128 林東源《堅守在荒寒之路——陳衍評傳》序
133 田彩仙《漢魏六朝文學與樂舞關係研究》序
139 釋慧蓮《東晉佛教思想與文學研究》序
144 卓克華《古蹟•歷史•金門人》序
152 江中柱《小草齋集》序
165 陳斌《明代中古詩歌接受與批評研究》序
171 趙君堯《天問•驚世——中國古代海洋文學》序
179 胡金望主編《文海揚波——福建省第三屆古代文學研究會學術集萃》序
187 寧淑華《南宋湖湘學派的文學研究》序
195 陳恩維《模擬與漢魏六朝文學嬗變》序
202 阮娟《三山葉氏家族及其文學研究》序
210 施志勝《翻轉中的金門》序
216 王振漢《悠悠浯江水》序
223 陳慶瀚《離散對話錄》序
231 蔡彥峰《玄學與魏晉南朝詩學研究》序
235 楊玲《林譯小說及其影響研究》序
240 王晚霞《柳宗元研究》序
245 郗文倩《古代禮俗中的文體與文學》序
253 福建師大文學院《藤山述林》序
260 陳未鵬《宋詞與地域文化》序
268 林怡《閩學脈》序
275 鄭珊珊《明清福建家族文學研究》序
282 楊海明《唐宋詞與人生》書後
291 顏立水《金同集》書後
298《金門洪景星先生墓誌銘》書後
303 吳宏一《留些好的給別人》書後
308《陳長慶作品集》書後
315 附錄:敬畏學術——我和《文學遺產》結下的五十年不解之緣
325 後記
016 林怡《庾信研究》序
021 施祖毓《吳梅村歌詩編年箋釋》序
027 張帆《末代帝師陳寶琛評傳》序
034 粲然《季節盛大》序
040 苗健青、呂若涵《文采風流千年榜——歷代閩籍作家作品掠影》序
047 胡大雷《宮體詩研究》序
054 苗健青《閩中十子詩》序
060 劉建萍《詩人何振岱評傳》序
069 鴛鴦溪詩社《鴛鴦溪詩詞》序
075 湯江浩《北宋臨川王氏家族及文學考論》序
081 張帆、劉建萍《同光體閩派詩歌評析》序
090 李小榮《〈弘明集〉〈廣弘明集〉述論稿》序
099 王玫《建安文學接受史論》序
107 劉福鑄、王連弟《歷代媽祖詩詠輯注》序
115 徐安琪《唐五代北宋詞學思想史論》序
121 藍雲昌《風生閣詩詞》序
128 林東源《堅守在荒寒之路——陳衍評傳》序
133 田彩仙《漢魏六朝文學與樂舞關係研究》序
139 釋慧蓮《東晉佛教思想與文學研究》序
144 卓克華《古蹟•歷史•金門人》序
152 江中柱《小草齋集》序
165 陳斌《明代中古詩歌接受與批評研究》序
171 趙君堯《天問•驚世——中國古代海洋文學》序
179 胡金望主編《文海揚波——福建省第三屆古代文學研究會學術集萃》序
187 寧淑華《南宋湖湘學派的文學研究》序
195 陳恩維《模擬與漢魏六朝文學嬗變》序
202 阮娟《三山葉氏家族及其文學研究》序
210 施志勝《翻轉中的金門》序
216 王振漢《悠悠浯江水》序
223 陳慶瀚《離散對話錄》序
231 蔡彥峰《玄學與魏晉南朝詩學研究》序
235 楊玲《林譯小說及其影響研究》序
240 王晚霞《柳宗元研究》序
245 郗文倩《古代禮俗中的文體與文學》序
253 福建師大文學院《藤山述林》序
260 陳未鵬《宋詞與地域文化》序
268 林怡《閩學脈》序
275 鄭珊珊《明清福建家族文學研究》序
282 楊海明《唐宋詞與人生》書後
291 顏立水《金同集》書後
298《金門洪景星先生墓誌銘》書後
303 吳宏一《留些好的給別人》書後
308《陳長慶作品集》書後
315 附錄:敬畏學術——我和《文學遺產》結下的五十年不解之緣
325 後記
序
序
古人作文,必先辨明文體。晚明文學家、藏書家徐為友人林古度之父林章作傳,林古度私下增益了一些瑣碎的、或不夠忠厚的內容入傳,徐甚為不快。不是林古度增益的內容不實,而是所增益的內容傳記不宜。徐說,你那些內容,寫入「行狀」,是可以的,寫入「傳」,是不宜的。傳有傳的文體,行狀有行狀的文體,不同的文體,有不同的寫作要求。
徐為了維護傳體的尊嚴,對林古度說,如果你執意增益那些內容,請不要把我寫的傳刻入《林初文集》中,另請髙明好了。我們今天看到《林初文集》徐所寫的林章傳,那些不宜入傳的內容果然刪去不存。
當然,大文章家偶然也會突破文體的局限,寫出人意料的作品。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首敘馬君先世及歷官、子女,次敘與馬氏三世交誼,再次哭馬氏三世,最後三哭,並感慨人世。或因少監無一事可紀,故著墨於三世交游,兩番摹寫,造出奇偉,雖似哀誄文、與墓誌體稍乖離,仍為韓集中名篇。後世如歐陽修,也是大家,屢仿之而不能。
新世紀以來,大學校園,科研機構,人人抱隋侯之珠、荊山之玉,內地每年出版圖書的數量已經傲居世界第一;如果按人口平均,台灣地區也位列世界第二。在這大潮流的裹挾下,不知不覺,我也混入出書的大軍之中。而且,不僅自己出書,還不時應朋友、同學所請(間或受命於單位)作序。收入本書之序,始於一九九九年,止於近期。其初每年一至兩篇,後來則兩三篇,集腋成裘,積少成多,三十多篇,加上數篇跋語,已可都為一書,於是命之曰《慶元序跋》。二〇一一年,《東吳手記》軟精裝本在蘭臺出版社出版,裝潢印製精美,師友同學稱贊有加,至有愛不釋手者。此後,我在內地出書,也開始關心書籍的美觀,二〇一二年、二〇一四年在廣陵書社出的《鼇峰集》(三冊)、《徐熥年譜》,封面設計古樸,精裝,排版疏朗;二〇一四年鳳凰出版集團的《陶淵明集》,小開本,布面精裝,亦差強人意。承盧社長瑞琴女士不棄,本書仍然交由蘭臺出版。
書序作為一種文體,有它固有的特質。書序,還可以細分若干小類,如文獻典籍序、詩文集序、雅集詩序、單篇詩賦序、專書專著序等,不同的小類,作法固有不同,但不論何種書序,序這種文體的寫作,和論文的寫作肯定有別。但是當今的許多研究著作的書序,卻和論文很相像,往往側重於把一部著作的成績歸納成若干要點,再稍稍論述之。我自己也不能
免俗。這樣一來,當今的書序往往也就缺少序作者的個性。研究當代文體的專家,是否對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各種文體有較全面深入的研究,我不太清楚。如果把當代的序體作為一個研究課題,一定是一個有趣的事。
除了文獻典籍,撰序者對撰序對象,通常不會太陌生。梁朝任昉,「嘗以筆札見知」於王儉,故為之整理遺文,撰《王文憲文集序》,對王儉生平履歷、性格好尚,文風特徵,無不了如指掌。唐賈至之父與李適交誼甚深,適子又與至有「聲譽之好」,故得以體察李適文之優長。宋歐陽修《釋祕演詩集序》,先撇開撰序對象釋祕演,而從石延年落筆,由石延年引出釋祕演,以為「皆奇男子也」。歐陽修再次撇開祕演之詩,而借石延年之「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評祕演詩,且點到為止,不作發揮,最後才引入作序的題旨。明曹學佺至交林光宇,曹氏為其選《林子真詩集》並撰序、跋。《林子真詩序》花了許多筆墨鉤畫林光宇的好色、疏懶、恃情傲物,然而卻至孝,大有魏晉之風,以見其詩的率真出自胸情。
回頭審視十多年來自己寫的這些序文,除了「未能免俗」的那部分,即一般序文的評價和介紹方面,似乎也注意到著作作者的生活經歷和求學經歷,甚至他們的個性好尚,也注意到在人生的旅途中,我和這位作者的交集往來,有時還記錄某些趣事,盡量避免把序文寫成枯燥無味的論說體。也就是說,盡量注意序文的可讀性。雖然經努力,還是沒能做好。
作序時,我常常想得很多,寫進序文的卻很少。認識安琪,是在認識她的夫君秦惠民先生之後。一九七九年,我在南京師範大學從段熙仲(一八九七-一九八七)教授治漢魏六朝文學,惠民先生從唐圭璋先生治宋詞,宿舍就在我的對門,其時,惠民先生和安琪尚未成為眷屬。沒想到二十一年後,安琪來從我讀博。二〇〇二年,恩維考博,後來他被另一所學校錄取了。過了一週,恩維來電,說打算退學,來我這兒旁聽,明年再考。我說,三年很快就會過去的,一定得堅持。恩維畢業後,果然回到我身邊做博後。人生的緣分如此!我為文倩作序,自然想起二〇〇四年河北師範大學的一個活動,接待我們的研究生有哪些人,全然忘記了,等到洪雷、文倩夫婦來福建師範大學工作,說起來,原來早已相識,他們忙碌的身影恍然再現;而且,洪雷還是我山東大學的朋友鄭訓佐教授的碩士生……
一篇序文,不過三千來字。來不可遏,去不可止,有時興頭一來,下筆千言,不能自休;有時文思枯竭,三天不能一字。有時是身不由己,忙於應付各種雜務,耽擱了寫作。至今我仍然深感抱歉的是為胡旭的著作撰序,被我一拖再拖,拖到他的書付印了,我的序還在「構思」之中。
有幾篇序跋是為金門同鄉作的。慶瀚教授是我的同宗兄弟,也是中央大學不同科系的同事。慶瀚在法國讀博士,學的自然科學,同時又修了兩年的文學博士課程。讀他的文章,像是喝法國葡萄酒一般,充滿溫情和些許的浪漫;他是一位自然科學家,又有很多有理性思考。長慶兄是著名的小說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有一段金門軍中服務處的特殊經歷,小說的題材別出匠心,我作的跋,附在他的多卷本文集之末,原題叫《長春書店裡的陳長慶》。卓克華教授雖然不是金門人,他的一部著作研究的卻是金門史,吸引我的不僅是該書的研究對象,更主要的是他的研究方法以及資料的蒐集。
書中序文涉及到的作者,施祖毓兄、胡金望兄已經離去。祖毓兄,五十後,病逝於二〇〇八年;金望兄,五零後,病逝於二〇一三年。前兩三年,重慶一位研究吳梅村的學者,苦於祖毓兄已經再也無法聯絡上,因讀過我作的序,轉而向我乞要複印本。也許這位學者比我更需要此書,我索性把有祖毓兄題籤的書轉送給他。轉寄之前,摩娑再三,如對故人,唏噓不已。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新一代的學者正在成為學術的中堅,我為之作序的阮娟、鄭珊珊,他們都是八零後,出書時都不過三十來歲。這兩三年給九零後的碩博士生上課,我對他們說,將來你們的著作出版,如果不嫌棄,我還會為你們撰序。
「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阮籍所說,的確是大實話。「朝如青絲暮成雪」,白髪如雪,仍不失美感,李白似乎比阮籍更懂得長者之美學。無論醜與美,阮籍、李白,都以青少年為「朝」,老人為「暮」,看法都是一致的;當今把長者都看作「夕陽」(雖然後邊綴上一個「紅」字),和「暮」的意思也差不多,只是很容易讓人聯想起李密所說「日薄西山」的意思。莊子講齊物,以為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的大椿,和不知晦朔的朝菌、不知春秋的蟪蛄沒有兩樣。作為個體的一切生物,結局固然沒有不同,但是個體生物存在時間的長度和過程卻是很不一樣的。曹學佺為林光宇作序,光宇卒年二十八;任昉為王儉作序,王儉卒年三十八;歐陽休作《蘇氏文集序》,蘇舜欽卒年四十一。對林光宇、王儉、蘇舜欽來說,二十多歲、三十多歲就是他的暮年。二〇一四年,廈門第一中學一九六四屆髙中畢業五十週年紀念活動,同學推舉我作為代表發言,我說,面對來參加活動的九十多歲的王毅林校長,我們沒有資格言老;面對九十多歲仍然乘公交車上教堂做禮拜、唱詩的我的母親和她的姐妹,我們沒有資格言老。
謝謝本書所有為我提供作序機會的朋友和同學,謝謝大家讓我分享閱讀作品和研究成果的快樂,謝謝大家帶給我作序過程和之後的莫大愉悅!謹將此書獻給為我慶生的親友和同學!
慶元七十初度
古人作文,必先辨明文體。晚明文學家、藏書家徐為友人林古度之父林章作傳,林古度私下增益了一些瑣碎的、或不夠忠厚的內容入傳,徐甚為不快。不是林古度增益的內容不實,而是所增益的內容傳記不宜。徐說,你那些內容,寫入「行狀」,是可以的,寫入「傳」,是不宜的。傳有傳的文體,行狀有行狀的文體,不同的文體,有不同的寫作要求。
徐為了維護傳體的尊嚴,對林古度說,如果你執意增益那些內容,請不要把我寫的傳刻入《林初文集》中,另請髙明好了。我們今天看到《林初文集》徐所寫的林章傳,那些不宜入傳的內容果然刪去不存。
當然,大文章家偶然也會突破文體的局限,寫出人意料的作品。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首敘馬君先世及歷官、子女,次敘與馬氏三世交誼,再次哭馬氏三世,最後三哭,並感慨人世。或因少監無一事可紀,故著墨於三世交游,兩番摹寫,造出奇偉,雖似哀誄文、與墓誌體稍乖離,仍為韓集中名篇。後世如歐陽修,也是大家,屢仿之而不能。
新世紀以來,大學校園,科研機構,人人抱隋侯之珠、荊山之玉,內地每年出版圖書的數量已經傲居世界第一;如果按人口平均,台灣地區也位列世界第二。在這大潮流的裹挾下,不知不覺,我也混入出書的大軍之中。而且,不僅自己出書,還不時應朋友、同學所請(間或受命於單位)作序。收入本書之序,始於一九九九年,止於近期。其初每年一至兩篇,後來則兩三篇,集腋成裘,積少成多,三十多篇,加上數篇跋語,已可都為一書,於是命之曰《慶元序跋》。二〇一一年,《東吳手記》軟精裝本在蘭臺出版社出版,裝潢印製精美,師友同學稱贊有加,至有愛不釋手者。此後,我在內地出書,也開始關心書籍的美觀,二〇一二年、二〇一四年在廣陵書社出的《鼇峰集》(三冊)、《徐熥年譜》,封面設計古樸,精裝,排版疏朗;二〇一四年鳳凰出版集團的《陶淵明集》,小開本,布面精裝,亦差強人意。承盧社長瑞琴女士不棄,本書仍然交由蘭臺出版。
書序作為一種文體,有它固有的特質。書序,還可以細分若干小類,如文獻典籍序、詩文集序、雅集詩序、單篇詩賦序、專書專著序等,不同的小類,作法固有不同,但不論何種書序,序這種文體的寫作,和論文的寫作肯定有別。但是當今的許多研究著作的書序,卻和論文很相像,往往側重於把一部著作的成績歸納成若干要點,再稍稍論述之。我自己也不能
免俗。這樣一來,當今的書序往往也就缺少序作者的個性。研究當代文體的專家,是否對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各種文體有較全面深入的研究,我不太清楚。如果把當代的序體作為一個研究課題,一定是一個有趣的事。
除了文獻典籍,撰序者對撰序對象,通常不會太陌生。梁朝任昉,「嘗以筆札見知」於王儉,故為之整理遺文,撰《王文憲文集序》,對王儉生平履歷、性格好尚,文風特徵,無不了如指掌。唐賈至之父與李適交誼甚深,適子又與至有「聲譽之好」,故得以體察李適文之優長。宋歐陽修《釋祕演詩集序》,先撇開撰序對象釋祕演,而從石延年落筆,由石延年引出釋祕演,以為「皆奇男子也」。歐陽修再次撇開祕演之詩,而借石延年之「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評祕演詩,且點到為止,不作發揮,最後才引入作序的題旨。明曹學佺至交林光宇,曹氏為其選《林子真詩集》並撰序、跋。《林子真詩序》花了許多筆墨鉤畫林光宇的好色、疏懶、恃情傲物,然而卻至孝,大有魏晉之風,以見其詩的率真出自胸情。
回頭審視十多年來自己寫的這些序文,除了「未能免俗」的那部分,即一般序文的評價和介紹方面,似乎也注意到著作作者的生活經歷和求學經歷,甚至他們的個性好尚,也注意到在人生的旅途中,我和這位作者的交集往來,有時還記錄某些趣事,盡量避免把序文寫成枯燥無味的論說體。也就是說,盡量注意序文的可讀性。雖然經努力,還是沒能做好。
作序時,我常常想得很多,寫進序文的卻很少。認識安琪,是在認識她的夫君秦惠民先生之後。一九七九年,我在南京師範大學從段熙仲(一八九七-一九八七)教授治漢魏六朝文學,惠民先生從唐圭璋先生治宋詞,宿舍就在我的對門,其時,惠民先生和安琪尚未成為眷屬。沒想到二十一年後,安琪來從我讀博。二〇〇二年,恩維考博,後來他被另一所學校錄取了。過了一週,恩維來電,說打算退學,來我這兒旁聽,明年再考。我說,三年很快就會過去的,一定得堅持。恩維畢業後,果然回到我身邊做博後。人生的緣分如此!我為文倩作序,自然想起二〇〇四年河北師範大學的一個活動,接待我們的研究生有哪些人,全然忘記了,等到洪雷、文倩夫婦來福建師範大學工作,說起來,原來早已相識,他們忙碌的身影恍然再現;而且,洪雷還是我山東大學的朋友鄭訓佐教授的碩士生……
一篇序文,不過三千來字。來不可遏,去不可止,有時興頭一來,下筆千言,不能自休;有時文思枯竭,三天不能一字。有時是身不由己,忙於應付各種雜務,耽擱了寫作。至今我仍然深感抱歉的是為胡旭的著作撰序,被我一拖再拖,拖到他的書付印了,我的序還在「構思」之中。
有幾篇序跋是為金門同鄉作的。慶瀚教授是我的同宗兄弟,也是中央大學不同科系的同事。慶瀚在法國讀博士,學的自然科學,同時又修了兩年的文學博士課程。讀他的文章,像是喝法國葡萄酒一般,充滿溫情和些許的浪漫;他是一位自然科學家,又有很多有理性思考。長慶兄是著名的小說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有一段金門軍中服務處的特殊經歷,小說的題材別出匠心,我作的跋,附在他的多卷本文集之末,原題叫《長春書店裡的陳長慶》。卓克華教授雖然不是金門人,他的一部著作研究的卻是金門史,吸引我的不僅是該書的研究對象,更主要的是他的研究方法以及資料的蒐集。
書中序文涉及到的作者,施祖毓兄、胡金望兄已經離去。祖毓兄,五十後,病逝於二〇〇八年;金望兄,五零後,病逝於二〇一三年。前兩三年,重慶一位研究吳梅村的學者,苦於祖毓兄已經再也無法聯絡上,因讀過我作的序,轉而向我乞要複印本。也許這位學者比我更需要此書,我索性把有祖毓兄題籤的書轉送給他。轉寄之前,摩娑再三,如對故人,唏噓不已。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新一代的學者正在成為學術的中堅,我為之作序的阮娟、鄭珊珊,他們都是八零後,出書時都不過三十來歲。這兩三年給九零後的碩博士生上課,我對他們說,將來你們的著作出版,如果不嫌棄,我還會為你們撰序。
「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阮籍所說,的確是大實話。「朝如青絲暮成雪」,白髪如雪,仍不失美感,李白似乎比阮籍更懂得長者之美學。無論醜與美,阮籍、李白,都以青少年為「朝」,老人為「暮」,看法都是一致的;當今把長者都看作「夕陽」(雖然後邊綴上一個「紅」字),和「暮」的意思也差不多,只是很容易讓人聯想起李密所說「日薄西山」的意思。莊子講齊物,以為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的大椿,和不知晦朔的朝菌、不知春秋的蟪蛄沒有兩樣。作為個體的一切生物,結局固然沒有不同,但是個體生物存在時間的長度和過程卻是很不一樣的。曹學佺為林光宇作序,光宇卒年二十八;任昉為王儉作序,王儉卒年三十八;歐陽休作《蘇氏文集序》,蘇舜欽卒年四十一。對林光宇、王儉、蘇舜欽來說,二十多歲、三十多歲就是他的暮年。二〇一四年,廈門第一中學一九六四屆髙中畢業五十週年紀念活動,同學推舉我作為代表發言,我說,面對來參加活動的九十多歲的王毅林校長,我們沒有資格言老;面對九十多歲仍然乘公交車上教堂做禮拜、唱詩的我的母親和她的姐妹,我們沒有資格言老。
謝謝本書所有為我提供作序機會的朋友和同學,謝謝大家讓我分享閱讀作品和研究成果的快樂,謝謝大家帶給我作序過程和之後的莫大愉悅!謹將此書獻給為我慶生的親友和同學!
慶元七十初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