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一
源自對於儒家思想與義理之學的喜愛,我在就讀中文系時同時雙修哲學系。從大學至研究所先後受教於張永儁、劉述先、林啟屏諸先生。多年薰習過程中,不僅對先秦子學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於儒家思想人文精神與時代意涵,也才產生真正的相應。這種精神上的驚喜不斷持續著,也因此如何詮釋孔孟思想使其接榫於現代社會,也就成為我日後研究重心所在。其中既挾帶了力有不逮的慚愧,也有當仁不讓、捨我其誰的使命感。
到了撰寫博士論文時,這個問題更加迫切具體。我不得不面對一個嚴肅的課題:在儒家思想復興、諸子研究百家爭鳴的現代學術場域中,自己是否可能可以在功夫論、本體論、心性論等領域論述中超越前人?又什麼樣的研究進路,可以更進一步凸顯傳統哲學的現代意涵?我的思考重心因此著落在兩個面向:一、什麼是這個時代的中心關懷?二、這個時代的價值設準何在?答案自是民主制度與法治理念。現代社會已不再討論如何建立一個「聖君賢相」的盛世,而是思考在民主體制下,國家權力與人民權利如何達成最大的平衡。人們安立的價值也不再是「分位不同、尊卑有別」之說,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平等、隱私、人權等概念。假如儒學不能通過「語言轉化」與「概念銜接」方式,開展古老文本的現代意義,乃至回應這個時代提出的各種挑戰,那麼所有對於儒學推崇的論述,終究只能說服儒家系統內的人,再難得到系統外之人的認可。經過一番長考,我於是決定從法思想角度切入,作為儒學乃至先秦諸子與現代社會的對話平台,除了引為博士論文撰寫主題,也是日後研究重心所在。就這樣,在原有中文、哲學學位外,博士修業期間我又另外取得法律學士資格,藉以厚實自己學術研究的理論基礎。
從政治外王面向思考儒家時代意涵的工作,其實開始得非常早。牟宗三《政道與治道》、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都隱含了解釋制度合理性的用心。李明輝《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鄧育仁《公民儒學》則更進一步,以現代語彙概念重新省察與分析。大陸學者蔣慶《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再論政治儒學》雖然與當代新儒家立場不同,批判甚鉅,但也是另一種重新詮釋儒家的嘗試,論述不同,用心彷彿。郭齊勇所編《儒家倫理爭鳴集─以親親互隱為中心》、《正本清源論中西─對某種中國文化觀的病理學剖析》,則是討論儒家倫理與現代法治理念的重要參考資料,所著《儒學與現代化的新探討》及馬小紅《禮與法─法的歷史連接》、任強《知識、信仰與超越─儒家禮法思想解讀》,均是站在「不薄古人,意在新詮」的立場,為儒家外王哲學發聲。
正如前面提到的:假如我們想要闡述儒家外王思想的普遍意義,那麼我們就不能只是解釋其主張的歷史發生合理性,更不能侷限在倫理範疇內闡述正當性。否則永遠只能說服系統內之人,於系統外者毫無影響。不幸的是民主法治社會中,儒學系統外的人很可能是多數,且是極大多數。什麼是系統內的人?即是接受傳統文獻語彙與現代儒學研究分析概念,在此基礎上建構並肯定儒家思想價值者,我自己就是其中一分子。我相信儒學探討的乃是人類普遍性的問題,不論古今、無分南北,都不會有落伍過時的問題。但是對系統外,也就是對於儒家思想無感乃至反感者,前述說法只是我們一廂情願的玄學幻想,多數人更在意的是如何捍衛自身的權益。甚至在若干激進派眼中,孔子「溫良恭儉讓」乃是禁錮自由的鴉片,呈現自己、競爭進步才是生存的硬道理。
舉例而言,法治社會強調法律的獨立客觀性,系統外者因此反對孔子「父子犯罪相隱」主張,如此片面強調群體和諧與家族利益,無異是將家庭倫理凌駕於公共秩序之上。他們更鄙棄夫子「聽訟吾猶人也,必也是無訟乎」之說,正因為孔子否定「法律訴訟」功能,使人厭惡或畏懼通過法律取得勝利與正義,導致中國千百年來始終無法發展出具有現代意義的實體法與程序法保障。這當然是一種極度負面的評價,但假如我們回應的方式是要求人們理解並同情儒家,由於儒家身處古老的農業社會,面對是缺乏效率與數字化管理的國度,因此必然需要提高血親倫理,使家族成為帝國最重要的管理單位。這種解釋不僅難以獲得現代人的同情,而縱使博得些微的憐憫,但那也只是坐實了儒家思想已經過時的印象。學者或許可以騰挪少數心力進行緬懷式的研究,但人們確實可以心安理得地將儒學束之高閣。
二
本書各篇嘗試跳脫過去從系統內思考事情方式,轉由現代法治社會系統考察儒墨思想的合理性。當然,我也意識到了自己即將陷入一個巨大的漩渦中。在客觀技術上,這牽涉到跨領域整合研究的操作能力問題;在基礎理論上,此一研究是否具備理論正當性與數據充分性,必然也將引起論者懷疑。原因在於現行法政制度乃是繼受自西方,傳統中華法系已不復存在,因此一個以倫常道德為價值基礎、血緣宗族為制度載體的儒家思想,如何可能與法治社會和諧共處?無論從直覺、常識到證成,在在都有極大的障礙。我開始進行一系列的思想實驗,儒家思想與現代法治社會可能的關係主要有三種:
一致關係。
矛盾關係。
互補關係。
第一種一致關係,即指對比客體間具有相同的價值設準,有如水乳般可以交融互攝。事實上這是可能性極低的選項,現行政法制度以自由主義為前提,個人為權利主體,強調「契約自主」下的法律關係而非「分位結構」中的道德關係。如說彼此和諧一致,則我們就無法解釋中國古代法律為何有如此多因身分階級而生的不平等規定。
第二種是矛盾關係,乃是有你無我、只有一種價值可以成立的排他選項。許多人批評儒家與民主政治在制度與價值認同完全相反,前者是君主禮治政體,後者是民主法治政體。儒家道德誡命只會馴化人民,麻痺民主自由意志,這是中國始終無法建立現代化社會的原因。筆者對於這樣的批判並不認同,事實上沒有一個法治社會不需要道德以及超越性理念的支持,民主國家《憲法》強調的「自由、平等、人權」就是抽象道德理念的呈現。如果民主社會領袖可以以致力追求國際和平、維持社會幸福安定為己任,那為何必不容許儒家提倡「修齊治平」之說,而稱「四維八德」為封建?批評者誤解了民主國家並非不重道德,更不排斥道德。相反的,在法律制度成形前,最好最大程度考慮道德的重量,避免日後產生實踐的困難。唯一要注意的是:(1)在法律制度形成前,道德不是至高或者唯一的標準。(2)通盤考量道德層面後,一旦完成立法,法律即產生排他效力,道德與宗教信仰不得再恣意干涉。
民主社會的道德容忍度確實遠大於古代社會,這也是造成一般人誤以為道德、法律必須脫鉤的原因。但其實「道德肯定」與「道德容忍」乃是兩種不同的標準,不應該混淆。當儒家宣稱孝是一種道德價值時,並不一定指不孝是法律所不該或不能容忍的行為,凡是違背孝道的行為都必須藉由律法加以處罰。著名的例子如《荀子‧宥坐》篇中記載: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歛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
孔子擔任魯司寇期間,國內發生一起父子相訟事件,孔子擱置三個月而不判案。此舉引來季孫氏的不滿,以為孔子平日高談德治但卻言行不一,實是對於自己的欺騙。從這個例子可知孔子並未將道德無限上綱,作為法律審判的終極標準。反而區分道德與法律的界線,要求國家必須履行「教民、治獄、謹令」程序正義後,司法才有介入處罰的正當性。單純道德誡命不能作為法律執行的依據,更不應該成為執政者暴虐人民的幫凶。
民主社會的任務在於不讓少數個人的主觀價值,成為箝制眾人自由與行動的枷鎖。只要儒家沒有宣稱自己的道德主張可以凌駕法律,那麼他的道德陳述對於民主法治社會就是無害的。不僅無害,如果這些道德主張也是當時社會多數人的共同信念,那麼法律制訂之初與裁判進行之際,法律就有義務審慎考慮這些觀點的影響,不能一概予以排除,以免產生不切實際、不合法感與情感的判決。
理由何在?蓋法律不是純粹數理邏輯的推導,而是人民情感價值結合理性正義的綜合體,如此法律才能成為社群維繫的核心力量。飄風不終朝、暴雨不終日,完全背離道德、風俗的法律,極有可能成為具文或暴政。越來越多的實證法學研究結果顯示,現代立法不但不反對道德概念的置入,反而有愈趨道德化的傾向。如我國《刑法》因受傳統孝道與仁義思想影響,對於殺害直系尊親屬行
為乃特別加重懲罰,《刑法》第271條「普通殺人罪」原本規定:「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刑法》第272條「殺害直系尊親屬罪」則加重其刑為:「殺直系血親尊親屬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又因仁義觀的影響,《刑法》第273條「義憤殺人罪」特別規定「當場激於義憤而殺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保障「義」的價值。晚近所訂如《公平交易法》也以「不可顯失公平」概念制衡獨大的企業一方。簡言之,將儒家倫理與法治社會絕對對立矛盾化,乃是一個情緒化且錯誤的直觀觀察。
如此看來,只剩第三種互補關係最有可能也最為適切。互補關係內涵可分為二:一是價值上的互補。法治社會強調個體主義、權利意識、人性尊嚴等價值,這是傳統儒家思想較少論及的部分,但也非儒家思想必不允許的價值。例如儒家強調人在群體中的義務身分,我應當忠於事、孝於親等,倫理關係涵蓋了人的生命整體活動範圍。另一方面儒家也肯定隱者處士的生命價值,進而給予高度的肯定,這點可以從孔子在《論語‧堯曰》篇中對於隱士表達的尊重;〈先進〉篇對於曾點「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人生自敘羨慕中得證。儒家倫常網絡中並非沒有個體自由的空間,孔子肯定願意承擔重責大任的仁人志士,但也賦予個人獨善其身的自由選項。
此外,儒家雖然強調倫理結構中的義務概念,但也不取消權利意識的正當性。事實上儒家的「義務語言」每每都是針對君王、大臣等有權者所宣說,對於一般百姓則是要求甚低,只是不違法亂紀,從不以高道德標準繩範之。關於這點我在本書〈價值與秩序的抉擇:荀子「禮」論於其法體系之功能與限制論析〉一文中有詳細解釋(參閱該文注34)。余英時先生很早就有這個洞見,他以《孟子‧梁惠王上》「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五畝之宅,樹以之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為例,認為孟子這段話是中國最早的「義務清單」(Bill of Duties),可與英國的「權利清單」相對照。在這份清單中,孟子清楚列舉各項事物,舉凡土地、家畜、耕作時間、教育等都是國家應盡的「義務」,而國家的「義務」反過來說便是人民基本的「權利」。
進一步說,在肯定「人性價值與尊嚴」上,東方遠比西方具有更悠久的論述歷史。西方文化建立在《舊約聖經》及基督教原罪概念之上,完美人性論固不可聞見,亞里斯多德《政治學》則肯定了奴隸制的正當性,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中則稱:「黑人性格之缺乏自制,業然已昭然可見。在這種狀態下,自不容有任何發展,有何文化,而我們今日的所見所聞,在他們向來便是如
此。」西方一向文化缺乏「鈞是人也,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的文化傳統,一個諷刺的歷史現象是,儘管美國開國先賢在〈獨立宣言〉宣稱:「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但是當時美國《憲法》卻公然陳述一個黑奴不等於一個自由人,而是只值自由男女的五分之三,同時保留奴隸制的存在。
相較之下孔子主張「我欲仁,斯仁至矣」、「夷狄入華夏則華夏之」;孟子主張「四端之心,人皆有之」;荀子則稱「塗之人可以為禹」,肯定每個人都具有相同的道德實踐能力與人性尊嚴之平等性。在實然的制度設計上,固然於禮制與律法層面區分尊卑貴賤,但理性上從不否定女人、小人、不同種族、宗教、階級、立場之人成聖成賢的可能。禮制身分劃分不可否認有其時代限制與考量,但卻不是必然的錯誤或邪惡。其實現代法律中也充斥了因身分而有差別對待的規定,如總統享有刑事豁免權、國會議員享有言論免責權、公務員受特別刑法《貪污治罪條例》的約束⋯⋯,都是根據身分別而受差別法律對待的例子。
無論對於中國文化多麼不滿的人,都不能否定上述儒家文獻傳遞的價值,他們是最早的人性尊嚴與平等思想宣言。這些潛藏的思想因子,後來也因民主法治傳入而得到潤生,終究開花成果而使台灣社會立法活動產生加速演進的現象。如同我在博士論文《先秦諸子法思想探析─以儒道墨法四家為主要考察對象》書中所分析的:
由於儒家重視道德義務的性格,其平等概念表現出濃厚的分位等差特色。儒家很早就具備了「相同事物,相同對待;不同事物,不同對待」的平等概念,與現代社會不同的是這個「不同事物」的認知基礎並非源自「契約」而係來自「血緣」。這種平等觀當然不會為我們所接受,然而對儒家而言,血緣身分雖是一個實然的現象,卻能導引出某種抽象的應然價值,正如《周易‧繫辭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的思考模式一樣。
儘管儒家的「平等」基石不為我們所認同,但是這種思維無疑更能銜接今日「平等權」的思想,而這也是中國文化得以接軌現代社會的重要資糧。如受到「男尊女卑」觀念的影響,中國社會長期壓抑女權發展。但是一旦這個觀念反轉,今日我們反而對於女權給予過度的保護。許多西方民主國家,並未在選舉制度中設計「婦女保障名額」的規定,然而我國《憲法》第一百三十四條則明訂了「各種選舉,應規定婦女當選名額,其辦法以法律定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中,也規定了立委選舉的婦女保障名額。在西方人看來,男女既是「平等」的,那麼在從政領域中固然不能特別歧視婦女,但同樣的也無須特別保護。然而我們卻在歷經兩千年壓抑婦女的禮教社會中快速轉變過來。從「女性是弱勢,應當學習服從」到「女性是弱勢,應當予以保障」,這種逆轉看似戲劇化,實則正是儒家「等差式」的平等觀長期浸潤影響使然。
過去傳統社會的階級劃分法我們沒有遵循的義務,更無歌頌讚美的必要。但是肯定人性尊嚴的平等無別,捨儒家人人皆可以為聖人、佛教眾生皆可以成佛之說,至少在同時期的西方文化中是難以聞見的。與其不顧文獻資料而全面批判否定傳統文化,我們實應撥出更大心力思考如何發揚自家寶藏,使之與現代社會銜接,以「合而不同、互助合作」方式建立一個優質的人文理性、民主法治社會。
三
以上說明法治社會可以補強儒家思想之處,反之法治社會難道毫無缺點?或雖有缺點但無儒家置喙發言的空間?這點顯然不合理。假如認同法律乃是社會價值的具體實踐,綜合了感性的文化認同與理性的正義訴求,則顯然只有理解過去文化資產,而非削足適履,迷失於冰冷橫植的法條與制度中,我們才能建立以人為本的法治社會。就這點來看,荀子「有治人無治法」之說至今仍然飽含深刻洞見在其中。
舉例言之,美國總統選舉特別設計了選舉人團制,這是美國建國初共和制與聯邦制權力制衡下的產物,也是各方利益計算妥協後的結果。今天看來選舉人團制實隱藏了若干重大缺陷,導致美國發生數次當選人總票數少於落選者,但因取得足夠「選舉人票」而勝出的例子。儘管如此,但假如想要廢除此制,必得修改《憲法》,亦即需要國會三分之二通過,三十八州贊成,而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若在其他開發中國家,這種總得票數高於另一位候選人而卻落選的結果,必然引發兩派勢力衝突乃至政變發生。但美國一路走來似乎如履坦途,或至少是化險為夷、遊刃有餘。可見人民與政治人物的素質決定了民主政體的良窳,法治社會是否可以良好有效的運作,制度僅是其中要件之一,但不是最重要的要件。由於「後出轉精」的關係,許多新興國家都有一部理念漂亮的《憲法》,但因成員缺乏民主素質,或者流於獨裁,或者陷入紊亂,終究成為具文空談。
從這點來看,荀子「有治人無治法」不能理解為儒家崇尚人治的言論(精確地說,儒家崇尚「禮制」,並以「禮制」壓抑君主恣意之「人治」),而是指出人在制度中的主導性與決定性地位。唯有通過良好的教育,教導出具有高度法治素養的人民,才能真正實現民主法治的優點。反之,徒法不足以自行,若只是終日疾呼建立制度,但卻漠視人文素養與理念教育,則不過是治絲益棼,對於民主政治發展終無實益。儒家是否能為現代法治社會提供養分?本書諸多篇章就是試圖證明這一點。
以上簡單說明我對儒學與法治互補關係的認知,這裡可用一個假設性題目讓問題更加清晰具體:若有一父親屢屢家暴子女,今天儒家會同意子女根據《家暴防治法》對父親提起訴訟嗎?假如儒家的回答是「不、絕對不行」、「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父要子死,子不死不孝」。那麼儒家倫理顯然已經過時,且絕對與法治理念衝突,確實可以棄於歷史灰燼中。但根據經典文獻推導,我們會發現上述三個論述都不會受到儒家的肯定,反將肯定「提起訴訟,聲請法律保護」的作法。論證如下:
理由一,儒家雖然強調親情倫理,但並不是無條件、絕對地接受家庭暴力。《韓詩外傳》、《孔子家語》都記載了曾參不避父親杖打差點喪命之事,孔子不僅不予同情,反而責備曾參,強調「小杖受、大杖走」的故事: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晢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晢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理由二,孟子反對子女無條件接受父母的命令,應當享有意志自主的空間。如《孟子‧萬章上》記舜之不告而娶: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理由三,子女聽從父母之言不是絕對的義務,而應以「義」為最高判準。由於「義」的表現不同,因此古今應對方法自然不一,所謂「從義不從父」是也。如《荀子‧子道篇》稱: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雖堯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愨、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
理由四,子女不但不該無條件服從父母,相反的應當積極勸誡父母,俾使父母改正錯誤的行為。如《孝經‧諫諍章》孔子提出「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的理念: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總結前說:通過法院裁判終止父親家暴行為,為什麼會是儒家今天所當積極肯定的行為?因為在民主法治社會,人們已經脫離古代簡陋的司法訴訟制度,肉刑及其他不合比例原則的刑罰已經廢止,父親不會因為訴訟導致非人的對待。此外在古代,家族乃是處理紛爭最靈活快速單位。今天則是相反,由於小家庭與個人主義盛行,族長裁定紛爭的時代已不復存在。反而法院可以更快速與客觀處理家庭問題,雙方也不會獲得不公平與非法的對待。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家暴事件,無疑是子女阻止父親陷入「親危、親辱、禽獸行」的最佳選項。儒家沒有理由捨棄法律裁判途徑而讓子女求救無門,儒家倫理唯一要求的,乃是勸告子女應以悲憫勸諫之心進行訴訟。雖然這在現代社會乃是不易達到的高標準要求,但卻是法律與親情並行的最大公約數,也是根據儒家經典導出的必然結論。
四
以上說明本書創作的中心關懷,一個可能的質疑是:此種研究方式的正當性何在?這是郢書燕說、一廂情願式的附會之談?或者確有學術研究價值與意義?就我而言答案自屬後者。在這裡,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法概念的真實內涵究竟為何。法律乃是人類社會自古即存的規範,由近代西方社會建立的憲政體制只是其中一種表現型態,無權壟斷所有的定義。從法的本質來看,法是一種具有客觀強效力的價值,也是群體願意共同遵循的行為準則,因此法不是法條、法典、法院、法官之謂。法條、法典僅是表達意義的方式;法院、法官則是展現力量的媒介。如同顏厥安先生〈中國法制史與其他法學課程之關係〉一文中所說:
由語意學的規範概念出發,我們可以發現法律並不是成文法規的集合,也不是裁判的集合,而是一些價值觀念與行為標準的集合,是一些存在於我們意識之中,存在於我們腦中的「意義」。不論包括的範圍多廣,法律不是,或至少可以說不只是任何成文文件的集合,而毋寧是一種觀念的叢結。即使法律就其表彰的媒介來看,絕大部分是以文字記載下來,但是我們仍然必須透過對這些文句的理解,最重要的是對這些文句的「解釋」,我們才能認識到這些法律。單純的文字表彰並不是法律之為法律的必要條件。
從這個定義出發,則法秩序與法思想幾乎與人類組成社群的歷史一樣悠久,神話與宗教即是民族最早法思想的呈現。當部落成員普遍相信某個湖泊為聖湖,常人不可於聖湖沐浴洗滌時,一種法律規範隨之誕生,無論是否伴隨刑罰(死刑、流放或道德譴責),這個堅實的信念都強力地約束了成員的行為。論者可能質疑這樣的定義太過寬泛,沒有條文化與強制力的信念不能隨便列入法規範之中。這點筆者並不反對,但法律是否必須條文化?是否必須伴隨一定刑罰?答案則不必然。判例法與憲政慣例就是一種沒有條文化的法,而《憲法》與《國際法》也不一定有強制力與具體處罰,但他們都是現在法治體制中重要的一環。申言之,如果我們可以接受「群體共同遵循之價值規範與行為準則」作為法的認識內涵,那麼我們就不應該否定古代社會具有法理念,而這些法理念也必然基於普遍理性所生。
如同筆者博士論文〈緒論〉中所說:法律的功能旨在規範社群不同利益個體,確保彼此的行為進入同一種秩序架構中,產生團體最大和諧與利益。為了達成這樣的目的,法律不能只是少數人的玄思產物,而須考量社會需求、道德情感,以及普遍理性等因素。這使得法律表現多元殊異面貌之餘,往往具備一定的共通性。舉例言之,無論是原始部落分配獵物的規則,或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憲法》修正案的討論,內容或有精粗深淺之別,但為了彌平紛爭,人們必然思考到下列幾個問題:
什麼是我們所欲求的價值?(「部落生存」或「立國精神」)
什麼樣的分配方式符合於公平正義?(「平均擁有」或「比例分攤」)
什麼人可以擁有支配的權力?(「巫師占卜」或「公民投票」)
法律現象看似繁複多端,但是法所要討論的本質性問題卻是始終如一。差別只在根據不同的價值,異文化社群也將導出不同的答案。假如只注意到法律表象文化,人們可能會沮喪於現象的多樣複雜,從而放棄比較法學的研究進路。但如果將觀照的重點放在社群如何思考公平正義理念?如何將之具體化為法規範?則法律似乎又與《周易》一樣,同時體現「簡易、變易、不易」三項特質。比較法學就是根據這點取得了研究正當性。有如順手拋出羽球與棒球,常人見到的是兩種不同的運行軌跡,但在科學家眼中,他們則是根據同樣的數學函數與物理法則運作。
這個理念貫穿了我的研究工作,也是過去以來對於比較法學抱持高度熱忱的原因。對比研究並非不問研究客體內涵,強將不同客體置入同一範疇中進行解析,而是根據一定正當性始能為之。就「質」而言,對比之客體必須具備相當程度之同質性。如同前面所述,法律乃是人類理性思維的產物,是故古今中外法條規定雖異,但異中必然有同,同中必可見異。其次就「量」而言,同質性的判定也不能脫離文獻效力範圍,這意味著文獻數量乃是質之判斷的重要來源。研究者必須做到引徵有據,而即使掌握一定資料,也當儘量避開斷簡殘篇式的引用。最好的情形是:除了理論陳述外,該學派或該思想家還能留下具體行事資料,讓我們可以比對理論與實務之間的契合程度,藉由交相驗證,盡可能建構一個能以最大效力解釋最多證據的論述模型。
五
本書總計收錄儒學相關論文四篇、墨學相關論文三篇,主要透過現代觀點重構儒墨思想的現代性意涵。另外附錄一篇,則是運用今日刑法學研究方法解析佛教戒律學內涵。傳統研究有「儒釋道」、「儒釋」、「儒道」、「儒墨」、「佛道」等範疇,本書以「儒釋墨」作為過去幾年研究範疇,似乎有點突兀而不協調。但假如理解筆者個人學習歷程與生命情調,這似乎又是一個合理且必然的進程。原因在於這三門學科都與我的生命有著深刻的交會,其中灌注的不只是學術熱忱,更包含了現實生命的實踐。
我對儒學的冥契,前面已有大篇幅敘述,茲不贅言。至於墨家思想又是如何與我產生聯繫呢?猶記大學求學階段,當時負責教導「中國思想史」課程,也是策勵我學習熱忱至多的,乃是國內墨學專家李賢中老師,這是我與墨子結緣的初始因緣。博士畢業第一年回到母校兼課,適逢李賢中老師轉至臺大哲學系任教,系上墨子課程因此空了出來。由於我在博士論文中專門處理了墨家法思想部分,中文系希望我能接替這門課,不要中斷了這個行之有年的課程,畢竟國內相關的研究與課程並不多。墨家法思想自然不等同於墨家思想,但是基於學術傳承使命感與課程情感,我也只能臨危授命、逼著自己重新練功,開始一段段、一篇篇說解《墨子》的講學(講中學)歷程。
現在看來,教學實是最好的研究,三年講課經驗讓我對於墨子人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一種孺慕之情與溫情敬意油然而生。遙想戰國殺人盈野、不義之戰充斥的年代,墨子與他的追隨者可以捨身忘死,不倦不悔地宣揚國際和平主義,這種精神正是這個時代所缺乏的元素。更難得是墨家並不止於空談理念,而是躬自實踐,終於在那個年代發揮高度影響力,贏得國君世人高度的敬重。《韓非子‧顯學》篇稱:「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淮南子‧泰族訓》則載:「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顯示仁人志士感化社會的強大影響力。
然而煊赫一時的墨家卻在漢以後銷聲匿跡,於中國歷史長河中再無半點音訊。這是一個不尋常的現象,畢竟文獻中找不到政權特別迫害墨家的記載(儒家尚有焚書坑儒劫難)。而即使先有秦火文化之厄,後有楚漢政治之爭,儒、道、法、名、陰陽家都持續在後來的思想與社會層面發揮影響力,唯獨墨家興如烈火焚林,逝如流星電殞。基於對墨子的尊敬與對墨家學派的好奇,我於是發揮所長,嘗試以現代視域重構墨家思想圖像。這些篇章固有個人的溫情敬意,但也不減冷峻筆觸而直言批判。
最後所附〈《四分律》知而妄語戒內涵及其法理分析:現代法律體系參照下的對比研究〉一文,性質看似與本書無關,但同樣屬於比較法學研究,也是筆者生命關懷凝聚所作。我學習佛法已三十年,雖然不是專業的佛學研究者,但是在法義學習與經典研讀上卻始終不輟。佛法不僅可以回答我所有關於宇宙人生問題的困惑,更提供了人們具體、切實、有效的實踐步驟。佛法不是一門形而上的學問或非理性的信仰體系,而是人類慈悲智慧究竟圓滿的表現。倘若使用現代的語言,可以說千百年來佛教各宗派傑出修行人及其追隨者,在他們身上已經進行無數次成功實驗,證明佛法乃是對治生命煩惱的絕佳解藥。這種法喜與慧解讓我願意在繁重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之外,持續投入佛法教育的行列。除了持續多年講授佛學外,同時利用閒暇回覆學生大量來信,以及如本篇之作般,運用跨領域科際整合研究專長,重新建構佛教戒律法理學。當然,作為一種學術呈現,我也必須避免個人宗教情感投射的影響,論文中我於是設計了一套前所未有的對比研究格式,即從現代刑法學角度檢視戒律思想。這些檢驗遠比對儒學、墨學更加嚴格,其中完全拋棄創造性詮釋而一任文獻講話。在此情形下,假如佛教戒律能夠開展出現代法體系所肯定的價值,而且彼此具有高度銜接對話的空間,那麼佛法的周遍圓滿性,也就能夠從中獲得更多的支持。學術分析的結果令人訝異,無論關於審判程序的保障、審判公開平等精神的實踐,乃至罪刑法定主義理念的呈現,律典都表現出超乎時代的嚴謹與進步。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儒墨思想的現代詮解與觀照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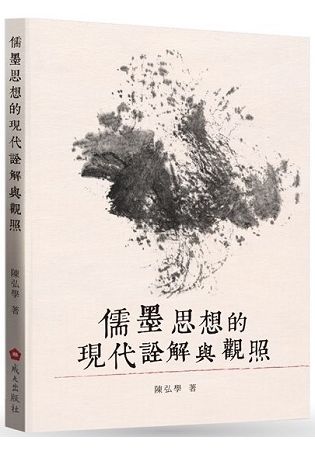 |
儒墨思想的現代詮解與觀照 作者:陳弘學 出版社:國立成功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8-03-20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44頁 / 15 x 21 x 1.3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增訂一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23 |
哲學 |
$ 342 |
社會人文 |
$ 361 |
教育學習 |
$ 361 |
中文書 |
$ 361 |
教育學習 |
$ 361 |
中國哲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儒墨思想的現代詮解與觀照
本書主要論述儒、墨兩家法政思想,並附錄現代刑法對比佛教戒律論文一篇。寫作特色要分為二:一、在研究方法上,採取比較法學研究進路,檢視傳統思想與現代價值體系銜轉共構之可能。是故文章論述重心不在闡述儒、墨內聖道德工夫論面向,而更側重其與現代法理念及現行法制度之對比分析。二、在論述內容方面,傳統研究主要通過價值系統內,即肯定傳統文化之專業研究者立場出發,彰顯中國哲學時代合理性。唯此種作法至多僅能獲得價值系統外,即對傳統文化價值不肯定、無認識或不在意者的同情,終究無法引起世人普遍認同,而成個體生命乃至整體思潮發展動能。本書有鑑於此,是故透過作者所受中國哲學與現代法學雙重訓練,由現代法治社會所生問題意識與價值關懷出發,漸次闡明儒、墨思想蘊藏之現代性意涵。冀此研究方式,能為中國哲學描繪另一種可能的詮解圖像。
作者簡介:
陳弘學
臺灣臺中人,9月28日生。政治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東吳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東吳大學哲學系學學士,輔仁大學學士後法律系學士。現任成功大學中文系專任助理教授、成大文學院應用哲學學程委員。學術專長主要為先秦諸子思想、中國學術史、學術方法論、傳統法學專題研究。著有《標點注釋智證傳》(合撰)、《哲學心靈與現代關懷——哲學概論的第一課》等書,並發表佛學、中國哲學相關論文十數篇。
TOP
推薦序
導論
一
源自對於儒家思想與義理之學的喜愛,我在就讀中文系時同時雙修哲學系。從大學至研究所先後受教於張永儁、劉述先、林啟屏諸先生。多年薰習過程中,不僅對先秦子學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於儒家思想人文精神與時代意涵,也才產生真正的相應。這種精神上的驚喜不斷持續著,也因此如何詮釋孔孟思想使其接榫於現代社會,也就成為我日後研究重心所在。其中既挾帶了力有不逮的慚愧,也有當仁不讓、捨我其誰的使命感。
到了撰寫博士論文時,這個問題更加迫切具體。我不得不面對一個嚴肅的課題:在儒家思想復興、諸子研究百家爭鳴的現代學術場...
一
源自對於儒家思想與義理之學的喜愛,我在就讀中文系時同時雙修哲學系。從大學至研究所先後受教於張永儁、劉述先、林啟屏諸先生。多年薰習過程中,不僅對先秦子學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於儒家思想人文精神與時代意涵,也才產生真正的相應。這種精神上的驚喜不斷持續著,也因此如何詮釋孔孟思想使其接榫於現代社會,也就成為我日後研究重心所在。其中既挾帶了力有不逮的慚愧,也有當仁不讓、捨我其誰的使命感。
到了撰寫博士論文時,這個問題更加迫切具體。我不得不面對一個嚴肅的課題:在儒家思想復興、諸子研究百家爭鳴的現代學術場...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一、前言
儒學作為傳統文化主流,除於思想領域發生深刻影響外,也主導了中國政治運作兩千年之久。近代以來由於儒學異化、國勢寢衰與西方民主科學思想湧入,儒家影響力乃急遽式微,由中心退至邊緣。當代儒學研究固然有中興氣象,但多著重道德心性、功夫修養論的論述,身處現代民主法治社會,儒家法思想似乎再難找到發用空間,終將成為歷史的緬懷。筆者具有中文、哲學、法律三系學位,在多年跨領域學門訓練中對此問題特加關注,越是深入思考越覺儒家倫理與現代社會具有高度對話的空間,關鍵在於理性社會所稱之法並非單純的條文規定,而係多...
儒學作為傳統文化主流,除於思想領域發生深刻影響外,也主導了中國政治運作兩千年之久。近代以來由於儒學異化、國勢寢衰與西方民主科學思想湧入,儒家影響力乃急遽式微,由中心退至邊緣。當代儒學研究固然有中興氣象,但多著重道德心性、功夫修養論的論述,身處現代民主法治社會,儒家法思想似乎再難找到發用空間,終將成為歷史的緬懷。筆者具有中文、哲學、法律三系學位,在多年跨領域學門訓練中對此問題特加關注,越是深入思考越覺儒家倫理與現代社會具有高度對話的空間,關鍵在於理性社會所稱之法並非單純的條文規定,而係多...
»看全部
TOP
目錄
導論
1 儒家倫理與現代法治社會銜轉的可能性探析:以「直躬案例」與「桃應難題」為主要考察對象
2 從禮、法內涵共通性論孔子法思想及其現代性意義
3 價值與秩序的抉擇:荀子「禮」論於其法體系之功能與限制論析
4 從現代法的觀點論儒家「規範優位」思維:以孔、孟、荀三子為主要考察對象
1 儒家倫理與現代法治社會銜轉的可能性探析:以「直躬案例」與「桃應難題」為主要考察對象
2 從禮、法內涵共通性論孔子法思想及其現代性意義
3 價值與秩序的抉擇:荀子「禮」論於其法體系之功能與限制論析
4 從現代法的觀點論儒家「規範優位」思維:以孔、孟、荀三子為主要考察對象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陳弘學
- 出版社: 成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3-20 ISBN/ISSN:978986563532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44頁
- 商品尺寸:長:150mm \ 寬:210mm \ 高:13mm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中國哲學
|











